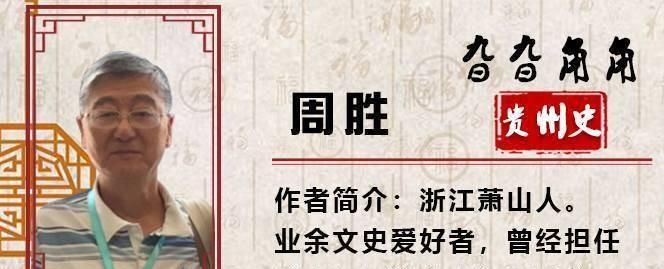
據說興義曾被誤稱為“黎峨”。
鹹豐《興義府志》認為稱興義為“黎峨”的始作俑者為道光年間興義知縣廖大聞,其所撰《興義雜詩》一卷,即名《黎峨雜詠》。這樁公案,在鹹豐《興義府志》中是這樣梳理的:“今郡人多稱興義縣為黎峨。道光中,興義知縣廖大聞撰《興義雜詩》一卷,即名《黎峨雜詠》,其詩有句雲:‘煙雲設色仰黎峨’。自注雲:山在城西。而今考縣城西實無黎峨山,蓋臆說也。即《明一統志》雲:‘平越衛,古蠻夷地,名黎峨’。是黎峨,乃平越也。又考嘉慶三年,總督鄂輝請設興義縣疏雲:黃草壩請改設縣治。查平越府之平越縣,事簡民淳,若将平越縣撤歸平越府,盡可調理裕如。請移設黃草壩,該處興義府所屬,即名為興義縣。是當裁平越縣而設興義縣,後人不知平越為黎峨,而遂誤以興義縣為黎峨。廖大聞鑿空附會,又進而為之辭也”。不僅被斥為“臆說”,“鑿空附會”,連興義的沿革都搞不清楚,居然還寫成詩。
說起來,廖大聞也還不算是個碌碌之輩。廣西臨桂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舉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出任安徽宿松縣知縣。明朝末年,宿松官府糧倉被毀。康熙四年(1660)和嘉慶二十二年(1817)兩次重建,廖大聞再次修建糧倉,這次修建比前次更加堅固,考慮更加周到。 邑人捐資在築墩渡增設公益渡船,增置田,岸北造渡屋讓行人避風雨,廖大聞撰寫碑記。還和望江縣、潛山縣、懷甯縣、太湖縣等知縣共同捐資修建省城試院。
道光元年(1821)任安徽桐城知縣。道光二年(1822),桐城士紳捐銀,于北門内培文書院旁,添買公房和民房,将合為考棚。三年(1823),遭遇水荒災,捐銀不敷,未及興工。廖大聞與大家公議,覺得培文書院及民宅,地勢狹隘。南鄉捐銀較多,因将民宅抵還南鄉,變價添修白鶴峰文社,易名為“白鶴峰書院”,“每歲二月,知縣擇期開課,”而考棚另議辦理。廖大聞還獨倡捐銀三百兩,合邑人捐銀共二千一百零三兩三錢,買崇文洲作學田,以增書院經費。廖大聞又捐廉倡導,裡人劉存莊、潘楫等廣募租銀,在明社學故址梵天城(今天城中學校址)文昌閣建天城書院。
天成書院碑
此外,廖大聞還和署懷甯縣朱士達,各倡捐銀一百兩,與省内各州縣共捐銀二千一百零三兩三錢,買新生洲一半,用于資助省城敬敷書院膏火。
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撫下令各縣修志,廖大聞便着手準備,“集邑士大夫相與謀是以修之者”。不料道光五年(1825),廖大聞“以吏議去”,卸職傳回家鄉臨桂。接任的奉天豐甯謝時和與貴州廣順金鼎壽“踵其事為之”。道光七年(1827)三月,廖大聞自廣西至桐城,繼續完成《桐城續修縣志》24 卷。知縣尹作翰說:“邑志之修實始事于廖,其終事也廖”。
道光十年至十一年(1830-1831),廖大聞起任安徽建平縣(今郎溪縣)知縣。十二年(1832)改任鳳陽縣知縣。誰知道第二年,就遭到“先行解任”的處分。其原委真是有點像小說情節。
道光十三年(1833),台灣有“匪徒滋事”,道光帝從河南、陝西調兵到福建,過境鳳陽。廖大聞派差役陳堂等人去雇車馬以供官兵之用,陳堂就叫振榮号的何铎雇備,何铎遣夥計徐五去雇,自己進城守候,即在陳堂家住宿。誰知到了半夜,何铎突然上吊自殺。道光帝認為“此次兵差過境,該縣站設馬匹不敷,自須寬為雇備。如果向民間發價和雇,何至累及闾閻。況何铎系由廪生報捐訓導,并非應充行戶之人。縱使代雇遲誤,何至情急輕生。”追查下來,原來是因何铎派夥計去雇馬遲延了,陳堂之子陳培就認為何铎延誤軍情,将何铎鎖押,加以逼吓,以緻何铎情急自盡。于是将陳培發極邊煙瘴充軍。廖大聞“失察差役釀命”,交部議處解職。
道光十九年(1839),廖大聞又被起用,來到貴州,署興義縣知縣。鹹豐《興義府志》也認為他“性剛介,居官廉潔”。興義自設縣學以來,還沒有鄉試中式的,大家都認為是縣學宮未建完,“風木不吉故也”。廖大聞上任後,他帶頭倡捐,想方設法籌集經費,将興義縣學宮續建完成,規模齊備。魚龍村黃氏土司與當地土民的土地糾紛,盡管前任已判“永為百姓之業,黃姓不得沾染丘角”,數十年來黃氏仍蠻橫糾纏,道光十九年(1839)“複捏詞妄控”,廖大聞當庭審結,并嚴詞告誡“永不得妄自霸占”。土民勒石立碑,稱“拒控碑”。廖大聞還和左營遊擊張殿奎主持修建了溝通馬嶺河峽谷兩岸的三尺石道,連接配接兩岸的酸棗寨子和馬别寨子,在馬嶺河峽谷濫灘段建成踩水渡,并刻了石碑。
踩水渡石闆路
再說廖大聞的《黎峨雜詠》,平心而論,無論其形式和内容都很值得玩味。共32首,立體式的描述了興義的地理沿革、曆史事件、山川城鄉、飲食習俗、風土人情,于是“邑士傳誦”。有稱:“詩格在香山放翁之間”。
從形式來看,幾乎每句詩後都有注釋,這種形式并不多見。姚華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 )赴興義途中所詠《竹枝辭》形式基本相似;普安楊忠熙《遣懷并序》詩十五首在一些詩句後面有注釋。一般都是在詩後有注釋。
廖大聞《黎峨雜詠》詩句後的注釋,有的是用典的解釋,有的是内容的延伸。以第一首和最後一首為例:“征輪何處六年間,又擁雙旌入八蠻(自甲午夏安徽鳳陽離任,至己亥春乃來貴州,遂署興義縣事)。城出地中環采水(水南十數裡即縣城),路橫天上過花山(安順興義兩府分界處也,越山而南,路極險峻)。居然望縣因唐置(唐置西平州,後改盤州之地即在縣境内),豈複明廷有漢奸,(苗民惡漢人之猾謂漢奸)。撫字心勞聊爾爾,闾閻安睹訟廷閑。”“三年邊俸道如何,輪指冬春兩度過(興義縣乃煙瘴邊缺,實授者三年俸滿。今署事自己亥三月履任,瞬屆辛醜三月矣)。琴築争鳴猶響水(水邊有鄉,寨在城北),煙雲設色仰黎峨(山在城西)。五文苗錦新花樣(今織者多川人,仿佛吾鄉壯錦),一曲蘆笙古調歌(苗樂也。橫木空其中而實其首,毋使之通。唯開圓孔于其旁,或三或五,如竹管大;因其竹管全通之,亦開圓孔于其旁,直插入木孔内,使竹孔與木之空中合,無少參差者。執木之尾而吹之,其聲嘐嘐,自成節奏)。馬别橋頭待言别,能言徧讓綠鹦哥(時尚無人替也。馬别橋在城北,乃往省及府必經之路。鹦鹉出小朝各處山中,間或飛至)”。關于蘆笙的注釋簡直像篇短文;最後一句注釋中的“小朝”指越南境内。其中“煙雲設色仰黎峨(山在城西)”和詩名便釀成了口實。
其詩句内容,尤其是注釋,很有些意思。如描述興義縣城的詩句:“街前街後石㟏岈,蒿目窮街七百家(縣無煙戶冊,于城市中查之,僅得此數)。流寓客民行杖竹(皆江西、福建、湖南、廣東、四川凡五省竝遵義、思南兩府之人,而四川及思南、遵義者尤衆),趕場苗女坐簪花(謂趁墟為趕場,乃四川語,貴州亦然。其有以蘭蕙成枝插鬓者,苗女也)。城頭鴿去雲初散(城内人家屋檐皆栖野鴿),巷口羊回日未斜(羊皆來自雲南,而蓄之者衆)。抱布蚩氓市門滿,大官不用說桑麻(屢奉上官申饬,勸民栽桑養蠶,而民惟種棉織布,無肯易業者,亦天有時地有氣之故乎)。”很形象地展示了興義縣城的概貌,最後一句似乎有點頂撞上司的味道。
有的詩句披露了當時誘苗民賭博的社會現象:“一個新歸寨猶好,夜深茅屋也呼盧(新歸鄉寨名。漢奸盤剝苗民,必先誘之以博)。”或白描下鄉途中就餐情景:“入門牛栅又豬欄,使者中庭作午餐。老圃幾叢花狗尾,(紅蓼也。吾鄉謂之狗尾花)行廚一味菌雞肝。(雞枞也。秋後産山中,如京師鮮蘑菇。然可漬以酺,縣俗謂之雞肝菌)”不少詩句描寫了當地的生活習俗。如“澗南澗北屋斜斜,澣女開門向水涯(黃草壩如是)。隐士泥都分白墡(清異錄:秣陵孟浪山有白墡,周護調以泥壁,謂之隐士泥。今山中以之澣衣去垢),仙人壺怎失丹砂(倭鉛廠及貞豐、冊亨皆産丹砂,縣鄰境也。而胡廬壺惟以貯酒)。歡場綠野閑跳月(縱童男女于野,行歌互答,自相比對,謂之跳月,苗俗有然),愁路青山是打花(鄉間罂粟盛開時,官人則往毀之,謂打花)。半截殘碑兩行字,隻防客過泣山乂(處處皆有路碑,惟多斷者)。”詩中所說澣衣去垢的白墡,就是貴州老百姓所稱“白泥巴”,即觀音土也稱高嶺土,在物資短缺年代,民間普遍用于代替肥皂浣洗衣服。
還有詩句反映出值得研究的當時人員流動現象:“行人來路已迢遙,又見紛紛入小朝(越南國地也。過雲南蒙自百餘裡,即入其境。由縣往七日程矣。今黃草壩有人滿之患,客民多有往者)。誰是同鄉籍五省(黃草壩有五省廟,乃五省客民公建,以聯鄉誼者),勢難長住客三苗。中華不識衣冠美,外國空懷水土饒。此去臨流定回首,天生何處有飛橋(天生橋在縣北)”可以這樣說,廖大聞的《黎峨雜詠》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以詩證史”,似不應以誤興義為黎峨而予以忽視。
令人奇怪的是,鹹豐《興義府志》也載了張國華的《興義縣竹枝詞》:“語音清軟是黎峨,苗錦成時市上多。排草盌糖攜筐賣,紅樓兒女喚幺哥(俗多稱滇人為幺哥)”。張國華,字蔚齋,清興義府城(今安龍縣)人。道光五年(1825)副貢。張之洞曾受業于張國華。同治年間張國華曾主講貴山書院。撰《貴州竹枝詞》350首。張國華亦是《興義府志》的采訪之一,莫非也是受到廖大聞的影響,誤稱興義為黎峨?為什麼《府志》不斥責張國華“臆說”呢?大概“甩鍋”給卸任已久的廖大聞麻煩不大吧。
稱興義為“黎峨”還大有人在。道光年間劉陶然重建興義蒼聖閣,名儒蔣效蔚碑序曰“蒼聖閣,黎峨培風水挽狂瀾建也”;劉陶然之友跋亦曰“黎峨東門外三元橋下原有蒼聖閣一廟”。同治年間雲南廣南才子陸岱秋過興義境内有詩《黎峨道中》;晚清興義廪生劉以誠撰《黎峨風景》八首;興義知府孫清彥印章邊款為“癸亥年刻于黎峨旅次,竹叟筆山人珍玩”;民國興義蔣芷澤《黎峨竹枝詞》,蔣叔雨《黎峨四時田家樂》等,均稱興義為黎峨。諸如蔣效蔚、孫清彥等,均為飽學之士,也不至于都受到廖大聞的誤導吧!
清末姚華應興義筆山書院山長之聘時所寫詩亦稱黎峨。姚華在赴筆山書院之前,就有詩《将之黎峨除弟服》;赴筆山書院途中,有《黎峨日記》紀事;在興義的詩作,收入《黎峨小草》詩集。民國《興義縣志》載:“大黑山距楓塘約八裡,魏巍聳立,為縣城山脈之主峰。”姚華的《竹枝辭》:“行從石隙道巑岏 ,打杵如篙下旱灘(交那路中石立夾道,累累散步,輿行甚艱。予與述之,謂之‘旱灘’)。信口同呼舅子路(輿子口号雲然),問君何處小姑山? 已登坦道尚嶒崚 ,千裡關山十日程(自貴築行十二日到黃草壩,将及千裡)。怪道來途行不得,蹙眉搔耳數巴陵(巴陵在募役司後一站,渡花江之第二日也)。 黔道艱難過蜀道,巴人僰仆亦相憐。黎峨風土誰曾識?浪語傳呼小四川(興義縣主山俗曰‘黑山’,故縣亦名黎峩,黎謂黑,峨謂山也)。 昨夜東風醉流霞,一宿山城賣酒家。疊數青錢呼小妹(自鎮甯來,用錢如銀,铢兩稱量。市人以青錢為貴,取其重也。新城以上仍計枚,而稱錢尚有餘風,土人呼處子為小妹,别呼其怒), 當門垂首坐雕花(語呼刺繡為雕花)”。詩句注釋中就說興義縣主山名黑山,是以縣名黎峨,“黎謂黑,峨謂山也。”或許能提供另一種思路,即用雅詞替代俗稱呢?
姚華
也還有人說,比如清鎮犁倭,原來叫泥窩,覺得不好聽,改為宜窩,抗日戰争時期更名犁倭。如果改宜窩時請文人雅士來改,就可能叫黎峨。
撰文: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