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0日下午,應中國曆史研究院近代以來曆史學知識體系中心、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和青年讀書會的邀請,清華大學曆史系教授侯旭東作了題為“關系視角、日常與曆史”的學術報告,線上線下共有50餘名學者參加。本次活動由崔志海研究員主持,近代史研究所李俊領副研究員、曆史理論研究所劉力耘助理研究員、近代史所呂文浩副研究員作為與談人參與讨論,世界曆史研究所胡玉娟研究員以古希臘羅馬公民社會的“公共日常生活”研究發表了讨論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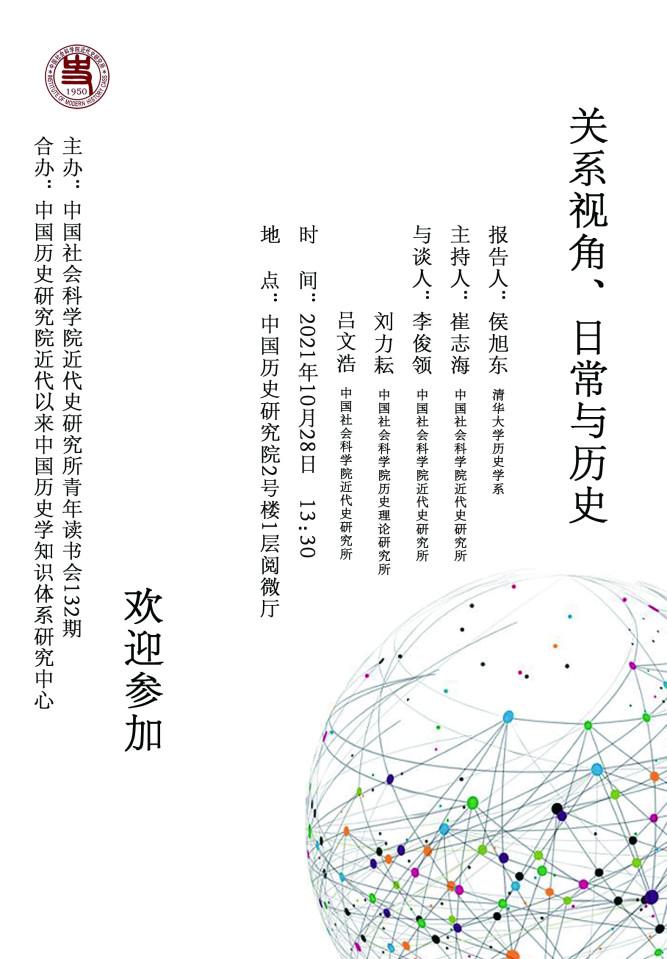
侯旭東教授在過去二十多年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向是秦漢三國時期出土文書簡牍,但他對社會學、人類學也下了很多功夫,是以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對反複進行的事務以及朝廷官府日常統治的研究。他最早完成的“日常統治”研究是2005年發表的《中國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義——尊卑、統屬與責任》(《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雖然其時還沒有提煉出“日常統治”這樣的學術表達。2008至2015年圍繞漢代傳舍使用先後發表了5篇論文,從不同側面對漢帝國日常統治中反複出現的事務進行深描。2010年發表的關于秦漢時期的農民普遍化的研究(《曆史研究》2010年第5期),2018年出版的《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曆史的展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等研究都是對日常統治研究的探索。在這些研究實踐探索的基礎上,侯旭東教授去年出版了一本全面總結個人二十多年來學術思考的專著《什麼是日常統治史》(三聯書店出版)。本次活動即以這本著作為基本研讨書目。
極具反思性的“日常統治史”
侯旭東教授在報告中介紹了日常統治史的基本概念、學術追求和具體思路等方面的内容。
他指出,這本書名為《什麼是日常統治史》,但世上本無作為研究對象或專屬領域、有着明确邊界的“日常統治史”,他實際上想表達的是對曆史上的日常統治進行研究。研究的主語是當下與未來的研究者,思考的是研究者的立場、研究者如何看待過去,包括對既有研究的檢討,以及如何更進一步開展新的研究,具體入手的視角,等等。曆史上的日常統治研究的對象,是開放的,需要當下與未來的研究者們去開發和創造。
“日常”重在“常”不在“日”,針對的是曆史上反複進行的活動(多數是周期性的,如事務性工作:直符、上計、常祀……;也存在無固定周期的重複性活動,如“寵”、候外出行塞、漢代災異的應對)以及固定/不固定兼有的重複性活動(如“蠻夷”的朝貢)及其意義。還可以包括更廣泛的常情、常識、常理、常态等。“常”比社會學關心的“同”範圍要更大,“同”更強調統一性重複。
中國傳統史學強調“常事不書”,關注異常與變化,20世紀以後深受西方的進化論影響,更重視“變”,似乎不變的就沒有什麼可以研究的價值。錢穆先生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裡說“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麼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曆史。曆史之必具變異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觀察生活,感覺曆史,“變”之外,底色和基調是“常”。我們要拓展視野,從重視“變”轉到關注“常”,“常”不僅包括延續,還有反複、循環等等,同時在“常”中再去觀察“變”,觀察“常”與“變”二者的關系。
至于為何用“統治”,而不是更常見的“政治”?那是因為“統治”可以做動詞,暗含了過程性,同時也可以有被動式(被統治),還可以做形容詞用來修飾名詞(如統治者/被統治者、統治方式、統治機制),其内涵更豐富,容得下文明産生後圍繞王朝秩序的各種努力。“統治”可以靈活且充分展現秩序的建立、維持以及統治/被統治—抵抗的關系性,也可以超越以往的獨特事件、缺乏人的制度的思路的局限。“政治”幾乎隻能做名詞,内容要單薄得多,且與現代性關聯更緊密,有礙于對古代王朝統治的全面把握。
曆史上的日常統治研究針對的亦不限于普通人,還包括了統治者,甚至皇帝。日常≠生活,日常≠隻屬于普通人。需要對所有人存在狀态的追問,以及他們的存在如何構成了綿延不絕的過去的追問,結構便是在日常中形成與維持的(慣例)。極端來講,什麼都可以是日常統治史,什麼都可以不是日常統治史,關鍵看研究者如何思考。
曆史上的日常統治研究具體思路有四個方面:主位觀察優先,輔以客位觀察;順時而觀優先,輔以後見之明;日常視角;以人為中心的關系思維。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人為中心的關系思維,希望從對象—研究者固定化的、無意識的關系狀态中解脫出來,發現新的研究空間。以關系思維取代實體思維,那麼1838年至1842年的曆史就不止是鴉片戰争一種解法。如同手裡拿的手機,換個角度觀察,可以說它不是手機:它同時也是一個長方形的物體、一種黑色的物品、一件華為産品、一個照相機、錢包、指南針、鏡子、電腦、電腦……,每種稱呼都包含一種關系,一種與某類其他物品的聯系,取決于觀察者的分類與關注點。研究者其實就是觀察者,可以在不斷的思考中發現研究對象中新的,為過去所忽略的側面,形成新的問題。
曆史上的日常統治研究的提出,包含着對中國傳統史學以及二十世紀初以來的新史學的強烈反思,希望把我們從後見之明中提取出來的重大事件序列研究中解脫出來,發現更為多元的、更為貼近曆史實際的研究空間。
“日常統治史”啟發我們思考些什麼問題
在評議環節,李俊領、劉力耘、呂文浩、胡玉娟等人就“日常統治史”概念的提出以及相關的研究實踐給予學術界同行的啟發提出讨論意見。
李俊領指出,日常統治史将“日常”作為“觀察和認識過去生活的一種方式:貼近人的實際生活本身,從循環反複、例行事務中發現生命的意義、生活的邏輯以及秩序的生成、維系與抵制”(《什麼是日常統治史》第26頁),強調對既有曆史研究方式的“祛魅”“去熟悉化”,刺激我們反思習以為常的知識與事物,考慮如何作更貼近原貌、更逼近真相的曆史認識,“發現更多被遮蔽的世界”。傳統史學有“常事不書”的慣例。作為我們這一代曆史研究者,雖說還生活在傳統中國的曆史延長線上,但對傳統中國政治架構與運作的常識其實并不熟悉。再加上20世紀以來既有曆史研究在研究範式上的局限和現代教育的不足,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青年學者普遍對中國古代史的了解不充分,不深入,明顯存在知識上的斷層。就認識和了解帝制時代中國的曆史而言,《什麼是日常統治史》一書促使我們去深入了解這一時期中國政治的結構、機制及其局限等問題,以“日常統治”為觀察視角,結合侯老師相關實證研究案例,會發現中國傳統政治鮮為人知的面相與機制。他認為侯老師反思既有“事件史”、“制度史”研究的局限,指出“事件”、“事件史”、“事件等級制”的學術話語與學術評價問題,指出“事件等級制”的觀念乃至潛意識不過是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等級制”的觀念映射,此言發人深省。他說,任何一個曆史事件,将其放在不同的事件連續體和邏輯鍊條中去觀察,就會有不同的定位。後人定位的具有标志性意義的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其他諸多事件構成一個連續的整體,這些事件被“切割”出來,也就容易被不自覺地強調或放大。如侯老師所言,“要想恢複鮮活的曆史,回到曆史現場,回到日常世界,恐怕是不得不采取的政策。隻有這樣,我們看到的才不隻是幾條躺在案上待人解剖的死魚,而是流淌的活水及其中活蹦亂跳的鮮魚。”(《什麼是日常統治史》第65頁)這促使我們思考,能否合情合理地了解前人,能否用前人的眼睛觀察他們所在的世界,能否用前人的心靈感受、體驗他們所處的時代。他還認為,日常統治史研究強調曆史研究是要重視英雄人物,但絕不能輕視或無視普通人的力量;不能隻重視大事件的探讨,也要關注小事件的意義,實作二者研究的某種平衡,自覺抵制“後見之明”的誘惑。大事件、大人物的研究都是自帶“流量”,很自然地廣受關注,但關于普通人的研究,尤其是邊緣群體的研究還是少有人在意。從“日常統治史”研究出發,社會史學界對于普通人的研究可以擴大學術視野,發現新的學術增長點。比如,将“日常統治”視角與社會史的“日常生活”視角結合起來。
劉力耘認為侯老師提出“日常”,主要還是以認識論為導向的理論建設,關注的是曆史再現與曆史證據、曆史經驗之間的關系,“日常”是認識“統治”的視角,而不是有一個作為認識對象的“日常統治”。她認為,侯老師在講“日常”這個觀察視角時,特别強調“事”(與制度相對)“小事件”(與大事件相對)“事務”(與事件相對)。這有點像中國哲學史學者楊國榮說的“以事觀之”,用“做事”來統攝作為實在形态的“物”以及人的精神活動和言語行為。侯老師也在書中一些地方提到“做事”(但用“使用”更多),當然這個“事”是跟統治相關的例行性的、重複性的。講到“做事”,必然有主體,“人”就登場了;人在什麼環境裡,憑着什麼經驗,借助什麼或者作用于什麼,為達到什麼目的,結果如何等等,涉及人和人、人和物的關系,而且是動态的、過程性的展現。比如說在傳舍的研究裡,舍、車、馬、食等都是物,從做事的角度,就進入了人的視野,成為人借助或作用的對象;再比如在古人“名”的研究裡,名本來是語言符号,但從做事的角度,是建立從屬關系,還是承擔責任,這就涉及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相比“使用”,“做事”或許是更好的表述,避免對象客體化,而且更能表現實踐性。她認為“日常”視角背後,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的“個體化”取向,曆史研究的對象從結構性的宏大問題轉向個體的經驗與感受,否認了曆史的單一性,強調曆史的多元性和複數特征。但由此也有一個疑問:在大事件上加上小事件,事件上加上事務,實體思維上加上關系思維,制度上加上制度運作,作為曆史主體的國家加上作為曆史主體的人,等等諸如此類1+1的操作以後,還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必要追求一個整體的曆史圖景?此外,她認為,教化是古代儒家理想的、但不止于理念層面的統治方式,而且是多向的,比如有自上而下皇帝教化官員,官員教化百姓;也有自下而上的,官員教化皇帝,而且可能是正常的、例行的,比如經筵,或許也可以納入日常統治史的視野。
呂文浩認為,侯老師近年來關于日常統治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高水準的成果,引起了很多關注,但史學界真正讀懂他的人似乎不是很多。舉例來說,2008年至2010年那幾年,史學界讨論的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是否專制”,這個讨論是由侯老師2008年發在《近代史研究》上的一篇論文引起的,讨論的結果,似乎主流意見傾向于肯定“專制說”,提出這些意見的人對侯老師沒有正面回答他們的意見有點生氣,說侯老師對大家的意見有些“不屑一顧”。他認為,侯老師隻是要反對政治批判式地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是專制或不是專制,用什麼詞彙來概括更好,需要對古代日常統治的生産和維持做出大量具體的研究後才能下判斷;“常事不書”,如果我們從史書上搜集很多例外情況來論證帝王專制,那無疑在方法論上存在“以變代常”的問題。呂文浩認為,侯老師報告中提到的主位優先、順時而觀優先,在史學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啟發,這和韋伯所說的了解社會行動者的主觀意圖也是相通的。我們如果不這樣觀察曆史的話,很容易給曆史當事人賦予我們從後見之明中提煉出來的“曆史使命”,看他們是否知曉或在多大程度上實作了我們所謂的“曆史使命”,這對前人是往往很不公平的。
胡玉娟認為侯老師的“日常統治”研究不同于新文化史的“日常生活”研究,他提出“日常”不等于“生活”,不局限于研究普通人,還包括統治者、甚至皇帝。在她看來,“統治”這個概念也許适合古代中國的政治史叙事,但在古希臘羅馬公民社會,“政治”不隻是“統治者”的日常,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以,她在研究和教學中采用的是“公共日常生活”這個概念,它既包含“普通人”,又包含“統治者”,既是“政治”,又是“生活”。“日常”視角可以打破階級分析法的固有成見,從日常因素發現導緻曆史重大轉折的關鍵原因。以“格拉古改革”為例,由于羅馬公民大會人群擁擠,秩序混亂、聲音嘈雜,提比略·格拉古的演說無法被站在遠處的群眾聽清,他無意中做出的一個手勢,被誤解為“想當國王”,由此招來殺身之禍,導緻了改革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說,“日常”研究就是要求研究者深入曆史場景去發現曆史真相,進而擺脫觀念和成見形成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