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關注“方志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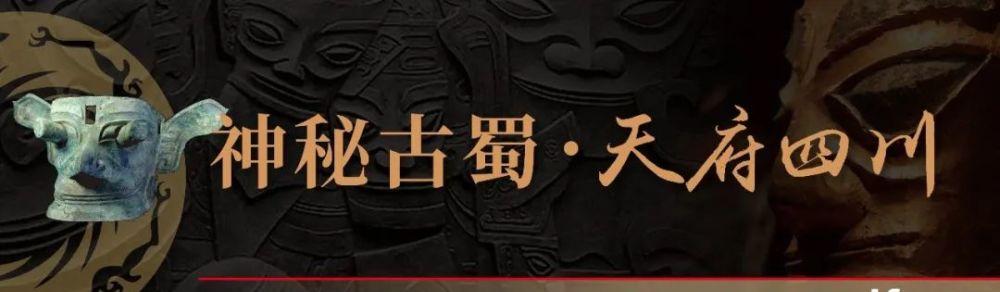
“燎祭”
一場盛大而凄涼的告别儀式
沈迪緻
三星堆目前出土文物,多用于宗教、祭祀活動。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位于1、2号祭祀坑旁。6個相似的祭祀坑,四大兩小,朝向一緻,器物掩埋時間差異明顯,不同坑的器物明顯埋藏于不同時期的土層。
帶來的證據,再次指向“燎祭”。
焚燒,沒有在坑裡進行。器物有規律地擺放在祭祀坑中,有序掩埋。下面,小件;中間,青銅容器和面具;上面,象牙。不像倒垃圾,一種主觀的“故意”行為——祭祀。
三星堆金杖(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宗廟崩塌帶走古蜀國的穩定
三星堆文明,在夏朝滅亡後出現。
神權政體,政教合一。
類似儒家的氏族王權,近乎道家的自然神權。
聯合執政。由辮發、笄發兩個族群。
特征鮮明。3000多年前古蜀國統治階層的縮影。
發型兩種:“辮發”,長長的辮子垂在腦後;“笄發”,頭發卷起,用笄系在腦後。
梳着“笄發”的青銅人像,身着華麗的服飾、頭戴鳥頭冠、下穿鳥足褲,手中緊攥一根神秘的樹枝,常常顯示出神秘的氣息,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儀式中,可能正在從事着宗教活動。
占有神權。控制着古蜀國人的精神,充當着人與神靈聯系的媒介。
梳着“辮發”的青銅人像,神情閑适、安逸。一個世俗的集團,掌握着政治權利。
占據王權。奴役着古蜀國人的身體,驅使他們勞作、征戰。
在對抗自然中,中原人書寫“精衛填海”“愚公移山”“誇父逐日”等故事。
古蜀國,“靈壽華實,草林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和諧的樂土,春耕待秋收,鸾鳥且自歌,居民們怡然自樂其中,自由自在的道家雛形思想開始揮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古蜀文明誕生開始,地域性格就不斷發展、衍化。
“三星堆文明”處于亞北方期,伴以突發性洪水。
在成都平原生活,總是生活在對洪水的恐慌之中。
雖然離開災難頻出的岷江河谷,卻沒能擺脫地震洪水災難的魔咒。
“水瀉盆底”。一次特大地震、一場巨大洪水,就可毀掉一個文明。
沖積扇的平原,左右堆積改變,使得在遷移過程也左右“搖擺”。
磁極倒轉。洪災成為文明中心遷移的潛在動因。
古岷江曾在汶川雁門一帶,穿過光光山,并沿今白水河、湔江,流向沱江。
天不助蜀。距今4000年左右,龍門山一帶突發強烈地震,導緻山崩、滑坡,沿今白水河、湔江,流向沱江的古岷江,在峽谷被堵塞,光光山以下成為斷頭河。堰塞湖湖水上漲,在雁門與汶川縣城間的低矮分水嶺溢出,向西南流向汶川縣城與雜谷腦河交彙,形成今日岷江上遊的水系形态。
“天水傾盆”。夏雨集中,盆地四周高、中間低,迫使水系向盆地中心彙集。沖積扇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遷徙性,經常改道,一旦遭遇頻繁的暴雨,便成水中澤國,生靈塗炭。
《水經注》記載:“漢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
河流改道。原流經三星堆的古岷江枯竭。
今都江堰玉壘山出山口水量,急劇增大。
“三星堆人”賴以生存的河流陡然消失,緻文明衰落。
一場意外,三星堆崩塌的宗廟,帶走古蜀國的穩定。
該向哪裡遷徙?
是“副都”金沙城,還是詩與遠方?
繼續過幸福生活,就該離開。
倉猝、彷徨、猶豫不定,沒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國内部出現劇烈的争吵、對峙,“辮發”的一支族群,要去“副都”定居,“笄發”的一支族群,執意要向中原遷徙。誰也說服不了誰。
一個已經産生階級分化的神權社會。
古蜀王一如那尊“青銅大立人”一樣,不僅擁有超群脫俗的地位,還在祭祀中負責祈福、禱告,集王權和神權于一身,其他貴族隻能在一旁跪着禀告,還有些奴隸隻能打下手。
“青銅大立人”本身頭戴高冠,身穿窄袖與半臂式共3層衣,衣服紋飾繁複精麗,以龍紋為主,輔配鳥紋、蟲紋和目紋等,身佩方格紋帶飾,似乎是具有通天異秉的“祭司”“蜀王”。
受中原文化影響。人面像,又稱“魌頭”。《周禮 夏官》中,就有“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以索室驅疫”的記載。祭祀時戴或使用面具,進行通靈祈禱是中原傳統。
戈形玉器,祭祀中重要的道具。
“三星堆人”溝通天帝的中介物。
聯合執政,意味着平衡。
平衡打破,就會出現問題。
神權、王權,終究不能和平相處,必然分庭抗禮。
異曲同工。商朝早期,一個神職集團決定着蔔筮權,假借鬼神的意志,聚頂國家的方向,被臣民尊敬、信仰,比商王還有權力的統治階層。武丁繼承王位後,王權才慢慢壓過神權。
大同小異。古蜀國與商王朝。
王權、神權,互相依存。
對權利的渴望,注定會讓“兩權”族群爆發沖突。
“夏氏遺族”的“笄發”打破平衡。
三星堆銅跪坐人像(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夏氏遺族”遷徙到成都平原
《尚書》記載:“成湯放桀于南巢。”
《淮南子》說:“湯敗桀於曆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鳴條之戰”中夏桀并未死,在數百精兵護衛下,帶着妹喜等妻妾、追随的“夏氏遺族”,向“南巢”逃竄……
“南巢”,禹夏在成都平原的老家、故地。
《竹書紀年》《帝王世紀》等文獻也說,夏桀主動逃至“巢山”。
《尚書》中《典寶》,今僅存序言。序言說:“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獲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三朡,屬于九夷之族,随夏桀南遷,被商兵追上,奪取寶玉。
宗廟禮器。用玉祭祀神祇,可避免水旱災害,故稱玉為寶玉。
得知消息,商湯派兵一路追殺。
從夏都斟鄩到成都,“婦好”帶兵的追擊路線,從二裡頭南行,越普救關(今河南省汝陽縣王坪鄉),直抵以盤龍城為中心的湖湘地區,溯江至成都平原,并降服沿途氐諸羌部落……
武丁即位時,古蜀國已在成都平原立國350年左右。
安陽殷墟,世界性的大都市。
青銅器、牛、馬、羊、小麥等名額,都已進入世界體系。
三星堆銅鷹形鈴(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文明的豐富性,使得文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富有彈性。
文明中心。成都平原出現早期城市群,原始形态的刻畫文字、青銅器,“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結束,一個植根于社會、又淩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産生。早期的三星堆王國。
擁有強大的力量、遼闊的城域。
武丁時期,甲骨文蔔辭中曾多次提到“蜀”。
彭州出土“覃父癸”“牧正父己”銘文的銅觯。
“至蜀有事”。商軍從武漢盤龍城,追至岷江中遊的武陽(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牧馬鎮、武陽鎮和成都市天府新區黃龍溪鎮一帶),進入古蜀設下的水軍埋伏圈,猝不及防。
商湯聞訊,發出“征蜀”的“伐岷山”令。
《竹書紀年》記載,夏桀“伐岷山”,稱“岷山道”。秦時李冰守蜀,壅江作堋,多得湔氐之力,開建龍溪、娘子嶺,通往冉駹的山道,又稱“冉駹山道”,即後人所稱“松茂古道”。
“巢山”在哪裡?
曆代感念杜宇的詩詞,有上百首之多。
李白、杜牧、李商隐、蘇轼、黃庭堅等,都曾感懷。
曾任成都府安撫使參議等閑職,陸遊在成都7年,常在“巢山”吟詩、垂釣、下棋……寫下《劍南詩稿》和《天彭牡丹譜》。
《劍南詩稿》中,有5首關于巢山的詩,即《巢山》2首和《山居》3首。
《巢山》詩說:“巢山避世紛,身隐萬重雲。”
《山居》詩說:“平生杜宇最相知,遺我巢山一段奇。”
陸遊吟詠的“巢山”,并非合肥巢縣的巢山。
在《天彭牡丹譜》中,陸遊開篇就說:“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一;在蜀,天彭為第一。”“洛花見記于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歐陽修記載的珍異品種不稀奇,成都彭州全部有。
成都官員,在彭州湔江河谷有山居别業。
“悔作東吳萬裡歸”。陸遊堅信自己“前生定蜀人”,稱成都為“吾蜀”,希望在成都終老、長眠。以杜宇自比,也在湔江河谷“海窩子”修“山居”,期許過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彭州至廣漢一帶的湔江,“成湯放桀于南巢”之地,離三星堆很近。
文獻中記載的“南巢”,“夏氏遺族”遷徙到成都平原的聚居地。
夏王朝“南土”的毗鄰區。“南土”,指今南陽、江漢平原、鄂西北一帶。據不完全統計,南陽目前已發現夏文化遺址8處,鄂西北和江漢平原發現夏文化遺址15處……
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大量綠松石,正是來自十堰、襄陽。
地名也是随着人群的遷徙轉移。
跟随夏桀遷徙的“夏氏遺族”,也将中原的一些山名帶入。
《史記》中,岷山皆作汶山。洛陽附近也有汶山。
洛陽的洛河,古稱雒水,三星堆旁的鴨子河,古名正是雒水。
廣漢,一直就有“雒城”之名。
三星堆一帶的“洛”字,在《山海經》中已有記錄。
漢語中記載的“雒城”,西漢時期即已存在。
洛水,亦作雒水。《漢書》廣漢郡雒縣條說:“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與湔江、綿水,同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原洛水應從羅浮山沿着龍泉山,一直流到樂山。“樂”在四川話裡也讀“luo”,沿途頗多帶“luo”音的地名,羅江、雒城。洛水改道涪江,是因大洪水,也或大禹治水,“東别為沱”。
湔江,今又稱青白江,即今流經三星堆遺址旁的鴨子河,古稱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為鄰紐旁對轉,音本相近。《國語》裡的伊水,應視為今三星堆遺址旁鴨子河的古稱。
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成都平原斷斷續續迎來一批批遠方的“親戚”“遊子”,有從祁山道、古陳倉道南下而來,也有逆長江而上、經嘉陵江北上,夏桀在位時的“夏氏遺族”。
同宗同源。共同祖先的古老記憶。
古蜀文明跨出成都平原。大禹率領的“北漂大軍”,懷着對遠方的向往,背井離鄉,于4000多年前,翻過茫茫岷山、龍門山,沿着奔騰的岷江河谷,來到有黃河的河洛地區定居。
大禹世系與古蜀人同出一脈。
商滅夏,直接搗毀一切宗廟、墓葬、宮室、為夏朝歌功頌德的檔案。攻克王城,搗毀一切、寸草不留。那個時代的行為準則。陶寺遺址貴族女子,被石峁人用牛角插入下體,折磨而死。
前朝的“夏氏遺族”,自然要被驅逐、流放。
三星堆銅尊(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帶回中原的政治遺産先進文明
夏朝剩餘勢力除留居中原,分裂成三支。
一支,逃亡到北方荒漠,與當地諸族融合,最後成了威脅中原王朝近2000年的匈奴民族。因與北方民族混血,越來越與中原民族隔離,過上遊牧生活,一直被當作異族,視為死敵。
生活在河套一帶,稱為南匈奴。
留居漠北(又稱嶺北),稱為北匈奴。今俄羅斯、蒙古國、中國、哈薩克斯坦等國。
司馬遷同情這支夏氏遺族,考證出匈奴是夏後氏一支。遇到英明神武的漢武帝,匈奴主力被徹底打殘,消失在北方,成為蒙古人來源,千年後再來,打到歐洲多瑙河邊。
一支,被招安的夏後氏部落,接受商湯冊封,領地在杞。商湯需要這面旗幟,繼續祭祖大禹王,安撫天下,以示道統。
一支,既不去北方,也不留在中原。
繼續往南,追随夏桀,流放到成都平原,做遺民也要保持夏氏貴族姿态,不食商粟。
夏桀已到“南巢”的消息,不胫而走。
有部分族人,沿着長江流域一路往西,一路走,一路散。
多年艱辛跋涉,曆經萬難才到成都平原。
來自“洛陽”的“雒城”。夏桀由洛陽遷往湔江河谷故地“巢山”時,看到三星堆一帶的地形地貌與二裡頭斟鄩出奇相似,就毫不猶豫地在這裡建立了一個行宮。
“越南蜀朝”的首都,稱為“螺城”,螺字古音與“雒”亦頗相近。
“夏氏遺族”本着墾荒,帶來種子和農耕技術。
中原的手工技術,特别是青銅的冶煉鑄造技術。
還帶回大量史料記錄、科技文獻……
按照《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夏桀在位51年,以斟鄩為都31年,“流放南巢”20年。根據對甲骨文的釋讀,夏桀在湔江河谷“南巢”生活的時間更長……
定都三星堆的古蜀國進入全盛。
富裕、安穩的成都平原,吸引不斷南下的“夏氏遺族”。
相當于“海外遊子”,漂泊千年後疲憊的回到“故地”。夏桀在位時的“夏氏遺族”,一支已經融合中原各族生命基因,跟随夏桀遷徙的夏朝遺民,帶回中原的政治遺産、先進文明。
沒有文字記載,主要因時代久遠,夏朝文字成為天書,沒人能看懂。
二裡頭文化中有文字,也有符号,合稱為字元。陶字元在河南一系列遺址均有發現,基本字元形不少于64種。二裡頭文化骨刻字元與陶刻字元之間具有相似性,屬于同一系統文字。
三星堆玉凹刃鑿(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故鄉的古蜀國表示歡迎。
“北漂大軍”後裔的“夏氏遺族”,帶回中原民族神秘、虔誠的祭祀儀式,用青銅為古蜀國鍛造出一種虛無而神秘的力量,被“三星堆人”,虔誠地全盤接受。
讓“夏氏遺族”擔當起古蜀國的巫師“笄發”,取代本土巫師。
祭祀坑中,“辮發”銅像的數量,遠遠超過“笄發”銅像。
數量與權力的分享,聯系不大。
青銅人像中,有4個戴着黃金面罩,代表着兩個階層簽下協定。
青銅時代,青銅固然珍貴,黃金更為貴重。4個青銅人像,代表古蜀國的最高權力。兩個梳“辮發”,兩個梳“笄發”,數量恰相等。制作者在刻意維持兩種力量的平衡。
在出土的一把金杖上,刻着一幅神秘的圖畫:4根羽箭平行射穿兩顆人頭,箭頭分别穿入兩條魚的頭部,箭尾是兩隻展翅的飛鳥。兩顆人頭,代表着梳“笄發”和梳“辮發”兩個階層。
魚和鳥,各自圖騰。
羽箭,相當于誓言。
“辮發”“笄發”刻下的契約,代表着莊嚴和肅穆的誓言。
祭司将“三金”也投入坑中焚燒
一場分道揚镳的“燎祭”。
盛大、闊氣而又凄涼、無奈。
大量砸碎的祭器、絲綢燃燒,文獻裡記載的“燎祭”“瘗埋”。“三星堆人”認為祭祀祖先,需把奉獻的祭品焚燒,神明才能享用,隻有把祭品打碎埋到地裡,才能誠心誠意獻給祖先。
自魚凫王時代起,上至王族,下至庶民,漸漸形成燒祭的祭祀模式。将先人的東西,或器物,以焚燒的方式燒給先人,集中掩埋,進行高規格的祭祀。飄到天空中的煙,便可以被天神聞到;埋入地下的祭品,可以被地下的神摸到。時至今日成都平原城鄉在祭奠去世之人時,還會使用焚燒的方法,傳承時年的“燎祭”。
祭祀時,為彰顯神王的威嚴、營造肅穆的氛圍,大量采用象牙作為祭祀主祭品。
随着青銅器水準逐漸提高,大型牙璋和青銅祭品,才慢慢取代象牙作為主祭品。
國家大事祭祀,古蜀國物産豐饒,“不差錢”。
場景“奢侈”。
臨走時,把放在神殿中的主要神器、祭器,搬到三星堆前的廣場,對着西北方神山中的天神祖先,舉行最後和最大的祭典。佩戴“三金”的祭司主持祭祀活動,命人們将五谷投入坑中,覆寫在玉器、錢貝之上,投入火把進行燃燒。等到坑裡的火焰熄滅,象征王權的各種青銅器進入輸送程式,輸送方法是“摔”。
摔,與焚燒類同。青銅器不易焚燒,将青銅器進行毀損,充分表達祭送的态度。還要奉獻紡織品,将各種紡織品鋪蓋在青銅器上,再一次舉行焚燒儀式。焚燒過程中,祭司手舞足蹈與各方神靈進行溝通,確定過程順利。
有序地埋藏于統一挖的祭祀坑中,表示送到天上和神界。
與此同時,将金庫裡搬出來的象牙投入火中。
象牙,國庫儲備物質。金庫裡,有錢貝、黃金、青銅、象牙。
“三金”,祭司的“标配”。
祭司,人與神對話的翻譯,能聽到神的話,并把神說的事翻譯給人聽,也能将人的話翻譯給神聽,地位僅次于國王。祭司左手拿根金手杖,右手拿黃金“太陽輪”,臉上帶着金面具。
黃金“太陽輪”,古蜀國最進階别的祭祀用品,由太陽、4隻火鳥組成。鳥最接近太陽,是太陽與人之間的聯絡員、火飛到空中聚集一起化成的神靈,4隻火鳥代表東南西北四方天空。
神杖全被黃金包裹,熠熠生輝,上面還刻有鳥、魚、人3組圖案。鳥,天空;魚,地下;人,人間。祭司上通天,下通地,中間通人間。在古蜀國,國王負責管理,祭司負責溝通。
黃金屬于神,由祭司佩戴,青銅屬于國王。黃金太陽輪,代表黑夜中沉睡的太陽,統治人們的精神;青銅太陽輪,代表白天照耀大地的太陽,統治人們的肉身。
青銅太陽輪以“五星”為基本設計格局,鑄造得霸氣十足。
大坑挖好,散發着泥土的味道。
前來的臣民,會從懷裡掏出各種各樣的玉器,有的随身攜帶,有的從家裡帶來,把美玉先抛進坑底,為先祖們帶去一份心意。先是貴族們往坑底奉上美玉,其次是平民往坑裡抛灑貝币。沒有美玉,隻奉上一些錢貝托先王帶給先祖。
待衆人抛完玉器和錢貝,祭祀活動第一輪開始。
等到火焰熄滅,對先祖的祭祀完成。
最後,祭司将自己的“三金”也投入坑中,令衆人回填覆寫……
帶上兵器、日常用品,逐漸往“副都”轉移。
大多數人遷到金沙城,開始“十二橋文化”占統治地位的開明王時期。
小部分人留在三星堆,一直守護着自己的家園。
盛大的祭儀不見,青銅人不見,金玉不見……
留下一片荒涼。
類似的祭祀坑,前後8個以上。
坑口大小不等,祭品多少不一。
獨特的祭祀現象。有點像交接儀式一樣,新王登基或新的一個王朝誕生,會把前一個王朝的東西,從宗廟裡面或是主廟裡面請出,埋進坑裡;然後,自己再造一套,繼續放進宗廟裡面。
以此類推,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連“辮發”“笄發”的“分家”,也同樣如此。
因水而斷。在三星堆前已經消失的還有,新津寶墩城、郫都古城、都江堰芒城、溫江魚凫城等,這5座古城同在成都平原核心地帶,同在岷江中遊,沿江分布,平均距離不超過30公裡。
世界古代文明發展史上“第一黑暗時期”。
毀于一旦。以西亞幼發拉底河、底格裡斯河為代表的兩河流域文明、尼羅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歐洲等地區的古文明,幾乎都在4300年前左右,出現同步的中斷、衰落。
第一輪人類文明瑰麗輝煌的篇章。
戛然而止。宏偉的古城消失。
張冠李戴。公元前1260年,三星堆文明毀滅。在《竹書紀年》中稱為“益幹啟位”,在《左傳》中稱為“後羿代夏”。将神話“後羿射日”的發生地,由河洛之間“轉場”到成都平原。
金沙文明崛起。《竹書紀年》中,稱“夏啟殺益”,《左傳》中,稱“後杼複國”,更是“黑白混淆”,把夏啟繼位、少康複國,“穿越千年”到春秋時期……
維系社會穩定、增強社會凝聚力。
手工業生産服務于宗教信仰,統治階層将社會财富用于祭祀活動。
祭祀告别儀式後,“辮發”與“笄發”分别踏上旅途。
遷移過程中,“辮發”族群遷到成都金沙,“笄發”族群遷入陝西寶雞,“投親”随大禹治水的“北飄大軍”,已在甘肅天水定居的柏灌遺民,這就是周人。
寶雞的一些出土文物,證明與古蜀國的親密關系。
三星堆銅鳥(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建成堪與三星堆媲美的國度
遷到金沙的“辮發”族群,開拓創新,奮發圖強。
如同父與子,一脈相承。
“十二橋文化”,繼“三星堆文化”後,古蜀文明發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
寶墩、三星堆、金沙城,古蜀文明的三部曲。
無縫對接。三星堆被洪水淹沒,政治中心轉移到金沙城。
改朝換代。“副都”變“首都”。
相距不過40多公裡。遷都過程中,聯合執政平衡被打破,“辮發”族群取代“笄發”族群,一家獨大。金沙遺址中,梳着“笄發”的青銅人像不見,隻剩下“辮發”銅像。
真相大白。出土的一條金腰帶上,同樣有人頭、魚、鳥、羽箭。不同的是,人頭圖案卻從兩顆變成了一顆。權力擁有的兩者間,一個消失、衰落,一個成為古蜀國真正的統治者。
王權擁有者們繼續掌握古蜀國的王權,還得到神權。
出土一個小銅立人,梳着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像一樣的辮子,腰間插着一根短杖。頭上戴着象征着太陽的高冠,手卻像青銅大立人一樣無限誇大舉在胸前,依稀有“笄發”銅像的影子。
神權與王權之争,“辮發”勝出。
“辮發”族群遷到金沙,“笄發”族群遷入陝西寶雞。
廢棄“舊都”三星堆,來到“新都”金沙城。
最終成為古蜀國世俗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唯一主宰者,将金沙城重建成一個堪與三星堆媲美的國度;遠上陝南的“笄發”族群,命運多舛,在異國他鄉,必須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銅,甚至是強大的周王朝信任。與已經先到,曾參與過武王伐纣,後又神秘消失的巴人不期而遇。
巴人的發源地在三峽地區,商朝早期就向四方擴充。
向北來到寶雞,向西到成都平原。
向北遷徙的巴人,翻越到陝南的城固、洋縣地區。
被殷商軍隊打敗,又分成兩支。
一支,沿嘉陵江南下,進入長江流域,與三峽西進的巴人會合,進入成都平原,開枝散葉,共同建設三星堆、金沙城。一支,順着嘉陵江北上,到鳳縣一帶暫住,逐漸發展壯大,又翻越秦嶺,在渭水以南的清姜河流域定居。遷徙的路線同故道(周道、陳倉道)一緻。
在渭水河畔,這群頑強的“三星堆人”,建立“弓魚國”。
一個活在過去的“故國”。
對三星堆有着無限追憶、緬懷的王國。
弓魚文化,“三星堆文化”的非典型、不完全延續。
杜宇已進入以農業為主的時代,開明成為拓地千裡的強國。
鼎盛熱鬧。開明王曾先後舉行過兩場重大的祭祀活動。
第一場。在今天的三星堆遺址地舉行,祭祀亡靈,留下1、2号祭祀坑中的一個。《蜀王本紀》所稱的開明,即為繼承三星堆王朝而得,義為“太陽家族”。
第二場。正式遷都成都城西的金沙城,真正的改朝換代,“副都”變成“首都”,進一步确立開明王“一統天下”的地位,舉行一場盛大的祭天儀式,留下1、2号祭祀坑中的另一個。
“複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兩次盛大的祭祀儀式,《左傳》留下了12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