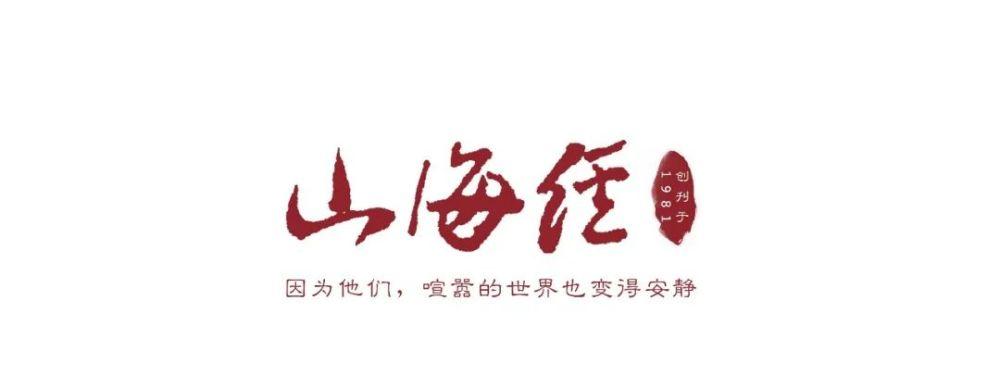
全國各大博物館都有着自己的鎮館之寶,琳琅滿目,精品荟萃。本欄目将為你展示文物背後的故事,揭開塵封的未解之謎。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因避骊姬之難,還未成為晉文公的重耳出逃在外,寄居于秦國。
一天,他的妻子正捧着盛水的匜,倒水侍候他洗手。
重耳洗完後,将濕手随意亂揮,緻使這位夫人惱起火來,她說:“秦國與晉國同等,你憑什麼瞧不起我?”意指重耳瞧不起秦國。
原來,此女是懷嬴,秦穆公的女兒。
重耳經了這麼一通斥責,才想起這位公主的身份,于是心生畏懼,脫去上衣,連連向她請罪求饒。
晉文公
此後,充滿膽識又敢怒敢言的懷嬴被人們銘記于心。
這就是大陸曆史上著名的“一次洗手引發的事故”,由此可見禮儀之邦嚴格的規則典範。
“沃”意為“澆水”,“盥”意為“洗手洗臉”,古代祭祀或宴飨前,皆需行“沃盥之禮”。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同樣是一件用于“沃盥”的器物,也同樣牽扯出一個春秋時期的女子的命運。
1997年,一個流落境外多年、輾轉于古玩店和私藏家的青銅盤,終于來到了上海博物館,這便是子仲姜盤。
它原在晉國土地上與另一件青銅匜相配成套,匜以注水,盤以承水。
可惜的是,它何時與它的原配匜失散已不得而知。
子仲姜盤,這個名字來自于盤的内壁所鑄的銘文“隹六月初吉辛亥/大師作為子仲姜沫/盤孔碩且好/用祈眉壽/子子孫孫永用為寶”。
這些告訴我們,這個青銅盤是春秋時晉國的一位屬官為其夫人仲姜所做的。
而女子姜姓大多來自于姜姓大國齊國,是以學者猜測是一個女子嫁到異國後,收到了來自丈夫的這麼一份禮物,受到了“長壽”和“子孫綿延”的祝福。
與懷嬴不受丈夫重視的命運不同,透過這件鑄工精良、妙趣橫生的器物,我們仿佛可以看見這位女子與心愛之人度過了幸福的一生,她極有可能實作了無數女子的夙願“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
與她惺惺相惜、感情恩愛的人,才會費工夫來鑄如此精美的青銅盤吧?
不同于早期青銅禮器的肅穆與猙獰,這件青銅器造型獨特,顯得尤其靈動與可愛。
攀緣在盤壁,聳出龍首向盤内探水觊觎的曲折角龍,作負重狀的猛虎,還有盤内所飾的魚、蛙、龜、水鳥等31個水生動物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盤内動物排列成五周,淺雕與圓雕相結合,形态各異卻絲毫不覺淩亂。仔細觀察, 立于盤心的雄鳥與外圈四隻雌鳥形态亦有鮮明的差別:雄鳥頭戴羽冠,體型稍大;雌鳥則胸部略鼓,腹部平坦,尾巴更為上翹。
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曾述,春秋早期一般被認為是青銅鑄造技術停滞或退步的時期,但子仲姜盤的鑄造技術,展現了這個時代鮮為人知的新的技術高度。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随着水流傾注于盤中,圓雕動物會順水原地旋轉,仿佛瞬間被賦予了生命一般。後來,人們通過斷層掃描發現,這是因為這些動物内部都配有轉軸來支援其旋轉。
為了使魚與鳥同樣可以進行平穩轉動,工匠将一類轉軸的頂部做成了圓錐狀,尖錐與動物背脊相頂,并留出了活動空隙。
由此可見古代匠人在繼承傳統工藝的基礎上,追求藝術美與工藝精的統一,不偷懶泥古,而是通過技術創新來服務于藝術審美的需求,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此。
子仲姜盤是上海博物館最受歡迎的館藏之一,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銅珍品。
古人構思的精妙以及對意趣的追求在它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緻。
并且,一直到現在,它都牽動着許多人的“少女心”——“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以物載情,曆久彌新。
上海博物館建立于1952年,是一座大型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現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南側黃浦區人民大道201号。館藏文物近102萬件,珍貴文物14萬餘件,其中尤以青銅器、陶瓷器、書法、繪畫為特色。
監制 | 先宏明
編輯 | 于 昕
部分圖檔素材整理自網絡
如有侵權請及時聯系删除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