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葉炜長篇小說《還鄉記》成功入選“2021年度影響力圖書”。這是該書繼入選“文藝聯合書單”和第三季、第四季影響力圖書之後入選的第四個權威業界榜單。作家葉炜,原名劉業偉,是第三屆茅盾文學新人獎獲得者,曾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也是美國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的通路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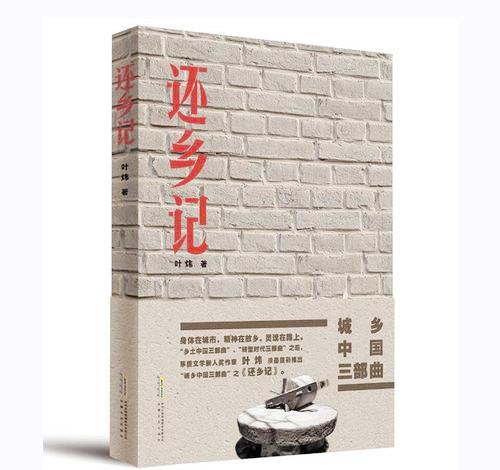
面對當下鄉村的巨變,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無動于衷
談及《還鄉記》這部長篇小說,葉炜表示,早在寫“鄉土中國三部曲”《福地》《富礦》《後土》之時,就有了《還鄉記》的“萌芽”。葉炜當時的想法是,為了接續“鄉土中國三部曲”的寫作,仍以家鄉棗莊的村莊為切片,進一步書寫當代中國魯南鄉村的變化和家鄉人民的精神狀态。随着經濟大發展,今天的中國早已經擺脫“純粹鄉土”的底色,以加速度的方式步入了“城鄉中國”時代。葉炜說:“以我的老家為例,當下的中國魯南鄉村,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帶動下,通過美麗鄉村建設和勞務輸出,已經呈現出城鄉融合的趨勢。”這一趨勢迫切需要新的文學來塑形和升華,講好新時代鄉村故事。
“在我的老家,一個突出的現象是,許多人開始到縣城去買房。随着私家車的普及,很多白天在鄉村小鎮上班的人,晚上駕車回縣城居住。我發現私家車在農村越來越多,多是中低檔車型,有些還是二手車。棗莊二手車交易市場巨大,全國的二手車都向這裡彙集,被當地人戲稱為‘中國三汽’。”葉炜發現了農村之變,于是便萌生了表現這種變化的想法。無論如何,現在的中國鄉村絕對已經不是原來想象中的樣子了。在葉炜長大的小村莊,幾年前就蓋起了小康樓,許多年輕人從老房子裡搬出來,住上了單元樓。原來的村莊也成了嶄新的社群。事實上,葉炜起初将這部長篇小說的名字定為《小康樓》。後來,他考慮到要組成一個新的“城鄉中國三部曲”,後面還有兩部以“記”為名的長篇小說,于是在出版時就改成了《還鄉記》。談及創作《還鄉記》的最大動因,葉炜表示:“面對當下鄉村的巨變,我們這些所謂的作家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無動于衷”。
在“鄉土中國三部曲”(《福地》《富礦》《後土》)和新的“城鄉中國三部曲”之間,利用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訪學創意寫作的時機,葉炜還完成了聚焦新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轉型時代三部曲”(《裂變》《踯躅》《天擇》)。顧名思義,“轉型時代三部曲”,關注的是時代轉型,其中主要寫了“75後”的精神“裂變”和無地彷徨的徘徊“踯躅”以及自我覺醒之後的物競“天擇”。而《還鄉記》作為“城鄉中國三部曲”的第一部,所着眼的正是“鄉土中國三部曲”的百年鄉村書寫和“轉型時代三部曲”的聚焦改革開放精神史的結合,重點觀照從鄉村走出來的“75後”一代人的沉重肉身和精神成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出版社将《還鄉記》定位為“一部反映新中國成立70年來城市和農村的變遷尤其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農業農村農民風貌巨變的長篇小說”是恰當的。對小說的概括“以城市青年趙尋根返鄉為叙述視角,塑造了以農村青年韓慧慧、劉少軍、劉君山為代表的新時代青年農民以及以趙尋根為代表的從鄉村走到城市的‘75後’青年形象”,也是精準的。
至于“小說在反映鄉村振興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透視了中國農村步入小康,農民住進小康樓之後的生活狀态,是一部反映城鄉巨變的史詩性寫作”的說法,則是對這部小說的褒揚與期待了。
“回不去的鄉村,進不去的城市”
時代發展是創作這部小說的主要動因。其實,葉炜之是以要寫這樣一部多少帶有一點兒精神自傳色彩的作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要給自己以及同時代的朋友們一個‘交代’”。
葉炜曾在不同作品和場合中多次談及,“我們這一代1975年以後出生的人,有許多是從小在鄉村長大的,後來因為讀大學等原因才來到城市上學、工作、定居。這一代人的精神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處于一種‘流浪’和‘漂泊’的狀态,或者說得更為極端一點,就是肉身和精神的‘撕裂’。”這一特點簡單概括就是“身體在城市,精神在故鄉,靈魂在路上”。葉炜稱自己的同代人屬于“踯躅”一代。這一代人的成長好像一直處于“中間夾層”,精神一直處于“擠壓”的狀态,而身體則懸浮在半空,如同《踯躅》的題記所說的那樣:“回不去的鄉村,進不去的城市”。
談到這裡,或許讀者已經可以明白,《還鄉記》其實還是一部“75後”作家的精神成長史。
自從離開那個小村莊,“75後”就開始在城市之間“流浪”。以葉炜本人為例,他在曲阜師範大學讀完四年大學,來到位于蘇北徐州的江蘇師範大學工作,工作期間到南京師範大學讀了碩士研究所學生,然後在上海大學讀了創意寫作的文學博士。中間到北京魯迅文學院,讀了兩次青年作家班,在北京前後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這一年還受邀去了美國中西部小城愛荷華,參加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青年項目。時隔不久,博士研究所學生畢業之後他再次到愛荷華大學訪學創意寫作,待了整整一年。兩年前,他到在杭州和桐鄉兩地辦學的浙江傳媒學院工作,同時在中國海洋大學攻讀文化創意方向的博士後。如果再加上先後和東莞文學院、成都文學院等城市文聯的創作簽約,葉炜差不多先後在十幾個城市“生活”“遊走”過。在“遊走”的過程中,雖然也時時刻刻回望故鄉,但總感覺身後的故鄉越來越遠,在精神上有一種莫名的回不去的感慨。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更加無法釋懷,在精神上帶來了進一步的沖擊。因而,意在精神還鄉的《還鄉記》呱呱墜地。
看過“世界”,才能寫好“故鄉”
回到“故鄉”,才能寫好“世界”
從“鄉土中國三部曲”到《還鄉記》,葉炜一直在進行新鄉土寫作的探索和實踐。
2015年“鄉土中國三部曲”出版之時,葉炜在《中華讀書報》的一次訪談中提出“當下中國需要一種新鄉土寫作”的觀點。同時也強調新鄉土寫作是一個開放的概念。從2015年開始,葉炜便以江蘇師範大學長篇小說創作與研究中心的名義面向全國征集新鄉土寫作長篇小說,并在中心主辦的刊物《雨花·中國作家研究》上以“長篇小說大展”方式連續予以刊發,引起了較大反響。随着新鄉土寫作不斷引起關注并成為文學年度主題,這一寫作也漸成熱潮。那麼,新鄉土寫作到底新在哪裡?與傳統的鄉土寫作有何不同?《人民日報·海外版》對新鄉土寫作進行了提煉。
首先,新鄉土寫作所重點關注的對象和傳統鄉土寫作不同。新鄉土寫作側重關注的是當下的中國現實,具體說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當代中國農村。在這一時段,中國鄉村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特點,有抱負、有志向的作家應該對此予以重新發現與觀照。
其次,新鄉土寫作的創作群體和傳統鄉土寫作不同。從事傳統鄉土寫作且依舊活躍在當代文壇的作家多以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作家為主,而有志于新鄉土寫作的作家則以20世紀70年代前後出生的青年作家居多,他們在生活閱曆和精神思想兩個方面都未中斷和中國當代鄉村的聯系,其寫作也越來越呈現出有别于傳統鄉土作家的特點。
最後,在寫作手法方面,新鄉土寫作也與傳統鄉土寫作有顯著差別。從事新鄉土寫作的作家普遍有着較為完善的知識結構,其寫作的寬度廣度以及理論自覺性普遍較高。比如,他們提出并嘗試了超現實主義這一寫作手法,一方面注重和現實的緊密勾連,另一方面又強調對現實主義的超越與遊離在先鋒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之間走出一條新路子。這是對中國鄉土文學的繼承,更是超越。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新鄉土時代必将需要新的鄉土文學。鄉土中國的古老基因已經深入中國人的骨髓,不管你身在鄉村還是都市,都脫不掉鄉土的底色。我們的生命植根于腳下的土地,對鄉土的歌唱就是對生命之根的贊揚,新鄉土寫作是靈魂深處的生命律動。一個作家要寫什麼題材,既是主動的選擇,也是被動的承受。
作為對新鄉土寫作這一概念的補充,葉炜在《看過世界,回到故鄉》中說道:對于文學創作來說,“故鄉”和“世界”是一個辯證的存在。看過“世界”,才能寫好“故鄉”;回到“故鄉”,才能寫好“世界”。換句話說:隻有看過世界,回到故鄉的寫作才能更有底氣;隻有回到故鄉,其寫作才能有世界性的意義。回到故鄉,才知世界之于鄉村的意義。如果沒有新的文學視野,沒有新的思想境界,沒有新的寫作手法,新鄉土寫作就很難稱之為新。隻有有了世界的大悲憫、人類的大通感,新鄉土寫作才可能對已有的鄉村叙事有所超越。寫作者必須回到故鄉,回到自己的紮根處,重新出發,才能讓世界的情感在自己郵票大小的“根據地”落地開花。
從世界與鄉村的意義上來說,寫鄉村并不意味着排斥城市。城市是鄉村的另一面。沒有城市的映照,看不到真實的鄉村。尤其是當下的鄉村,已經和城鎮密切聯系在了一起。未來的新鄉土寫作一定是鄉村和城市逐漸融合。如果說城市是屬于前衛藝術的,是熱鬧和喧嚣的,是音樂中的搖滾樂,美術中的油畫,那麼鄉村則是屬于先鋒文學的,是閑适和安靜的,是音樂中的民歌小調,是美術中的工筆山水和寫意。而新鄉土寫作,則是上述特點的集合。
《還鄉記》是“城鄉中國三部曲”的第一部。目前,葉炜正着手構思寫作第二部。新的作品仍将聚焦新時代中國鄉村,關注“75後”一代人的精神成長,以此作為自己逐漸步入中年寫作的開篇。畢竟,随着時間的推移,年齡的漸長,葉炜這一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已然發生了不易察覺的“巨變”,寫作也面臨着重新出發。
(大衆日報用戶端記者 劉蘭慧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