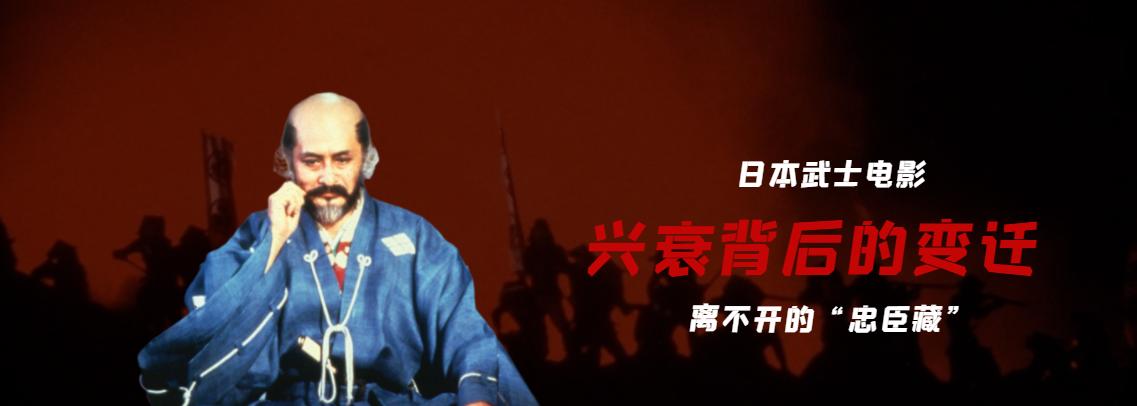
日本社會有一個潛意識規則:
每當面臨國家危機或社會動蕩時,日本文人都會再次掀起"武士"的思想潮流,電影制作人會拿出"忠誠者"的故事進行翻拍。
忠臣藏人,取自德川幕府将軍的真實故事——明仁四十七義人承擔着屈辱的重擔,故事主要為複仇。
故事并不複雜,具有現代美學,其崇高的集體主義與軍事意識形态相沖突,甚至會受到文化學者的強烈批評。
但僅從日本文化的角度來看,《忠藏人》的故事才具有現象層面的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從1928年的《忠心:記錄的忠心西藏》到2010年的《最後的忠藏人》,日本有近80部以"忠心西藏"為主題的電影。
《忠臣藏人》故事成功被日本觀衆認可的關鍵因素在于,它堅持了傳統武士精神的推廣和堅持。
雖然從日本到現代化,明治過後,日本的武士階級正式宣布滅亡,但由于改革本身具有強烈的武士意識和封建殘餘,武士階級雖然消失了,但其對武士精神的信仰并沒有離開。
在日本千年的曆史文化曆程中,"武士道"精神逐漸轉變為日本民族精神的背景,滲透到每個日本人的心中。
在某種程度上,日本觀衆觀看的關于"忠誠者"的電影類似于西方信徒的教堂崇拜,曆史過程賦予了它獨特的文化意義。
<"武士道">h1級""pgc-h-decimal"資料索引的來源</h1>
雖然"武士道"的精神核心起源于孔萌的方式,但根據曆史書,"武士"一詞最早出現在日本奈良時代早期(公元710-784年)。
但嚴格來說,這一次的"武士"沒有"武士"的精神,沒有地位,它的責任是:守護封建領主的莊園,或者聽從領主的訓示入侵其他莊園。
乍一看,似乎與我們中國封建王朝的強力戰士、宅軍有相似之處,但實質上,中國封建王朝的士兵都是以"征兵制"和"育種制度"為基礎的,日本武士地位大多是"繼承制"傳承下來的。
早期武士階級的"繼承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強制行動,是皇帝為鞏固統治、削弱封建領主的影響力而采取的措施。
但是,為了提高封建領主的生産熱情,皇帝肯定了封建主義在土地上的所有權:圈内的人隻對圈内領主負責,無法逃脫封建領主的面積。
這意味着,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農民隻能是農民,木匠隻能是木匠,鐵匠隻能是鐵匠,武士隻能是武士。
在維持封建領主家族統治和發展的初衷下,武士逐漸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集體,成為橫向和縱向強勢家族争奪權力的工具和工具。
在我們的儒家文化中,"忠孝"似乎有聯系,但實際上它隻是字面上的聯系,但在"忠孝"的實踐中卻是不同的。
中國儒家思想要求"忠誠和孝順"對君主制無差别,無條件,絕對從屬。
日本武士的"忠孝"思想是有條件的,是一種基于利益的交換關系。
當日本武士行軍或守衛家園時,君主們可以給家人一些人身安全保障或土地資源。
這裡可以對"北方五代"的記錄進行檢驗:"沒有領土,就沒有必要忠于國王,沒有必要在戰場上放棄自己的生命"
一些戰士還認為,如果戰場奮力拼搏,卻無法證明自己的"貢獻",那麼自己的"死亡"就毫無意義。是以,早期的武士崇尚道德精神,其實是一種不真實的利益關系。
更重要的是,在當時領土經常變化的現實作實中,武士往往隻能選擇"替身"問題,如果站得不對或投機不夠,武士很難保證自己的家庭和财産安全。
但是,由于武士的主要關系往往是世襲的,再加上君主為了武士階層的穩定,與武士建立了"非血緣"聯系的家庭組織形式,這也使得很多武士從"受益"和"現實"也逐漸轉變為"主動"和"規範",當然,這隻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烏托邦, 面對真實的人性,人們往往經不起誘惑和考驗。
< h1級"pgc-h-decimal"資料索引"02">"進化"武士道</h1>
武士團的初衷是維持家族的統治,也就是說,"武士"本身的出現,是中央集權制垮台、封建地産發展的共同産物。
百年戰争,武士們以反複的犧牲和奉獻換取自己的政治地位,鐮倉時代确立了"家庭朝臣制度",武士通過表現和忠誠可以獲得君主的禮物,而這份禮物與過去的口頭協定的從屬關系不同,戰士的忠誠有"制度"和"權威"上的保證。
進入神川幕府時代後,日本進入了一個相對較長的和平時期,原來的武士階級也把和平時期"無所作為"變成了"官僚工商"階級,君主對武士的文化素養也有更高的要求。
是以,武士的社會性在這裡也得到了加強,在"儒家"和"佛教"以及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影響下,日本武士的"武士"精神加強了更多的知識和内容。
然而,武士階級本身在社會中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這也使得一些"學識淵博"的武士向"精英"階級和群衆脫線,但無論是傳統的武士精神還是現代的武士精神,他們都強調的"無私"、"禮儀"、"責任"、"集體"意識具有積極的意義。
武士,在日本長達一個世紀的幕府将軍統治史上,他們的思想意志也傳承至今。雖然人們常說日本社會的等級秩序是森林,企業僵化,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在日本社會下,集團主義的等級秩序,勤奮,謙遜,禮儀,國術,物質衰退,本身就是對日本武士精神的積極肯定。
這些文化的種子最終在後來的日本電影中紮根。
< h1級""pgc-h-decimal"資料索引"03">武士路"</h1>
《中慶藏人》這部電影之是以能被日本觀衆肯定和追捧,是因為每個日本人的背後,都隐藏着武士的影子。它可以對日本觀衆産生很大的吸引力,并具有某種精神淨化效果。
在代表人物黑澤明的指導下,日本的"武士電影"脫離了傳統的武士精神,不再隻是"武士"的精神,在黑澤明的電影中,它賦予了那些"武士"更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文化符号,我們可以用黑澤明的電影來看待同一時期的日本社會生活, 經濟,文化和其他時代變化。
1945年,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豪感在天皇戰敗、天皇倒台、傳統信仰崩潰後達到了極緻。
黑澤明帶來了他的第一部武士電影《踩在老虎尾巴上的男人》,以重振民族自信。
1950年,戰後重建後,日本的民族認同感喪失,文化認同感喪失,整個日本都彌漫着烏雲密布。
黑澤明帶來了他的《羅森門》這部在世界電影史上留下了不少墨迹的電影,通過平安境的一起謀殺案,揭露了複雜的人性和人性的黑暗。
在羅生門的故事中,黑澤爾民對普通人"貶損"武士。
這似乎也是一個隐喻:日本人"菊花與刀"之間的沖突,一方讓他們與傳統相聯系,另一方讓他們不斷擺脫傳統的束縛,最終迷失在過去和未來的迷茫中。我們是強悍還是軟弱?
1954年,當武士歸來時,日本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良好的經濟環境帶來了内在體積的"消費"循環。
黑澤明分别代表着"堅韌、友情、武功、智慧、樂觀、未來、希望",肯定了日本武士的回歸和民族自信的反彈。
1965年,思想危機,文化的喪失,貧富差距。
黑澤明在他的《紅胡子》中,用古老的諷刺意味指出了日本社會的思想沖突,這與當時的幕府時期高度吻合,揭示了那些脫離"火車"脫軌的人的困境,底層生活困難和群體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不安。
1980年,資本很熱,但經濟開始出現危機。
黑澤明還罕見地提出推出他的《暗影戰士》,這部悲劇引用了日本戰國時期的《武田大》,直接指出了日本社會目前潛在"繁榮與蕭條"的風險和可能性。
不幸的是,在那些狂熱的年代不被接受的《影子戰士》花了600萬美元,但票房隻有400萬美元。"一路向上"之後,這個巨大的泡沫完全破滅了。
日本也進入了"失去的十年"。
回顧日本的曆史、電影史、黑澤明的武士電影,我們可以找到:
從曆史上看,日本人留下了武士的鮮血,武士的影子在不同的時代留下了他的印記。
在影片中,武士電影的完善和發展再次強化了日本人民對"武士"的文化認同,而"忠心臣"的故事也在不斷演進,最終在恢複"武士道"的過程中,民族文化遺産變得豐富起來。
這使他們節儉,勤奮,堅強,但沖突,自卑,自我否定......
武士電影就像鏡子,日本人看到自己,看他們的人看到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