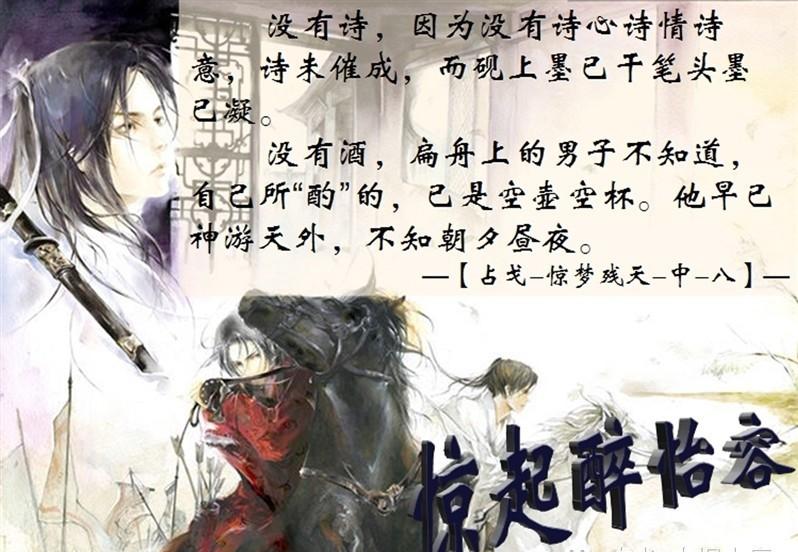
(中:夜長人奈何)
第八次驚慌失措,喝醉又惬意
夜晚的夜晚
- 李偉
昨晚的風雨,
秋天的帷幕正在吱吱作響。
蠟燭殘餘破頻率枕頭,
提升不能是平的。
世界與它一起流動,
數着漂浮的夢想。
醉酒的鄉村道路是穩定的頻率,
此外,這是無法忍受的。
天石精品民宿
白色的話語獨自坐着,在法庭前冥想。
李被溫柔地走了過去,靜靜地坐在一旁。
俞戶野浩然走過院子,懷特在她身後說:"已經半年了,但是有風女的消息嗎?沒有她的山村,好冷!"
嚴戶野浩然搖了搖頭:"蘇丹寄了一封信寄來信,說風女在大理呆了五天,沒能留住她,她起身去追不去,追不住。"
李一一淡淡淡地說道:"師傅的火太大了,但五爺也是一些年輕富貴的人。看到戶野浩漫不經心地看了自己一眼,心裡有些害怕,卻是一個勃艮第的兒子,繼續道:"孩子不應該說師傅不是,而是五師傅是妹妹,為什麼五爺走了,其他四個師傅也不去老師的祖上求愛......"聲音終于越來越低......"
白淼道:"李公子說得很好。沒有風,這裡很冷。你什麼都沒說,就連西瑪伯也裝什麼都沒說。原來你傷害了她,這都是假的!忽然轉過身來,李迎面而來,眼睜睜地看着他滿滿的欣賞,忍不住向他做了個鬼臉。
李遇見她笑得像一朵花,不能說光亮活潑,心跳,忙碌的頭低埋。
闫東諾皓忽然看到兩個人長得不一樣,心裡暗自好笑,也知道北宮千帆出門的事情跟他們不清了,然後說:"我有事要回去,你陪李公子練了一會兒武功,順便可以指點他。"轉身走開,不再被打擾。
"他不把我當老師,他為什麼要指點他?""把臉轉過去,我看到李深深地遇見了自己,他的舉止不耐煩。然後他問他:"你用拱門做什麼?"我甚至可以懶惰地練習自己,但我沒有時間指點你。"
李一一是一個深邃的人,說道:"李一血海深仇,是以下定決心要拜訪師傅,但希望早點學會下山,報仇。女孩願意點,李心有心。"
白淼語這才記起他想報仇的對象是他的父親、哥哥和整個東一幫,心裡突然亂了,又擔心又生氣,對他大喊:"什麼大爸爸讨厭殺了他的妻子?難道你老人不被吓死了,誰會做什麼?你跳下懸崖摔斷了腿,現在你不是了,你還想要什麼?殺人放火,還是用推土機推平人們的土地?"
李立遇見她突然發脾氣,迷惑道:"耿爸爸直,教我做人要公平正直,不能随波逐流,自嘲。這樣一位善良仁慈的老官,卻想到宮廷要給他的住所,享受晚年的好運,卻給山賊們吓得心力衰竭不下去。越是傷心,想想自己跳崖的處境,說道:"父親近幾年連喪親之痛的兒子,五兄妹都超前帶着他的老百姓走了,白發黑發的人已經是人類的悲劇,而中年喪偶,而我還沒有成為一名天才, 他遭受了這種禍害...如果這種仇恨沒有被報道,我在世界上有一張臉?"
白葆美妙的話語忍不住沖了上來,心裡說:"中年喪偶晚年喪子丢了兒子,哼哼,為官司不公此報答,還要到我們頭上算算這個賬?"快要脫口而出的話,看見他臉酸溜溜的,又強力地往後吞了下去。
李某不知道自己的心思,還是恭恭敬敬地說:"李某一體大恨,北宮姑娘和五大主的一般肝膽,為了不相幹的李某某一個正義的幫助。他一天的複仇,一定是女孩去湯火,不後悔!我不知道這個女孩現在要教我什麼。"
雖然生氣,但也很無奈,隻問:"用一個人的力量,你打算如何報複這個'大複仇'?"
"自然是勤奮練習,盡快下山,在東一幫挑戰白心儀式上,大地打敗他。如果他願意做一個行為,不知道要悔改,李會為人民殺人。如果他有悔改的想法,李給他一種生活方式,建議他解散幫派幫派,為宮廷服務,或者把武器遺棄回家,誠實的人!"
他被一條白紙白字的資訊打斷了:"讀聖人的道路!你官公的女婿,茶要伸出手開口,又怎麼知道老百姓辛苦了一年,面朝黃土還天,卻不吃肚子的味道呢?如果你整天吃東西什麼都不做,你會知道,如果人們生了一個體面的女孩,他們會害怕被選入宮中,永遠見不到親人嗎?還要知道,如果一個男孩生來就不傻,那麼擔心被征召入伍打仗,戰死沙場和生死的悲痛?你在宮廷裡滿是義,滿懷憂慮,幾個昏厥的君王入耳?還有多少人因為你的言辭而避免了征兵的災難,征兵的禍害?"
李一一從未聽過這麼"大逆"的語言,心中既害怕又好奇,盯着她的眼睛,聽着她說:"凡想當皇帝的人都說自己是義人,一定是不朽的,人民的軍人會理所當然地用骨腐病嗎?好吧,赢得政府自稱正統,有理由燒掉儒家的書坑;項羽說自己是叛軍,可以燒毀A室宮殿;劉邦說,是兒子的真命,就用正确的話語去殺功勳......都說了很多宏大的道理,老百姓應該活到要經受多年的戰争,更活的妻子離子散戶破碎的人死了,血流進了河白骨堆裡不是嗎?"
白話很少抱怨,因為不屑于酸話,書本讀得不多,隻是走在江湖兩邊,眼睛看,要麼是火是白骨,要麼是心裡恨成骨頭。這樣滔滔不絕的争論是對與錯,是人生中第一次,他們的心,雖然很滑稽,但也很開心。
20多年來,李怡亦是第一次聽人如此"反轉",雖然不同意,但也找不到反駁,看到她如此生氣,怕生氣她,聽完,才輕輕地說:"北宮姑娘,無論如何,堕落成一個co,伏擊,不是總是紳士嗎?這是否意味着在一個混亂的世界裡,有理由做壞事?"
"你父親被殺了嗎?"你被推下懸崖了嗎?你明白盜賊、武林門派和江湖幫的差別嗎?你為什麼要扣小偷的帽子?你真的不知道你父親在任時做了什麼嗎?"
"從我變得理智的那一刻起,父親就教我忠孝,"他說。母親死了,哥哥早死了,父親連再婚的繩子都沒有續約,憑什麼天瞎了眼,讓他受這個禍害?一個人公義也是錯的嗎?"
白淼看到他不知道李成波做了什麼,急切地想說出自己父親的惡行,突然想起了白心的禮貌指令:告訴她不要欺負李,因為它還有正确的精神;心裡既煩惱又無奈,看到他如此盲目自信,不想不理他,轉身就走了。
"北宮姑娘,你...你教了我什麼國術?"
白淼的頭也沒有回答:"跟我進來,我找一本書給你看。要進入上級武道,首先要說的是,心裡沒有憤怒,沒有殺氣,一切都是安全的。另外,将來稱我為"美麗"會很好,每個人都會這樣稱呼我。"
"那麼,這種國術有什麼用呢?"
聽聽後面一個人的話:"武功,是要強骨、懲罰和強奸幫助弱者為主,不為屠殺,不為仇恨。隻是因為世界的美德不同,好壞,必須用武力征服。如果你是一個有德的人,手不碰邊不碰血,我們可以勸說人棄惡,是最好的政策。也可以說,學習國術,是全世界的悲哀也是,是下一個政策!"
是鐘昌藏劍進來了。白淼聽到她這麼說,豎起了大拇指。
鐘昌藏劍朝李辰,一臉莊嚴:"你練武功沒有成功,卻因為你沒有通過三個層次:一是少見世國,都從書本上知道,理所當然的耳朵生氣是危險的,既沒有基礎,又有利于快成, 比如一匹馬倒退而沒有腳踏實地,第三,除了書中的真相,其他知識是有限的,無法整合。之後,不僅要讀聖人的方式,平時不屑一顧的藥學、藥理學等"左路",應該涉獵,不會沾沾自喜,夜郎自大!"
鐘昌藏劍本性輕,不喜歡争執,而且既鑿,又語言無機鋒線,是以最李遇到欽佩。聽她這話,比起白話的極端話,多讓人拿口才。
鐘昌藏劍見心喜悅,隻是說:"到明天的起起落落,當大地為根,以人為本,書為用。從明天開始,你可以學會在山上種花草,以緻因果。一句好話有心,也可以是同學。"
白色的魔術字不這麼認為:"灑水有什麼了不起的,這也想學?"
"你有自知之明,是以你必須知道困難和退縮。很好!"
"别激怒我!"憤怒的白耳語說。這會讓我很難嗎?轉過身來,看到李在眨眼間相遇,看着自己,心裡一團糟,轉過頭來。
"淡淡的秦雲淡淡的日子,新年景象進入中年。
愛更讨厭花無言以對,悲傷的一面知道酒對吧。"
中年人的心,中年的煩惱,真的很喜歡濃烈的酒。
除夕夜,溫暖的春天,年輕的男孩和女孩會開朗起來,伴随着春天的巡回演出。而這種感覺是中年人。
樓上的采石場太白了。獨自一人的女人看着雲層,沉思着。
在平底船頂上,望着她的中年男人,也在自行酌定喝酒,不知道自己的家鄉在哪裡。
沒有詩意,因為沒有詩意的詩意,詩意還沒有被催促進去,墨迹上的墨迹已經幹涸的筆墨被凝結了。
沒有酒,平底船上的男人不知道,自己的"判斷力"已經是空鍋空杯子了。他早已不在天空中,不知道白天和黑夜。
樓上女人們的長袖輕輕一拂,桌上一罐剛開瓶的酒立即飛出"太白的樓房",飛向平底船頭旁邊,短短幾十英尺的距離,卻輕輕一拂,那罐酒就會落在短短的幾下。
"一杯酒,青陽遊行。沒有一個飲酒者喝醉了。中年人不容易喝醉。風也不錯,風景也好,或者,為了愛情——"春風過幾天,各進兩涼"。"
"登上壯觀的世界,浩瀚的河流沒有回歸。一去不去,就是華華的青春!中年婦女看着平底船上的中年男人:他們都開始變老了。無論如何不想面對,白頭的日子終究會到來。
"迷路千裡,茫然無光。在三月,煙花像金子,柳樹像煙霧。心裡的中年男人問道:"這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情緒,她還在擔心什麼呢?或者她在期待什麼?你得等到白發長三千英尺,我們才能手牽手嗎?"
不要說不做,他們從遠處看着對方,然後他們回頭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擔憂。
遠處飄揚的雲朵,獨自流淌的水。馮去台灣空河自流。
于雪平心裡道:"對不起,因為連我都不知道該去哪裡!"
白心敬禮揚辔跄,心裡說:"你為什麼走進去,你對她了解多少?"酒和誰,她?"
他們不必說再見,看着對方,互相交談。
也許這種互相猜測,互相拒絕的誤解,才是他們真正的内心。
夜色寂靜,高樓孤零零。
中年男女如何避免彼此的白心禮儀和雪灘?
孫楚樓.
"月亮沉沒了很久,古人的眼睛很薄。李白一謝,他們呢?
這樣的夜晚這樣的一個月,年輕的男孩和女孩可能會花語言。中年人他們不會,他們隻能環顧四周,說出他在說什麼。
仍然沒有葡萄酒。顧清遠愛酒,但他知道葉薇不愛,是以陪她去喝茶。
當三月的風吹來時,誰是悲傷的春天?- 是悲傷的春天實施,也是苦雨傷害灌木叢。
白心麗因為迷茫迷茫,雪萍不知道該去哪裡。
顧清遠因為自己的知識而迷茫,葉偉知道該去哪裡。
莫名其妙的誤解,了解的了解,結果是一樣的:海員談論大陸,越南語。
葉葉葆想:"萬物向東流淌,過去如潮,怎麼一切又不一樣呢?"
顧清遠歎了口氣:"你敢要什麼?她玩得很開心,你不是很自在嗎?你值得擔心嗎?這些年來你去過哪裡?"
同樣的月夜,一樣的詩歌像風中的一幅畫。年輕人在做什麼?
如果不是老心,心不再年輕,綠絲如雲朵,清澈優雅又有什麼用呢?
蘇州靈岩山,故宮遺址。
西門驿客在祝福中許願:那對死世界,現在能好嗎?西方風沙不小,一個苗條的秀學生,一個弱小的女人,能承受西部地區的反遊嗎?也許,真正的幸福是,他們,曾經在渤海之後,可以成為兒子的手!
高高的鏡子,如最後在細緻地思考:吳王宴會又空了。她在這裡做什麼來哀悼西施?感情?絞刑?這些天她一直很沮喪。雖然快半年了,偶爾看到她的鳳凰笑,眉毛,但為什麼不減少呢?
"天涯占了夢的數量,懷疑有新知識。那麼,她心裡的那個人是誰呢?
真正的寂寞、寂寞,不是一對對未解之人的誤解。
是她擁抱了孤獨的人,是她離開了。
"悠揚的回歸夢想隻有看到,職業生涯的結束隻有葡萄酒知道。月亮就是燈,隻有希峰。
"竹煙銷售皇帝行業是假的","沒有雞狗有烏鴉"。在廬山上方,在燒書坑之前。
鼠尾是鹿劍方形出來,焦尾鋼琴自鳴得意。在陽光下,人們在山上。
在異國他鄉的幾個月裡,她度過了冬天。一個男人,在異國他鄉的山上,沒有同胞,甚至不認識她的人民。因為她變得如此容易。
她為一些她認為很重要的人做了很多事情。一個人這樣做是不想被人知道的。
她自負,為她的智慧、才華、荒謬,她也自卑,為她年輕、淺薄、孤獨。
有沒有一顆心,總是熱血沸騰?隻要對她認為值得的人來說是值得的,就一定有!
有沒有人總是傲慢自大?隻要有她自以為是的意願去走這條路,就一定有!
有沒有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方向?隻要她認為自己配得上傾斜的做,百死不後悔的選擇,一定有!
......
北宮千帆喝着最後一口酒,溫身心靈。由月色鏡子自拍:輕松的臉上沒有裂縫可尋,連她都不知道鏡子裡的人。
她很滿意,收起青銅鏡,開始計劃下一盤棋。
同樣的春風和早晨一樣。又是一波江湖水,獨自一人擁抱着自己的記憶,整夜失眠。
回到呼南山,談笑合歡。生活多麼舒适!
但在這座南山之中,他幾乎無法入睡。沒有詩歌,沒有葡萄酒,沒有喚醒,沒有陶醉。
長安市南,南山盡頭。據該男子說,隻看到滿眼的目光落入英國,看不到彜族人。
北宮的千帆在哪裡?流放的心情,能不能有戲弄的感覺,心裡狹隘?她會是什麼樣子,她會去哪裡,她會在誰身上玩把戲?
如果梅譚不知道到哪裡去找她,不知道為什麼去找她,該對她說什麼,不知道,會在什麼場合看她是什麼。
隻有一種感覺:也許,在某個地方,他和她會路過。也許她變了臉,他認不出來。但他一定會見到她,雖然不知道在哪裡——華山?廬山?廬山?還是說這是南山的末日?
她笑了。毋庸置疑,大自然再次取得了勝利。
廬山決鬥。她質疑"臨沂三少"的霸淩,因為錯了。在昨天之前,他們也生氣了,飛了起來。現在,他們有一隻眼睛,一隻耳朵,一隻缺少三顆門牙。
用過的雙鈎手扶着她的身體,拍拍着身上的灰塵,她很驕傲。丫環在側面擦了擦鈎血迹,也是一張臉。
"四個黑幫老大人,我們從龍泉趕到臨沂,兩場決鬥大獲全勝,又回來了。是時候回到天台山了嗎?我們已經出去三個多月了!"
女人的柳樹眉毛豎了一下,不耐煩地說:"向前看,你不覺得無聊嗎?我也想成為兩兄妹,看到他們真好!Eliu,你認為我們能跟上他們的步伐嗎?"
"好姑娘,你怎麼了?"被叫女孩的伊柳笑着說。給你力量,别人看不了?此外,他們看起來不像壞人!"
"你知道他們從哪裡來嗎?"女人說。景慧門的"金童玉女"朱歌兄妹,身體還不錯。如果你能和他們打架,那真是上瘾了!"
劉毅道:"景惠門的人不是很強,你不惹麻煩。知道要打個招呼國術,不知道就是說是英傑幫挑戰景慧門,"傳劍"萬道如果理論化,怎麼會好呢?"
女人說:"萬宇的心是劍術、劍術、人格孤立的大師。可惜她來找我,但我賺了錢!嗯,不知道她真的有那麼好!"說起來,是英傑幫四大青軒。
易六道:"蘭影,蘭魂上個月你也看到了,'蘭心輝品質'八劍女氣質還不錯,金童玉女氣質非凡,都難以駕馭。你會在主裡惹上麻煩,但我會逃跑,不再跟隨你了!"
她瞪了她一眼,惱怒道:"跟我來兩個月,你怎麼還會這麼弄巧成拙,隻會毀掉自己的威望?"
奕嘀咕道,聲音不小:"買我等你,隻說是跟着做飯來住,卻沒說幫你敲鑼鼓。我不懂打架,要我幫忙,是不是在尋找死亡之道?"
"沒什麼興趣!"于慶軒說:"世上就是因為你們中有些自覺弱小的女性流,欺負女性的臭男會那麼普遍。你自以為是美德,目光短淺,生來就當奴隸!"
伊琉也彬彬有禮地說:"就算你學了打仗,也和奴為奴不一樣?而且一旦學會了幾個花樣,打架的時候,我也要手陪,是不是太長了?"
玉青歎了口氣:"荊慧門,亞環書村裡的毛巾,都面朝江湖,可是我卻随身攜帶了這麼一塊廢品?他一天要看到"心劍"和"仙子五劍",一定要問他們意見,你怎麼能把這種浪費變成人才!"
伊留低隧道:"人們的眼神看人人如手腳,自然人是俊傑;
"越來越大膽!""
伊琉低下頭輕輕撫摸着馬背,歎了口氣:"馬,下一個生來的嬰兒不是男人。哦,可惜!"
于青軒聽了,氣不是,笑不是,哼哼又不理她,在馬背上自理。過了一會兒,忽然按下按鈕一動不動,等着伊琉的馬和自己騎,隻有低矮的隧道:"那個弱小的女人小心翼翼,我們的主仆被土匪盯上了肥羊。我師傅真倒黴,花銀買來你來,也負責你全面發展。羨慕《仙子五劍》真是太好了。"
伊琉笑道:"還有一場戰鬥,姑娘你一定不能孤獨。嗯,雙鈎也是你,我這個小孩子也要靠你來保護,女皓傑?"
她聽着自己的贊美,心裡如火如荼。
果然,澤瑪走了半英裡,與一隊人面對面,大約十七八個人。
其中一位上司,左臂肩并肩袖空空,瘦眼鷹鼻,大約三十五、六歲,在路上遇到了兩個年輕女子,一臉通奸向她們揮手。
伊琉看到這個獨臂男子,眉毛揚起,沉默寡言。
于慶軒把柳樹的眉毛倒過來,一聲細膩的:"誰來,敢擋住姑姑奶的路?"
"嗯,小姓氏。獨臂小偷笑着說:"單鞠躬!
"河湖上有這樣的人物嗎?""餘青玉沉思了一會兒,卻沒有到本質,嘴裡喃喃自語道:"奇怪,一把弓?誰是弓,你怎麼從來沒聽說過這個數字?一鞠躬,一鞠躬!"
奕留露出一絲微笑,還是低着頭,什麼也沒說。
"嗯!弓自然是我!你怎麼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把這一切都說出來了?"獨臂人在天空中大笑。
于清軒已經陷入了迷霧之中,嘴裡還在重複着自己的名字。看到獨臂人笑着雨夾雪,忽然想起鞠躬這個詞是"公平"諧波,他們反複閱讀這些時候,已經對方要求便宜了。在憤怒的心中,政策立即走,雙鈎面對面,滿懷以為對方沒有被她掃過,也會被吓到立即摔倒,這知道了,卻撲上了空虛。
一雙雙眼睛的固定眼睛,單臂男子輕輕地閃過,依然是一張面不雅,卻毫發無損。于清軒心裡略顯驚訝,知道打了一個兇狠的敵人,深吸一口丹田氣,揮動勾再掃。不知道另一邊左臂空着袖子,但輕描淡寫地掃了一下,就會是她的雙手張開,而且力不小,震撼着她的頭發。
獨臂男人嘴邊的笑容:弓最愛美女,怎麼願意欺負你?你罵弓,打弓,心自然,親近和愛。唉,弓的心可以很美!"
一聲怒吼,跳出馬,雙鈎出,用十個成功的力量掃地而去。獨臂男人看到她的聲音不小,不敢慢下來,一邊笑,一邊也跳下馬,躲避她的打,甚至歎了口氣:"打得那麼狠,愛情弓一定是死的才能活下去。哈哈哈!"把一隻拽着的手放在她的頭上,拉出一個發型。
空氣已經耗盡,幾乎暈倒在繩結下。走幾步,如果你無法保持力量,就會摔倒。
獨臂人笑道:"鞠躬是心痛,不要摔倒!否則,我必須把你抱進洞穴房間!"
在伊琉的身邊,馬匹已經被十幾個人包圍着,不敢動。她在戰鬥中環顧四周,顫抖道:"這個女孩今天心情很好,不......不啟動殺戮戒指,你不滾?""
伊琉走向十幾個男人,拉着嗓子喊道:"不要等到阿姨和奶奶開槍才後悔,你真的可以......真是不知悔改!"
獨臂男人一邊想着便宜一邊躲閃,一邊笑道:"啊喲,大美夠熱,小美人好好鑽,弓喜歡!唉,弓的祝福真的不淺!"
香味出汗,過度的體力消耗,邊緣幾乎昏厥。
馬吓壞了,易劉驚呼地把馬放下,露出眼鏡,伸出手,碰巧撞到了一個男人的小腿。在大驚訝的纖維手腕縮回,看到邊緣的血迹,伊琉被叫到地上,抱着老鼠的頭跑。頭也不敢擡起臉跑,"乒乓"一聲響,又一人打了一個正,柳樹的力量不小,雖然被撞倒了,對方居然倒在了地上。她摔倒了,反手撐着,想坐起來,突然聽到一聲叫喊,但她的手上的匕首卻不小心了一個人的背上。
舉起手來,柳樹在地上滾了一圈,運氣不好,"咕噜咕噜"滾到一個人的腳下,一腳踢的動作,那人絆倒了一腳跟,在天上掉了下來。巧合的是,她的另一隻腳不經意間掃了一下,一塊石頭被腳趾頭卷了出來,就在男人腦袋的後部觸碰,男人的後腦沉重,立刻暈倒了。
她筋疲力盡,沒有時間轉過他的臉去看。獨臂男子稍稍瞥了一眼,但臉上卻充滿了驚訝。當我把目光轉回去的時候,我看到于清璇已經搖搖欲墜,心裡快樂,左袖揮舞着,雙手用雙鈎卷起,上去抱住她。
"小姐!易劉大匆匆,不顧自身安危,都會用匕首的手向他扔去,他微微側頭閃過,正想取笑,要了幾句便宜的話,忽然瞥見了匕首上的八滴水,一動心,轉身對易劉道: "你是什麼,怎麼會有'八把仙女匕首'?""
伊琉低聲說,正試圖撲向獨臂男子打架。忽然看到他後退了幾步,臉上是綠色的,汗流浃背,然後不再無視他,跑上前去扶清奇,主仆兩個人摔倒在地上一起坐下。
快樂低矮的隧道的底色:"有幫手!"心寬,倚在埃柳的懷裡無法呼吸。
伊玥擡起頭,确實看到一男一女劍拔了出來,剛才是他們的主仆兩個人在談兄弟姐妹。然而,十幾個花樣,看到十幾個男人沒有帶子剪掉,或者頭發被剪掉一團,長袖被剪掉一幅畫,沒有感受到心中的喜悅,單臂男人的感覺不是對手的兄弟姐妹。
轉過臉來,隻見單臂男子緩緩後退,臉上滿是恐懼,仿佛要面對一些兇狠的敵人。好奇地低下眼睛,我看到一個年輕人慢慢地向他走來。這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粗布,大耳朵,劍眉,雖然沉默,動作緩慢,但有自己的強迫精神;伊琉隻是看了他一眼,然後低下頭,唇出一個笑容,非常感激。
獨臂人突然必須,動起來也不敢再動了,但年輕人還站着,不再往前走,會當場害怕他,不敢多說。
朱歌兄妹一邊,已經數在送了十幾個人留下的印記,讓他們自己逃走,相對一笑,然後就沒追上去。
年輕人冷冷地說:"還記得我嗎?"
"驚喜破風雲——梅仿佛?""
諸格菊鑒朗頻道:"先是董公子和嫂子割破了他的手指,然後自作自斷了左臂,在小野,這次你想留下什麼?"梅先生,我們離開他的頭還是腳?"
餘梅如真道明:"小野俞,你選擇屬于自己!"
諸葛一毅還說:"如果家裡不和人打架消耗能量,你怎麼能看到眼睛裡的老鼠那一代呢?""
他微笑着轉過臉。
餘小野臉像死灰一樣,忽然道:"四家的時候,嗯,四家的英傑幫!英傑幫和景惠門、少林寺沒有友誼,三人如何聯手?"
"五月不是為了取悅英傑團夥,更何況他們是需要男性保護的女人,隻是沖着趁着這個人的危險,對衆無恥的瞞乖,然後治好你一個藥!"是你自己做,還是我做?"
他沒有嘲笑自己是一支戰敗的軍隊,更沒有蔑視她們是女人的事實,忍不住暗暗點了點頭。
易劉一側的目光,卻看到他站得像一座山,浩然積極,還有唇角的笑聲,暗自欣賞。
小野羽知道并走過了麥城,也知道少林寺、景惠門、毛巾等山,都不容易殺,活在一起,腳趾踢起一把長刀,右手抓着,咬牙緊閉着眼睛,在小腿上揮手,立刻看到血直流,疼痛自己蒼白,直起冷汗。看到三人不再勢不可擋,他們一瘸一拐地騎在馬背上,在黑暗中逃走了。
于清軒心無後顧之憂,而隻是一場惡狠手,一直憤怒的心,累了,頭歪歪扭扭,暈倒在伊琉的懷裡。
(請注意)在《張高小說》中,《夢日》(九):思考在哪裡
在張高的小說《做夢的日子》(七):月亮建築中的長笛
在張高的小說中,《夢見殘餘》(九):在哪裡思考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