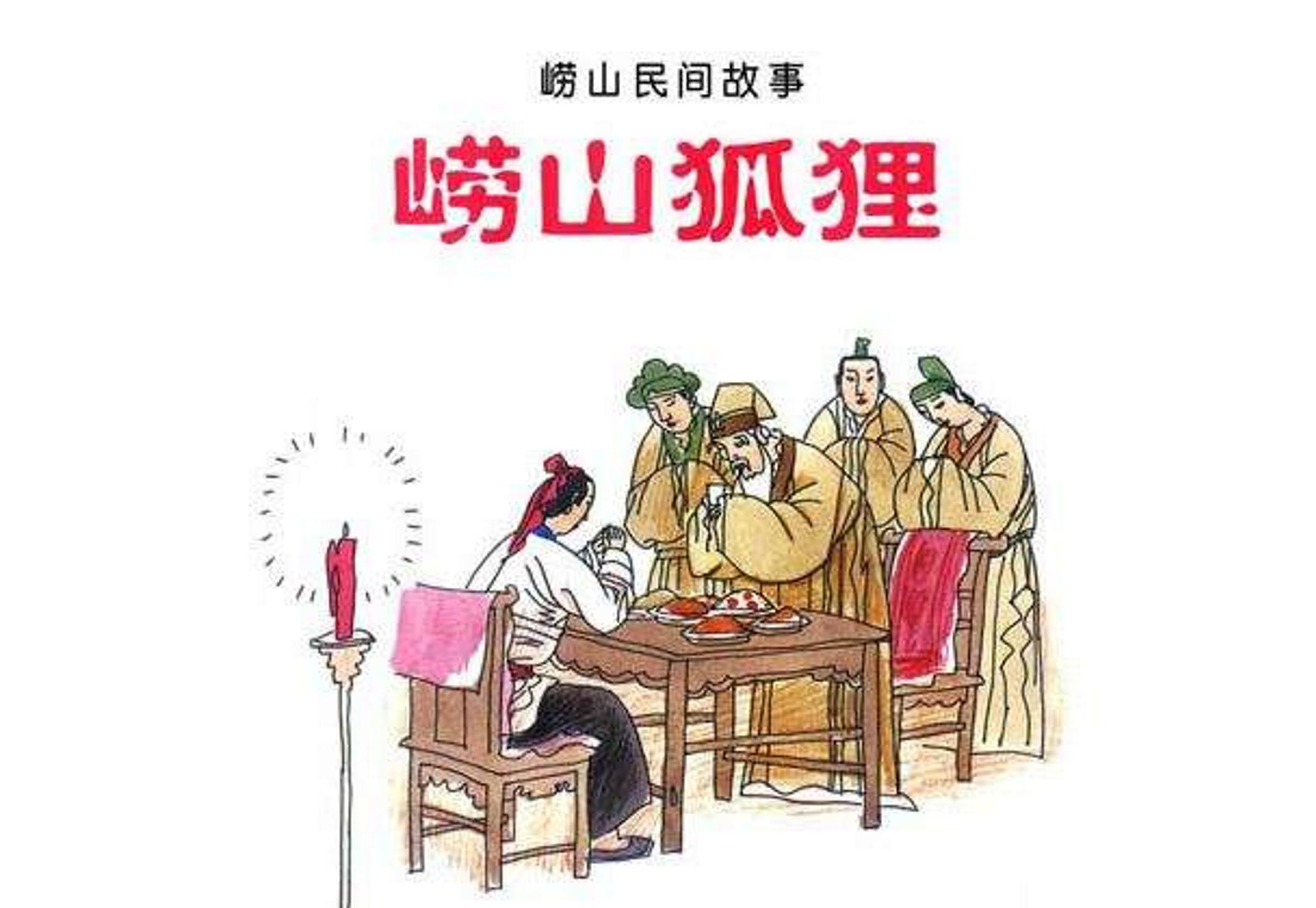| 一、起 狐仙,又名狐妖、狐精,大約宋元以後俗稱為狐狸精。傳說大禹三十歲那年,在塗山遇到塗山氏之女,兩情相悅,結為夫妻。塗山氏首領臯陶,是大禹治水的有力支援者。上古神話傳說中,夏族的始祖神為塗山氏,塗山氏的崇拜圖騰是九尾狐,傳說大禹之妻是九尾白狐化身,生下了啟,啟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 《山海經》:“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德至乃來。” 《周易·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 《詩經》中的《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禮記·檀弓上》:“狐死正丘首,仁也。” 《尹文子》記載狐假虎威的故事,狐惑虎,小菜一碟。 《史記·陳涉世家》記載吳廣學狐鳴的故事,足見秦朝民間狐神崇拜的情況。 《焦氏易林》的《睽》之《升》:“老狐屈尾,東西為鬼,病我長女,哭涕拙指。”《萃》之《既濟》:“老狐多态,行為蠱怪,驚我主母,終無疚悔。” 《說文解字》:“狐,龍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後丘首。” 關于狐的形象,至少在西漢以前,在民間已有相當的傳說和記載。傳說中的圖騰狐神,現實生活中的狐狸,幻變人形的狐精,狐的世界開始豐富起來。 至魏晉六朝,狐的形象開始轉變。幹寶《搜神記》中,多言老狐、老狸化為人形作怪的故事,狐為狐,狸為狸,未見狐狸一詞。現在看來狐是犬科,狸是貓科,根本就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兩者相似處是都捉老鼠,古代有城狐社鼠之說,狸是山貓、野貓,和鼠的關系自不必多言。陶淵明《搜神後記》中,隻有幾則狐精故事,而沒有狸精故事。連郭璞也認為狐妖實有,可見當時文人大多喜談狐狸。 唐朝張鹫《朝野佥載》:“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 唐朝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啟宋、明、清初志怪小說的重要著作,全書20卷,續集10卷,所記分類編錄,一部分内容屬志怪傳奇類,另一部分記錄各地與異域的珍奇異物。有一篇講到狐媚:“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極數則天過惡,則天覽及‘峨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女人狐媚,微笑而已。 宋朝《太平廣記》引郭璞《玄中記》:“狐五十歲,能變代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裡外事,善蠱惑,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則與天通,為天狐。”《太平廣記》是一部大書,12位作者奉宋太宗之命編纂,全書500卷,狐精的故事有9卷,以志怪小說為多,可說是宋朝以前的小說總選集。洪邁的《容齋随筆》,也言及狐精的故事。 明、清初志怪小說,狐精、狐仙故事蔚為壯觀,《三遂平妖傳》、《封神演義》多言狐事,至清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包羅萬象,纏綿悱恻,狐仙故事達到巅峰。狐神澆漓,穿越叢林,念書修道,化為人形,亦正亦邪,來到人間矣。《聊齋志異》之後,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記有狐故事200餘則,魯迅先生評說:“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隽思妙語,時足解頤。” 二、承 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号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自稱異史氏,山東淄川蒲家莊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逝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生熱衷科舉,卻始終不得志,71歲時才破例補為貢生。他畢生精力完成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共8卷491篇約40萬字,故事多采用民間傳說和野史轶聞,将花狐鬼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情節幻異跌宕,文筆簡練通達,結構井然有序,被譽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 蒲松齡在1672年4月遊覽過崂山,住太清宮,後來寫了名篇《崂山道士》、《香玉》。蒲松齡對狐仙情有獨鐘,為什麼沒寫過崂山的狐仙呢,這似乎是一個謎。當時崂山盛拜狐仙,有一個傳奇人物胡峄陽,人稱胡三太爺,也稱狐三太爺,與崂山狐仙有很神秘的關系。 胡峄陽,名良相,字峄陽,青島城陽流亭人,約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逝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終生不做官,以教書授徒為業。胡峄陽生有異禀,精研《周易》,與崂山百福庵蔣清山道長相交甚密。著有《易象授蒙》、《易經征實》、《解指蒙圖說》、《柳溪碎語》、《寒夜集》等,現僅有《易象授蒙》和《柳溪碎語》,喜愛山水,常遊崂山,多住狐仙山洞,亦儒亦仙,是為易學大家。 蔣清山,字雲石,又名蔣迪南,号煙霞散人,江南人。一說曾任河南祥符縣知縣,明亡後不願繼續為官,于清順治二年(1645年)至百佛庵隐居。蔣清山修真養性,行誼高潔,士大夫皆雅重之,與理學名儒胡峄陽是契友,與隐居崂山的萊陽名士孫笃先為至交。蔣清山一生緻力于重建百福庵,明亡後,養豔姬、蔺婉玉等四名宮女随邊永清逃至崂山,得蔣清山之助,得以到百福庵出家靜修,精心研究道樂。蔣清山酷愛書籍,于百福庵中藏有大量經典書籍,時稱“蔣迪南書院”。 據說蔣道長與蒲松齡相識,蒲松齡是否略曉胡峄陽的傳奇轶事,也未詳知。但知一理學名儒,遊崂山而常住狐仙山洞,一住就是幾天,不得而解。傳說胡峄陽常住的寂光洞旁,在胡先生逝世後,有了一個狐狸的墳墓。我想,這一定是個崂山狐狸,狐仙乎,狐精乎,狐神乎,也未詳知。但凡每年的正月初八,說是狐仙生日,山民多拜之,以求祥瑞。 胡峄陽學貫儒、道、釋,留下的奇聞逸事甚多。清《膠州志》載:靈山東南海中有鼓子洋,有人在此遇一駕舟老人,芒履道服,貌甚古,雲“即墨有道學先生胡峄陽,為吾通一問訊。”該人歸後對胡面陳此事,胡撫然曰:“此三國時徐庶也,隐居鼓子洋久矣!” 清黃肇鄂《崂山續志》雲:乾隆戍午冬,海上漁者數人,至流亭訪胡映黎。映黎者,光乙名也(峄陽子),漁者曰:“日下海遇風,筏随浪去,一晝夜不知幾千裡。忽抵一島,島中百花盛開,暖如春;有洞穴,無室廬,一石平如砥方丈餘,曬丹棗滿之。棗大如雞卵,有老人坐其旁,貌甚清古。與之語不答;告以饑,人與一棗,食之腹果然。既曰:“東南風起矣,可速去。”叩問姓名,老人曰:“識流亭否?”曰:“知之。”老人曰:“吾故裡也。歸語胡映黎,好為人,若翁在仙島甚樂”老人說自己是流亭人,并讓漁人回去後轉告其子“好為人,若翁在仙島甚樂。”衆乘風返棹,翌日抵家,不覺饑也。三日後,至流亭。時先生殁四十年矣,衆人駭然,拜木主而去。殆所謂仙風欤。 既有仙風道骨,又有洞穴,而無室廬,也是奇哉。另有傳說,胡峄陽多次預知洪水,但不明言,隻由細心人旁觀體會。《搜神記》有篇故事:“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雲:‘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鼹鼠。’客遂化為老狸。”古人以為狐、狸同屬,胡峄陽熟知雨情,喜住洞穴,當對狐仙之道深解。 三、轉 胡峄陽有句名言至今被人傳誦:“大難不難,大艱不艱,千難萬難,莫離崂山。”崂山風骨,地接海陸,主峰崂頂也稱巨峰,為中國18000公裡海岸線上的最高峰,方圓面積400多平方公裡,群峰幽谷,奇花異草,天池冰臼,山高水長。更有古冰川遺迹遍布,花崗岩石穿土入海,巍然屹立,通達海陸,似有連山歸藏之磁力,山海奇觀,神峻靈秀。 今年8月7日上午,據說60年不遇的九号台風梅花,可能在青島沿海登陸,那天上午10點多,我帶攀上海拔710多米的大流頂主峰,隻見狂風呼号,烏雲翻滾,濃霧飛奔,雨滴如珠,梅花前鋒在大流頂、雞石山、會仙山、天茶頂一線被阻攔,後有崂頂雄峙。一面是叢林濤聲漫天而動,一面卻了無風潮隻有濃霧細雨,當時感覺,崂山群峰确有神奇之處。而且大流頂幾處大小冰臼,都儲滿了清水,也不知那些清水是怎麼來的。我想,可能這是崂山山神内有的水勢吧。後來,梅花台風驟然減弱,也不知轉到哪裡去了。此一奇也。 兩年前的正月間,雪映山林,我随竹竿隊衆山友野爬,至天地官财石途中我帶隊,見雪地中有一段獸蹄印迹,有幾十米遠,不知所來,不知所歸,突然就消失了。有山友說,可能崂山有一種會飛的走獸,偶然把腳印留下一段。又有山友說,可能有會跳躍的大獸,走一段雪地又跳走了。我有疑惑,無從得解,隻拍了幾張手迹的照片。 大隊人馬在眺望天官石前野餐後下山,我與尚志辭别大隊,踏雪穿林,欲往天官石方向探路。繞來繞去良久,至一露天山洞,怕迷路,留寫“洞天”兩字。再上行,至山梁闊處。尚志驚呼,好像有個人從松樹上跳下來,把樹枝都刮斷了。我走上前去一看,啥也沒有。我笑說,可能是個大山貓吧。當時心裡也後怕,要不是這個人,難道是别的啥嗎。我對尚志說,别探路了,今天蹊跷,趕緊下山。不想走着走着,不見了尚志。大呼。尚志回應,我趕上去看到尚志,大喊,走錯了,趕緊從這邊下山。當時我覺得,他似乎被那個山貓啥的引去相反的方向了。那時我還沒想到狐仙啥的,這時想來,也許那可能是傳說中的崂山狐仙吧。 聽崂山山民說,崂山中有的狐狸确實能迷惑人,它們口有狐香,單人活動時聞之則迷,宛若夢遊一般,待所迷之人昏睡時,狐狸會以嘴舌添人面頰,吸吮被迷人的唾液。被迷途中,要是有個溝崖深谷的一跌,那就慘了。當然這樣的狐狸未幻人形,隻以氣味相誘,是以多人在白天結伴行走,還是安全的。 前幾天周六爬山,适逢啤酒節第一天,我們在蝴蝶泉河谷吃午餐,品酒,品茶。聽隊友羅漢大哥說,前年冬天,他辦了年卡獨自上崂頂。那天隻有他一個人乘旅遊車到天地淳和,然後獨自上山。良久,後面有一老漢追來。老漢說他76歲了,從台東騎自行車到天地淳和,老漢說一定到崂頂拍張照片,回去向小崽子們證明老爺子上崂頂了。那天羅漢大哥未帶飯,以為景區有賣的,不想崂頂景區根本沒有賣東西的,前後隻有他和老漢。他問老漢帶吃的沒有。老漢從尼龍綢包内拿出四個很小的面餅說,隻能給他一個吃,因為老漢還要從天地淳和騎自行車回台東。 後來,老漢和他到靈旗峰後獨自傳回,他一人去了丹爐峰、杜鵑坡,之後開始腿痛,傳回天地淳和時天色已黑,旅遊車沒有了,他按年卡上的電話打去,山下專派一輛車将他接下山去。随後猜想,那老漢确實神奇,人乎,仙乎,幻形乎,不得而知。 若說崂山狐狸,一次我從崂頂下山,下午經磚塔嶺舊村時,确實見過一隻白毛狐狸,隻是白狐從我眼前一晃,我想拿相機拍照時,白狐不見了。聽山民說,千年狐黑,萬年狐白。我想崂山已是神奇,千年萬年的,狐啊仙的,也許是一種隐喻吧。若說崂山狐仙,可能早已修化為人,或放浪于市井,或混迹在山友之間了吧。 四、合 中國古代有月神崇拜,春季祭日,秋季祭月,古人對月亮的崇拜,最早記載見于《尚書·堯典》,《太平廣記》中有群仙拜月的故事,元朝大戲劇家關漢卿寫過一出《拜月亭》的劇本。 同樣,古時候也有狐狸拜月之說,《酉陽雜俎》寫:“舊說:野狐名阿紫,夜擊尾火出;将為怪,必戴髑髅拜北鬥,髑髅不墜,則化為人。”馮夢龍借鑒狐變人的說法,在《平妖傳》第三回中增設了“拜月”儀式,特别點明狐拜月是在九月初八。 《聊齋志異》記載:“有狐在月下,昂首望天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月中,一吸,辄複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似在拜月,似在修煉,小說氣息濃郁。 錢鐘書《管錐編》寫:唐時有一俗說,後世無傳,餘讀唐詩得之。(引詩略)然則狐仙拜月,多不在中秋矣。傳說,胡峄陽的生日是正月初八,狐仙的生日農是正月初八,佛誕日是四月初八,王洛賓寫過一首民歌《半個月亮爬上來》。農曆初八,正好有半個月亮,看來狐仙所拜,是在月半之夜。狐仙,介于人和獸之間,與人相比,同有動物的屬性,同有感情的升華,一個月亮,你拜十五,我拜初八,上弦月月半趨圓,月亮朔望,自然而然。 有人說,崂山文化也是狐仙文化,感覺有一定道理。狐者狐也,人者人也,仙神鬼道者仙神鬼道也,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崂山神秀無奇不有,東海叢林,竟無歸乎。隻是,物心觀點業已穩存,神秘猜測或有動念,因詩情乎,因文學乎,因狐仙千嬌百媚乎,細微之處難說了。 若有狐仙,或者若有狐仙之隐念幻覺,時代在變化發展中,工業文明至資訊網絡文明,狐仙能無變化适應乎。若有狐仙,當然也必定已進入資訊網絡文明了。傳說胡峄陽在三百多年前,見村民點蠟燭感言,将來都要倒過來,匪夷所思,可能是真也可能是托說。時間是人類最主要的線索,曆史也是,現在也是,未來也是,未來之來,時間而已,什麼不是呢。 古人雲,萬物有靈。曆經千百萬年,靈有變乎有無變乎,有也無也。竊以為,物種流延,或有摻雜,多少而已,顯則顯之,隐則隐之,不一而論。理性原則是理性原則,神秘觀念是神秘觀念。胡峄陽以理學大儒起發,又融入狐仙傳奇,山川地理,海陸對接,亦儒亦仙,亦釋亦道,感歎之。 野爬崂山多年,遇物則物,遇心則心,怎想物已止而心漫動,物心之間隙,情何以堪。莫非于山野行走,沾染了狐仙遺留的異香,莫非在市井逗留,又被幻形的狐仙相誘。好在這隻是一個傳說,傳說之後是詩意的遺忘。 傳說中的崂山狐仙,是怎樣的,傳說中的胡三太爺,又是如何。我想,胡三太爺可能就是狐仙,他是狐仙中出類拔萃的儒者,他有一個紅顔知己的狐仙,紅顔知己随他而來,又随他而去。甚至,胡峄陽和4000年前的大禹一樣,或顯或隐,都做過狐仙家族的上門女婿。大禹治水創造了曆史,他的老婆來自一個崇拜狐仙的部落,大禹是大禹。胡峄陽神遊崂山,留下與紅顔狐仙的千古佳話,胡峄陽是胡峄陽。 蒲松齡與胡峄陽,是狐仙文化的兩座高峰。蒲松齡在文學,搦筆生花,胡峄陽在易學,身體力行,蒲松齡在齊魯之野,胡峄陽在崂山之巅。狐仙文化,是中華隐形文化和民間崇拜中的重要部分,民間信仰之善美,道德出入之基本。狐之仙之,人之物之,凡者随波,俗者逐流,靈神無端,仙形萬象,大道無形而殊途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