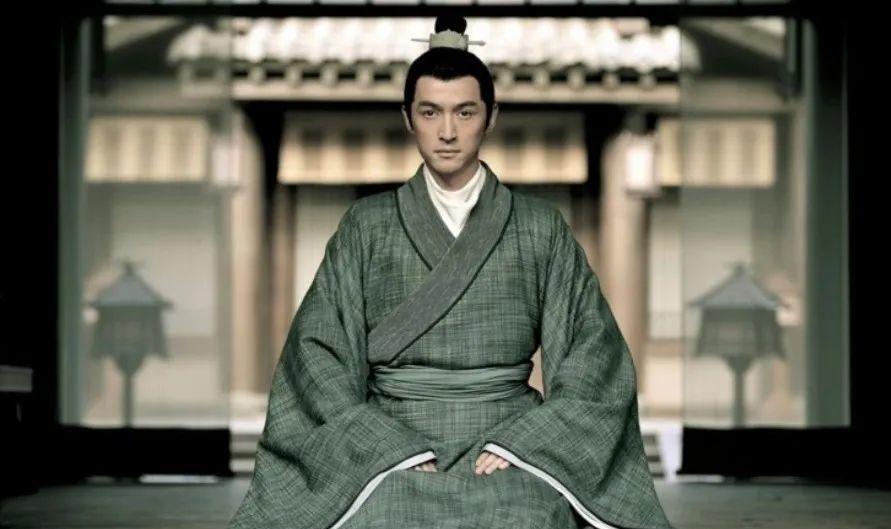
西晉:
一個有錢就是爺的王朝,一個被奢靡侵蝕的王朝。
前期類似東漢桓靈時期,後期變成北宋靖康年間。
前期的西晉經過漢末三國的折騰。
在晉武帝司馬炎的勵精圖治下,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也曾看到“太康之治”的盛世苗頭。
也僅僅是盛世黎明前的黑夜,結果晉朝立刻得意忘形,重新回到東漢桓帝與靈帝時期的樣子。
後期的西晉經過八王之亂的折騰,在與匈奴的交手中,敗的一塌糊塗。
最終,司馬睿攜全家老小南渡江南,與兩宋時期的建炎南渡驚人相似。
站在曆史的軸線上,遙望1700年前的西晉。
嵇康撫琴、劉伶醉酒、阮籍猖狂……不得不感歎魏晉風骨多名仕。
在那個歌與酒盛行的年代,聽起來是多麼叫人悠然神往。
殊不知,西晉是一部沉重的曆史。上乘三國,下啟南北朝,更多地扮演着“過度”的角色。
立國一百五十五年,在農耕文明建立的中原王朝中,昙花一現。
究其原因,是一個觸目驚心的詞——“奢靡”。
1
攀比鬥富與病态虛榮
西晉是中國曆史上,攀比鬥富最為嚴重的王朝。
從貴族階層來說,最為著名的人物莫過于“石崇王恺鬥富”。
此二人,為何許人也?
王恺是國舅,石崇是西晉首富。
兩家都很有錢,誰也不服誰,整天為“誰是西晉首富”争得死去活來。
石崇移居洛陽後,聽說王恺家很有錢。
為了壓一壓王恺的嚣張氣焰,直接拿糖水刷鍋洗碗,用蠟燭當柴火燒水做飯。
洛陽城的人聽說此事後,紛紛豎起大拇指,稱贊石崇家真有錢。
此事傳到王恺耳中,他立刻叫人把自家門口以外四十裡道路用絲綢圍起來。
石崇看到王恺用絲綢圍了四十裡路,自己就用更加昂貴的彩娟做了五十裡的屏障。
兩人你來我往,誰也不服誰,長期霸占着西晉王朝的炫富“熱搜”。
另一位叫何曾的士大夫,也不甘示弱。據說何曾每天都為吃什麼而感到苦惱。史書記載說:
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一頓飯要花費“萬錢”,相當于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費。
即便如此,他依然感到“無下箸處”(嫌棄飯菜檔次低,下不了筷子)。
繼續拿石崇來說,除了與王恺鬥富以外,石崇還有一件毀人三觀的舉動——“飲酒不盡,則斬美人”。
石崇經常在家宴請親朋好友。
席間,他會讓美女敬酒,而且對方必須得喝,要是對方沒有一飲而盡的話。
石崇會覺得自己特别沒面子,會埋怨美女的顔值和氣質欠點火候,直接叫人把敬酒的美女拉出去斬了。
實際上,這是石崇病态虛榮心的展現。
現在社會上,有一些領域、有一些人,像極了西晉那群攀比鬥富的人。
結婚時,彩禮要攀比。人家收了八萬,那我家必須要十萬,要少了會覺得沒面子,在親戚朋友面前擡不起頭。
有很多人整天變着法的炫富,給寵物阿貓阿狗買羊腿、豬腳吃。
要說出于一顆愛護小動物的善心,無可厚非。
但有些人絕對是目的不純,非要把視訊放到網上直播。
人都吃不起的羊腿豬腳,被他們拿去喂了狗。
要說錢是你們家的,你想怎麼花就怎麼花,似乎也有道理。
不要忘了,社會風氣是大家的,不能由着你們想怎麼敗壞就怎麼敗壞。
你私底下給狗狗喂海參鮑魚,拿人頭馬澆花,那是你的家事。
你要放在網上故意顯擺,那就是社會公德問題。
2
拜金到達頂峰
在西晉,華夏民族的拜金主義達到“全盛”。
“錢”被社會奉為萬能的“神物”。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
錢财成為撬動社會的有力杠杆,人人争相談論錢财。
毫不避諱地談錢,沒有羞恥地愛錢,喪失道德地賺錢,絞盡腦汁地花錢。
一位有良知和遠見的士大夫,叫魯褒。
他實在看不下去了,寫了一篇《錢神論》來諷刺當時的拜金之風。
魯褒十分形象地将“錢”進行人格化處理,他說:
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仆。
同時,借助虛構人物司空公子和綦母先生的口吻,表達出:隻要有錢,吉無不利,必有富貴,還讀什麼書。
魯褒因為生活在西晉那樣的拜金社會,從“萬般皆下品,唯有賺錢高”的現狀,看到銅臭氣息的無處不在以及對世人的危害,進而寫下《錢神論》。
《錢神論》放在當下,依然有極其重要的現實對照意義。在一部分人眼中,“錢多錢少”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标準。
在一些名為“企業家”,實為“資本家”對錢财的極力鼓吹下,有些人的價值觀已經呈現畸形。
甚至有人認為,隻要有錢,讀書的意義不大,說什麼“大學生打工,國中生當老闆”的言論。
更有女生赤裸裸地說出“甯坐在寶馬車上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
這一幕,與魯褒的經曆極其相似。
錢,固然是好東西,其作用也巨大無比。
然,人的心裡裝得全是錢,想方設法用錢來“使鬼”,把“錢”立為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
扔了書本,丢了仁義,失了美德,抛了愛情,棄了親情,社會風氣是以敗壞。
3
“清談”與享樂
魏晉風骨,咋一聽很酷的樣子。
細細琢磨,那些所謂魏晉名仕真的沒有做一些有實際意義的事。
用現在的話來說,那是一個娛樂至死的年代。
而娛樂至死的背後,一方面有文人士大夫對司馬氏的抗拒,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奢靡享樂主義的影響。
在生産力相對落後的西晉時期,那些魏晉名仕整日不做實事。
要麼相約竹林縱情歡歌,要麼喝酒度日逃避現實。
對于社會财富和公共資源,何嘗不是一種浪費。
知識分子所探讨的内容大多華而不實,以“玄學”居多,嚴重背離生活實際。
哪怕是王羲之的家族,琅琊王氏被稱為魏晉“玄壇”的領軍人物。
當家人王衍官至尚書令,甚至到南北朝時,王氏依然顯赫無比。
前邊有鬥富的王恺。
後有王衍、王衍,再往後王敦、王導、王廙、王曠。
以及東床快婿的王羲之,都出自琅琊王氏家族。
但翻看史書,影響曆史長達數百年的王氏,卻被人評價說“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
唐代房玄齡修完《晉史》後,拿給太宗李世民批閱,李世民看到《晉武帝本紀》時,曾感慨說
“不知處廣而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也”。
可謂是一語擊中要害。
然,知識分子應當引以為戒,把學術做實,腳踏實地做學問。
而不是像商人那樣投機倒把,急于變現,樂于享受。
4
奢靡是社會的“癌細胞”
很多人沉迷于奢靡享樂中,把“錢”奉為圭臬,抱着過把瘾就死的心态,對自己恬不知恥的銅臭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極盡所能地享受着奢靡帶來的低級快樂。
為了尋找更加“美好”、更有快感的奢靡生活,變本加厲。
最終,被奢靡的癌細胞所吞噬。
“在看”點一下,互相共勉,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