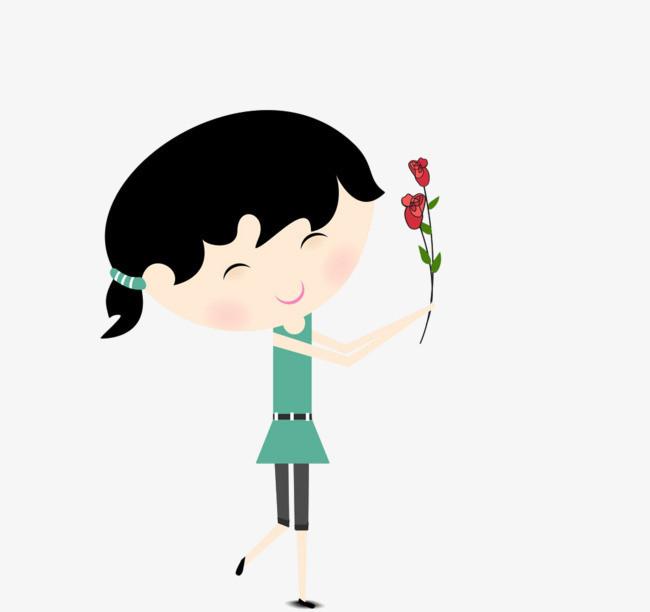李康美
友人讓我給他寫一幅字,内容是: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尋平處住,向寬處行。此乃左宗棠的傳世名言,最先镌刻在江蘇無錫的榮氏梅園中。新中國成立前,榮氏梅園的主人曾是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家族的私家花園,後來許多官員和文人也都紛紛效仿,把如此的條幅懸挂在家裡客廳或工作的書案作以自勉。據說,世界級富豪李嘉誠同樣對此聯非常喜歡,不但自己經常吟誦,而且還推薦給朋友。不管是左宗棠,還是榮毅仁、李嘉誠,他們都是家财萬貫,可是又提醒自己要“享下等福”,這是不是故作矯情地站着說話不腰疼?尤其是無錫榮氏梅園何其奢華,何其氣派,還要把諸如“享下等福”的句子借來嵌入園中,就實在是一種反諷了。
有學者對左宗棠的撰聯也作出了诠釋,說那就是心有遠大的志向和抱負,對緣分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對物質追求普通人的生活。此聯濃縮了古代聖賢“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智慧,暗含着深刻而普遍的人生哲理。其實,作為最底層的老百姓,對生活的向往更簡單、更樸素,比如在那早先的農耕年代,“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就是最坦然、最舒适的生活享受。随着時代的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年輕人訂婚和結婚出現了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三轉一響”的聘禮标配。90年代以後,聘禮又變成了金項鍊、金戒指、金耳環和木蘭機車的“三金一木”,而且還要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等“四大件”。近年以來,再添加了車子和房子,人們平時對生活的追求,實在是花樣翻新。
誰還在追求“享下等福”?
古人在創造“福”字時,當然也離不開原始歲月的拘泥,那樣的追求幾乎是人人平等,絕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在甲骨文中,左旁的“示”,實際是一個祭祀台,而右邊又是一個酒壇子,把酒倒在祭祀台上,以表示共同對神靈的乞求。随着文字的演變,左旁的“示”字仍然為祝願和祈禱,而右邊的“一口田”也僅僅是有飯吃有地種的寓意和象征。從“福”字的演變中也可以看出,前者是精神的護佑,後者就是物質的小滿足。
那麼從左宗棠手裡寫出的“享下等福”真是故作矯情的自我欺騙嗎?其實這樣的吟誦和身份地位沒有關系,說到底就是一種生活态度,就是一種心境的自然和平和,是一種永遠不忘本的民間情結。富豪的房産千萬間,而他和常人的睡覺都一樣,更何況如果取之無道,那就會噩夢連接配接着噩夢,絕不比硬闆床睡得舒适和安然。是以說“享下等福”就是首先要走在“正道”上,保持一顆平常心,時時提醒自己,除了身份和地位,每個人都是肉體凡胎。用普通人的心境生活,和人交往,就會免除許多精神之累。
下等福也應該是享福的範疇,我感悟左宗棠的意思,也不是說時時一介布衣,頓頓粗茶淡飯,或者是安于陋室,樂居山林就是福氣;下等福絕不是要當下等人,而是心有高遠的視界,卻活在清靜自在的氛圍和心态裡。享下等福的人,就是首先在心靈上離開爾虞我詐,離開紙醉金迷,離開欲念飛揚。哪怕工作和事業仍然停留在官場或名利場,也必須警示自己要善良,不攀比,不膨脹,始終保持一顆普通的心。自己覺得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應該是享下等福、的真正注解。有下等福,那就必然有上等福、中等福吧?要不然左宗棠就不會刻意把“享下等福”劃分出來。按照我們的習慣思維,皇上就應該享着上等福,現代的高官和富商以及社會名流們。就應該是享着中等福的另類群體。可是先不說他們每天要操多少心,要擺平多少事,就是腳步和大腦,也由不得自己自由配置設定了。那麼作為高高在上的封建士大夫,左宗棠自己有沒有生活和精神的自由呢?我想應該是做不到的。缺失的才覺得格外珍貴,是以就隻是一種願望,也可以說隻是一種美好的向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