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菲、高明
在我心靈深處,黑色的大鼓咚咚作響。
我聽見黑色的曆史在歌唱。
——[幾內亞·比索]米德萊賽《我聽見黑色的曆史在歌唱》
非洲進步詩人米德萊塞在《我聽見黑色的曆史在歌唱》[1]一詩中盡情地讴歌了飽經滄桑、負重前行的非洲大地。他在全詩中表達了對非洲黑色皮膚,以及對非洲厚重曆史的深刻認同。當代非洲思想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雖然出生于印度裔家庭,成長于殖民時期的烏幹達,卻也更認同自己的非洲人[2]身份。将非洲視為一個整體,号召全世界黑人反對種族歧視和殖民統治,這樣的“泛非主義”[3]思想具有超越民族國家範疇的意義。《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讀本》[4](以下簡稱《讀本》)收錄了這位思想家的五篇論文與一篇訪談。雖然這是一本編譯而成的書,但我們仍可從這幾篇寫于不同時期的重要文章中梳理出馬姆達尼的問題意識:如何在殖民的曆史語境中與後殖民的當代國際格局中了解非洲的族群、種族與民族問題,進而徹底地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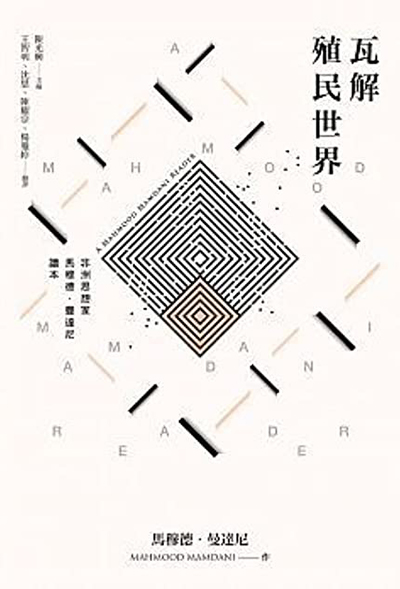
《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讀本》
馬姆達尼獨特的人生經曆指引着他關注非洲問題,認同非洲身份。自少年時代起,他就一直輾轉于世界的各個角落,在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文化氛圍中成長。他上世紀60年代赴美留學,期間參與了美國的民權運動。70年代在烏幹達因前總統阿明的排亞政策而被驅逐出境,最終在197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是以,專業的學術訓練,為他思考非洲問題提供了紮實的基礎,而波折的生活經曆則讓他的思考更具有人文關懷的精神,激勵他踐行知識分子的使命與擔當。
馬姆達尼的書以及他的學術精神對于今天身處于中國的我們來說有着怎樣的現實意義呢?從中非的曆史淵源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與非洲因相似的曆史遭遇,在民族獨立和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牢固的兄弟般的情誼。另一方面,我們對于非洲的認識卻又總是隔閡的。那些認為非洲等同于苦難、落後、疾病和懶惰的歧視與偏見,或多或少也會影響我們今天對非洲的認識。如今,中國與非洲的關系已經進入轉型更新的新時期,《讀本》首先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非洲,了解其殖民主義曆史,把握非洲政治和傳統的特殊性與複雜性,挖掘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與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鬥争的共同點,增強彼此的共鳴和了解。該書還有利于我們在了解非洲處境的同時形成全球視野,在與非洲的政治傳統進行比較的同時加強對自身曆史的認識。
一、徒有其表的獨立與和解
20世紀大部分非洲國家解放運動的性質主要是“反對種族壓迫,而不是階級壓迫,是黑人對白人的反抗,而不是無産階級革命”。[5]這些非洲國家都不是通過階級鬥争,而是以反抗種族壓迫來獲得民族國家獨立的。民族國家在獲得獨立的同時,意味着各個族群在其民族國家的内部達成和平的共識,探索包涵解決内部沖突方式在内的國家治理機制。然而,很多非洲國家的獨立并沒有為其帶來期待已久的平等、和平、民主與繁榮。寫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當代非洲的政府與公民社會》和近年寫就的《超越紐倫堡》這組文章對烏幹達和南非這兩個非洲國家獨立的性質與各族群之間和解的實質進行了剖析,揭示了國家民族主義的空洞性,以及族群和解的不徹底性。其空洞性與不徹底性是後殖民主義政治遺留下來的問題。從外因來看,前西方宗主國雖然不再直接占領非洲殖民地,但卻通過後殖民主義的政治治理術間接但有效地控制了烏幹達、南非、盧旺達等國。從内因來看,非洲各國自身解放力量的羸弱與妥協,為自己初生脆弱的政權埋下了尾大不掉的隐患。他們看似用和平談判的方式避免了暴力血腥,但卻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形成了曠日持久的内耗。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英國在烏幹達的殖民政府居然開始主動放棄宗主國權力,以烏幹達自治為目标展開名為“殖民改革政治”(Colonial Reform Politics)的計劃。馬姆達尼一針見血地指出[4],英國在烏幹達的殖民政府并非出于“好心”而放棄統治。當烏幹達的民族抵抗力量逐漸将底層的勞工、農民和其他庶民階層成功地組織到一起的時候,殖民統治者驚覺,與其死抱着殖民政權,不如順應曆史潮流,主動将主權過渡給烏幹達人。放棄直接統制後,前宗主國仍可以利用烏幹達民族抵抗力量内部不同階層和族群之間的沖突,瓦解勞工、農民和其他庶民之間的團結,培植具有專業能力的烏幹達精英接手原殖民性的國家機器。
通過這樣的方式,前宗主國便可保留自己在烏幹達的利益。烏幹達用表面上的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為英國的殖民統治畫上句号的同時,開啟了新的殖民形式。“恩賜”而來的民族國家獨立夾帶了前殖民地宗主國的私貨,親西方的神職人員與上層精英人士掌握了國家政權,而烏幹達内部不同階層和族群之間仍沖突重重。
到了1980年代,未能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的穆塞維尼組織成立了烏幹達全國抵抗軍(National Resistance Army,簡稱NRA),再一次艱辛地将烏幹達不同民族的庶民階層組織在了一起。然而,當穆塞維尼終于在1986年成功當選總統,他上司下的NRA獲得了國家政權的時候,他們反而再一次錯失了徹底清除殖民機制的機會。馬姆達尼指出[4],NRA摧毀了當時新殖民政府的鎮壓機制,卻仍然對行政和司法部門照單全收,沿用了舊國家機器中的專業人員,沒能将NRA原來的骨幹培育為有能力參與國家治理的力量。
經過這兩個政治階段,烏幹達新政府的利益取代了各族人民大衆的利益。不同族群庶民的力量被空置,人民民主抗争的訴求被窄化為精英主義的訴求,民族主義的話語被依賴于原宗主國國家的社會精英所利用。代理宗主國利益的政府精英利用民族主義話語,以維護民族國家政權,穩定國内政局為由,打壓各族群庶民追求平等權利的訴求和行動。
無獨有偶,南非的民族國家獨立曆程雖然與烏幹達不同,但是它在處理種族隔離帶來的遺留問題上與烏幹達有着共性:都保留了舊有的官僚體系,族群“和解”等關鍵概念的内涵被替換,族群之間的沖突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馬姆達尼在《超越紐倫堡》中指出,二戰後與東京審判齊名的紐倫堡審判有這樣幾個特點。首先它是戰争結束後,戰敗方和受害者以及戰勝方和加害者在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陣營之後,展開的審判。這個審判展現了受害者正義,并由代表加害者國家的官員個人來承擔戰敗後果。從刑事正義出發,由國家首腦一類的個人對戰争中侵害人權的行為進行負責,由紐倫堡審判奠定的這一模式隐含了兩個政治條件:二戰是以毋庸置疑的勝敗情況為結果的;比起對戰敗者的審判,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秩序是二戰後更為重要的政治任務,而新秩序可以在國際政治領域裡建立,不需通過紐倫堡審判來建立。
于1961年宣告獨立的南非共和國,沒能在民族國家獨立的同時解決内部的種族沖突問題,掌控政權的南非白人反而推行起内部的種族隔離制度,使南非獨而不立。南非内部的白人和黑人,以及黑人各族群之間的沖突沖突恰恰反映了前殖民宗主國在南非仍享有非常大的特權,借由南非白人展現出來。
于是,為推動種族平等,建立真正平等、民主、繁榮的國家,當南非面對解放運動組織和種族隔離政權相持不下的時候,雙方決定參考紐倫堡審判的部分理念,召開“民主南非大會”,并在“民主南非大會”的政治協定下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試圖用和平、寬恕、赦免的方式解決争端,換來雙方認同的政治改革協定,為南非建立更為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礎。然而,這一因政治僵局而非明顯的勝敗分殊而開啟的“和解”過程充滿了南非解放組織對當權者的妥協,而這些妥協埋下了後續的政治後患。南非共産黨與以曼德拉為首的非國大[4]同意了“保留舊有的官僚體系,以及讓全面披露真相者可以得到大赦”[4]這一條款。
最終,南非舊有的官僚體系獲得了與烏幹達舊有官僚體系類似的待遇,不僅得以延續,甚至還可繼續發揮反面作用。另一方面,以寬恕和大赦為原則的“和解”過程,雖然看似延續了紐倫堡審判由個人為暴行承擔責任的傳統,以開啟新的政治秩序為目标,而事實上,南非取消種族隔離的“和解”過程并沒有紐倫堡審判的戰争勝敗為前提條件。這意味着在沒有勝敗之分的情況下,正義與非正義,對與錯之間的界限無法明确地樹立起來,解放運動的政治力量和種族隔離政權不得不進行曠日持久的反複談判。于是,南非各政治派别一起召開的“南非民主大會”最終以“幸存者”的利益為出發點,無視“幸存者”中混有加害者、受害者以及加害行為的其他支援者、受益者等情況。“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過将視線轉移到“幸存者”身上,忽略種族隔離制度的制度性、政治性問題,隻要某一被審判者願意承認罪行并忏悔,他就可以得到寬恕和赦免,反而讓相關個人及其背後的政治性問題逃避了問責。南非為了達成“和解”這一目标,付出了擱置真問題的代價,舊有的國家機器得以保留,“和解”的内涵變得空洞不已。
馬姆達尼痛快淋漓地揭示了殘留在非洲民族國家獨立過程中的後患:殖民主義可以以和平、和解為冠冕堂皇的理由,通過新的手段,滲入國家行政體系、司法體系和社會治理的具體方式,實作間接控制。然而他并未在該書的篇章中進一步分析,為什麼非洲各國的進步力量總是與殖民當局形成僵持局面,發展不出自身強大的力量?為什麼非洲的進步力量對舊式官僚機構沒有足夠的警惕?如果非洲各國獨立過程中的這些問題有其必然性,那麼這個必然性的内涵是什麼?
蔣晖指出,非洲大多數國家的政黨及其領袖本身就是在西方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往往充當的是調停殖民者和人民利益的角色。”[8]同時,受西方思想影響的非洲領袖們在反抗殖民統治,追尋獨立解放的過程中又往往希望同時能對西方的自由民主、西方基督教博愛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還有非洲部落的團結傳統進行整合。[8]諸多領袖希望整合不同的思想資源,在整個非洲層面團結所有的黑人兄弟姐妹,走出非洲自己的解放獨立之路,這一“泛非主義”思想[9]其實内在地具有超越民族國家利益,追求更高層面的解放的意義。
在思想理論的建構上,非洲的領袖與思想家們既試圖複興非洲傳統,又努力學習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同時還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争取非洲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征程中,非洲的思想家和領袖們既抵抗西方的殖民主義,也警惕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内部的霸權姿态,同時還要發揮非洲傳統中積極的一面,走出一條非洲的解放、富強之路。思想與實踐路徑内在的沖突之處展現了非洲領袖們的複雜心理:既想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也清晰地認識到他人之長容易演變為殖民借口;如承認非洲傳統落後而對之采取徹底否定的态度,非洲又将何以自立?這一思想上的沖突性其實也與以章太炎、梁漱溟等為代表的中國早期現代思想家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呼應。[10]
無論用什麼方式博采衆長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和道路,對思想的基底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是最為基本且必要的前提。馬姆達尼雖然未在《讀本》中深入揭示非洲各國的政黨和領袖與西方殖民者之間的微妙聯系,但卻從“移住民”和“原住民”這對概念入手,對非洲的曆史和傳統進行了去殖民化的反思,構成《讀本》的另一重要部分。當一些非洲思想家試圖複興非洲傳統,希望建立一個超越階級和族群,以個體團結為基礎,作為家庭延展的非洲時[8],馬姆達尼對傳統的透視有助于去除非洲對自己過去的浪漫化想象。
馬姆達尼
二、透視種族問題的曆史
通常,當我們在談到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之是以存在諸多問題且導緻非洲國家至今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仍動蕩不已時,我們總會認為,長期的殖民統治是造成非洲種族問題,族群沖突相持不下的根源。
殖民地的邊界劃分是歐洲列強在非洲建立政治統治的基礎,包括外部邊界和内部邊界兩個方面。[11]外部邊界,指殖民地之間的邊界劃分,這種邊界的劃分是殖民者通過武力占領之後與非洲統治者簽約或與其他列強協商完成的。這樣的劃分不僅使得非洲大陸被分割得支離破碎,也使得過去屬于相同種族、民族和部落的人民分散到各個國家之間,出現了無休止的糾紛。内部邊界則是殖民者為了有效管理在殖民地内部進行的行政劃分,一方面殖民政府用邊界将他們認為屬于當地不同政治機關的人民分隔開來,另一方面,他們用原來的名稱或是選用新的名稱來命名這些機關,實際上是創造了不屬于該政治機關成員的新身份。這些都為獨立後非洲國家的民族沖突埋下隐患。
《讀本》中《移住民殖民主義之今昔》這篇文章揭示了盧旺達[12]内部邊界造成的問題。盧旺達的圖西人雖然在殖民統治開始之前就已經從非洲的其他地區遷移而來,曆經幾個世紀之久,但德國和比利時殖民統治者仍從統治的需要出發,人為地給他們按上哈姆族(the Hamitic race)這個種族身份,宣稱他們無論身居何出,都是從非洲其他地區遷移而來的外來移住民,而他們到底從何而來,卻早已無法考證。于是永遠作為“移住民”的圖西人就無法像世世代代在自己祖先家園生活的,被劃為“原住民”的盧旺達胡圖人那樣按照“傳統習慣”獲得“族裔空間”——也即隻有“原住民”才有資格獲得的土地。圖西人和胡圖人之間的沖突越演越烈。
盧旺達的圖西人和胡圖人的族裔身份性質不同,這導緻他們雖然看似享有平等的公民權,但在實際上,他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截然不同。這固然是内部邊界劃分導緻種族沖突活生生的例子,但《移住民殖民主義之今昔》這篇文章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它進一步揭示了胡圖人和圖西人在殖民統治開始之前的交往曆史。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交往傳統既非沖突重重、充滿血腥也非毫無龃龉、一片和諧。事實上,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通婚曆史至少有三個世紀之久,“一半以上的盧安達人口是這兩個群體通婚的産物”[4]。然而這兩個族群的封建父權制使得通婚後的族群身份隻能按照父親的族群身份,以排他性的方式傳給後代。在德國和比利時輪番殖民盧旺達之前,圖西人普遍掌控财富和權力,而胡圖人則在整體上更為貧困。但是,胡圖人可以通過自己創造出來的本族群傳統儀式,去除自己的族性,與圖西人結婚,讓自己的孩子成為圖西人。而圖西人中的窮困者很難為自己找到圖西族配偶,隻得與胡圖人通婚,社會地位由此下降。
弄清胡圖人和圖西人的之間交往的傳統之後,我們發現,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有着悠久的交流曆史,兩個族群之間是具有共同的生活與情感基礎的。但是,這兩個族群恰恰對應了兩個不同的封建階層,他們在政治經濟地位上有顯著的高低區分,這正是兩個族群曆史中真實沖突的來源。所謂傳統,其實并非一成不變,總會根據實際情況而有所發展,比如胡圖人的去胡圖化儀式。最後,德國和比利時殖民統治者恰恰利用了胡圖人和圖西人自古以來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沖突對立,把新殖民主義的治理手段包裝成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治理技術,擴大兩個族群的沖突,留給了獨立後的盧旺達。這提醒我們,在進行反殖民主義鬥争的同時,必須正視并清理曆史,隻有真正解決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曆時已久的政治經濟地位不平等的問題,才能避免對傳統産生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重新煥發這兩個族群世代通婚的情感凝聚力,讓傳統服務于盧旺達的平等、民主和富強。
馬姆達尼在該文的最後部分呼籲,非洲各國應超越殖民統治遺留的各種公民、族裔身份,打造一個全民共有的單一公民身份。當然,如果要落實這一呼籲,非洲人民不僅要面對政治上的挑戰,也要面對知識上去殖民化的挑戰,打破對于族裔、傳統等方面的固有認知。思想認知也是間接統治的一部分。一般情況下,間接統治指的是殖民者為減輕管理成本将日常行政移交給當地的原住民政府,在此過程中,殖民者會以自己的意志對當地民族進行政治資源的配置設定,以達到制衡的效果。但馬姆達尼指出,間接統治并不止于此,間接統治是要:
努力重塑被殖民者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其方式是按照一種原住民主義模式分别來塑造它們:通過人口調查中的一系列身份認同來塑造現在,通過一種新型曆史編纂的動力來塑造過去,以及通過一種法律和行政計劃來塑造未來。[13]
正是通過設定法律、建構文化、塑造曆史等一系列實際措施,非洲的移住民、原住民兩種公民身份始終因政治、經濟地位的不平等而沖突不斷。盧旺達在1920年殖民改革之後,作為少數群體的圖西人獲得原住民當局的權力,胡圖人則被排斥在權利之外。此後,圖西人與胡圖人的沖突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終于在1994年爆發了胡圖人對圖西人的大屠殺。但這一民族國家内部自相殘殺式的暴力并非從兩個族群之間的真問題入手,殖民主義遺留的種族問題依然存在。
三、《讀本》方法論的啟示
《讀本》讓我們認識到殖民主義并未遠去。我們可以從書中感受到馬姆達尼對于非洲現狀和世界格局的不滿與批判,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更進一步思考如何實作去殖民化。
首先,馬姆達尼通過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一個客觀過程來了解所有的社會關系”[4],從整體上把握非洲發展的客觀情況,讓我們看到在非洲國家,乃至世界範圍内仍存在着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以及不平衡的世界格局,為挖掘非洲在地經驗提供必要的依據。其次,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雖注重對社會關系結構的分析,卻容易忽視非洲文化環境的獨特性,容易忽視人對社會關系結構的主觀認知。對此,馬姆達尼從非洲的曆史文化環境出發來思考現實問題,為了解世界提供了多重的視角。馬姆達尼從非洲“移住民/原住民”的視角出發,反思美國曆史,他發現美國的曆史總會被當作移住民的自傳來書寫,被包裝成平等、多元、民主的國家,而作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在美國則毫無立足之地,“印第安人生存在一個帝國、種族、以及我們稱為‘西方’的現代勢力集團穩居優勢的世界與時代”[4]。這一發現,不僅對美國的公民權所受到的稱揚提出挑戰,也對美國在目前的霸權地位提出質疑。
然而,較為遺憾的是,馬姆達尼沒有在《讀本》中進一步探讨,為什麼投身解放運動的非洲各進步政黨以及政黨領袖們總是容易妥協,并被“和平”的表象所迷惑。獨立後的非洲國家依然難以擺脫原宗主國的幹涉,難以完全實作獨立自主的發展要求。首先,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始終需要依賴國外資本,沒有形成完備的工農業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因而“非洲的國際位置完全是由其潛在的‘消費市場’和‘能源基地’兩個功能所決定的。”[5]其次,非洲國家自主權的行使也受到原宗主國的影響。發展戰略的制定與發展結果的脫節是原宗主國幹涉非洲國家的典型例證,一方面非洲國家的發展戰略多為西方國家的專家制定,脫離非洲現實,無法成功;另一方面,西方媒體主導非洲輿論與話語權,每當這些發展戰略失敗時,無人對這些外國專家進行問責。[11]
雖然《讀本》沒有對非洲政黨和領袖們内在的問題進行進一步分析,馬姆達尼将政治經濟學、曆史文化和意識形态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仍值得我們學習,隻有這樣才能對非洲問題展開抽絲剝繭式的分析,深入到非洲社會肌理。馬姆達尼的文章既具備理論的深刻性,同時也具備現實的實在性。以多種方法分析非洲問題的方式,來源于馬姆達尼對去殖民化過程中知識分子角色的思考。在非洲大學探索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公共知識分子與學者兩種身份的沖突,是争論的核心問題,牽涉到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公共知識分子強調關注現實問題,針對公共利益展開辯論,而高校學者則堅持追求學術上的卓越性,希望同世界進行全球性的理論交流。在政治上兩者的分歧則意味着:“公共知識分子選邊站,而學者則主張觀察者的客觀性”。[4]但馬姆達尼認為,進入21世紀,非洲的公共知識分子與學者之間的界線不再清晰,兩者之間可以滑動。學術追求與關照現實都是反殖民的重要層面,而實作去殖民化的關鍵則在于,填補生産理論與應用理論之間的鴻溝。長久以來我們在學習西方理論的同時,也産生一種西方理論可以應用到他處的預設,但這是一種“技術轉移”的方案。西方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在地經驗,也不能夠指導在地實踐。是以,馬姆達尼提出要“理論化我們自己的現實”[4],要對我們運用的理論重新進行思考,對我們的思想重新進行梳理,進而“建造應合于了解與肯定獨特曆史與經驗的新穎範疇。”[4]隻有這樣,方法論與認識論的去殖民才是可能的。
總而言之,《瓦解殖民世界》通過對非洲問題的分析,讓我們看到殖民主義不僅存在于政治經濟之中,也通過一系列法律、制度滲透到文化與日常生活當中,世界仍被殖民主義的陰霾所籠罩。馬姆達尼的文章啟示我們,當世界都在以歐美經驗為标杆時,我們更應該注意到地方曆史文化的特殊性,進而思考如何生産在地化的理論與知識,形成在地經驗,最終真正實作去殖民。這一過程勢必是艱巨而充滿挑戰的,但是我們看到以馬姆達尼為代表的非洲思想家已經開始了思考與嘗試,為我們挖掘在地經驗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方法與資源。去殖民的道路仍舊漫長,但是非洲的大鼓已經敲響!
[1] 周國勇 張鶴 編譯.非洲詩選[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 馬姆達尼.馬姆達尼:在中國與西方之間,非洲沒有站隊[DB/OL].https://www.guancha.cn/america/2011_11_08_61529.shtml?xgyd,2020/8/5.
[3]“泛非主義”源遠流長,但是其現代意義上的反帝反殖民内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清晰起來的。具體見:阿裡·穆薩·以耶,李臻.泛非主義與非洲複興:21世紀會成為非洲的時代嗎?[J].西亞非洲,2017(01):34-43.
[4](烏幹達)馬穆德·曼達尼 著 王智明 沈思 陳耀宗 楊雅挺 譯.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讀本[M].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6.大陸暫未有譯本出版,該書作者為Mahmood Mamdani。台灣将作者名譯為馬穆德·曼達尼,大陸譯為馬哈茂德·馬姆達尼。為友善大陸讀者,文中的作者名均采用大陸譯名,即“馬哈茂德·馬姆達尼”或“馬姆達尼”,注釋采用台灣譯名。
[5]蔣晖.當代非洲的社會和階級[J].讀書,2019(12):85-92.
[6]“種族”一詞更強調不同群體之間的不同是由生物基因的不同這一根本原因造成的,常見于和種族歧視相關的論述。而“族群”這一概念不僅指基因的不同,更将人群之間不同的文化曆史納入其内涵。然而,近來也有對不同“種族”具有不同生物基因的說法有反思、批判的聲音。
具體可參考:Elizabeth Kolbert.There’s No Scientific Basis for Race—It's a Made-Up Label[DB/OL]. National Geographic,2018(4),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8/04/race-genetics-science-africa/,2020/8/5.
[7]《讀本》翻譯為非洲民族議會,而中國大陸習慣譯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8] 蔣晖.當非洲遇見社會主義(上、中)[DB/OL].https://www.guancha.cn/jianghui/2016_08_20_371940.shtml; https://www.guancha.cn/jianghui/2016_08_21_372013_s.shtml,2020/8/5.
[9](法)法農 著 萬冰 譯.全世界受苦的人[M].譯林出版社,2005.
[10]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書中第二章和第三章明确論述了中國的文化旨趣因為太過早熟,超越了工具理性的計算而以天人合一為目标,其實不适應二十世紀初期以西方奮起發展這一文化特點為主要内涵的曆史階段。梁漱溟既将中國文化判定為早熟的文化而維護了中華民族文化和曆史的尊嚴,同時也解釋了既然中國文化如此之好,為何還會落後挨打的原因。
[11] 李安山.淺析非洲地方民族主義的緣起[J].北大史學,2001(00):292-319+430.
[12]《讀本》中将盧旺達翻譯為盧安達。
[13] (烏幹達)馬哈茂德·馬姆達尼 著 田立年 譯.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