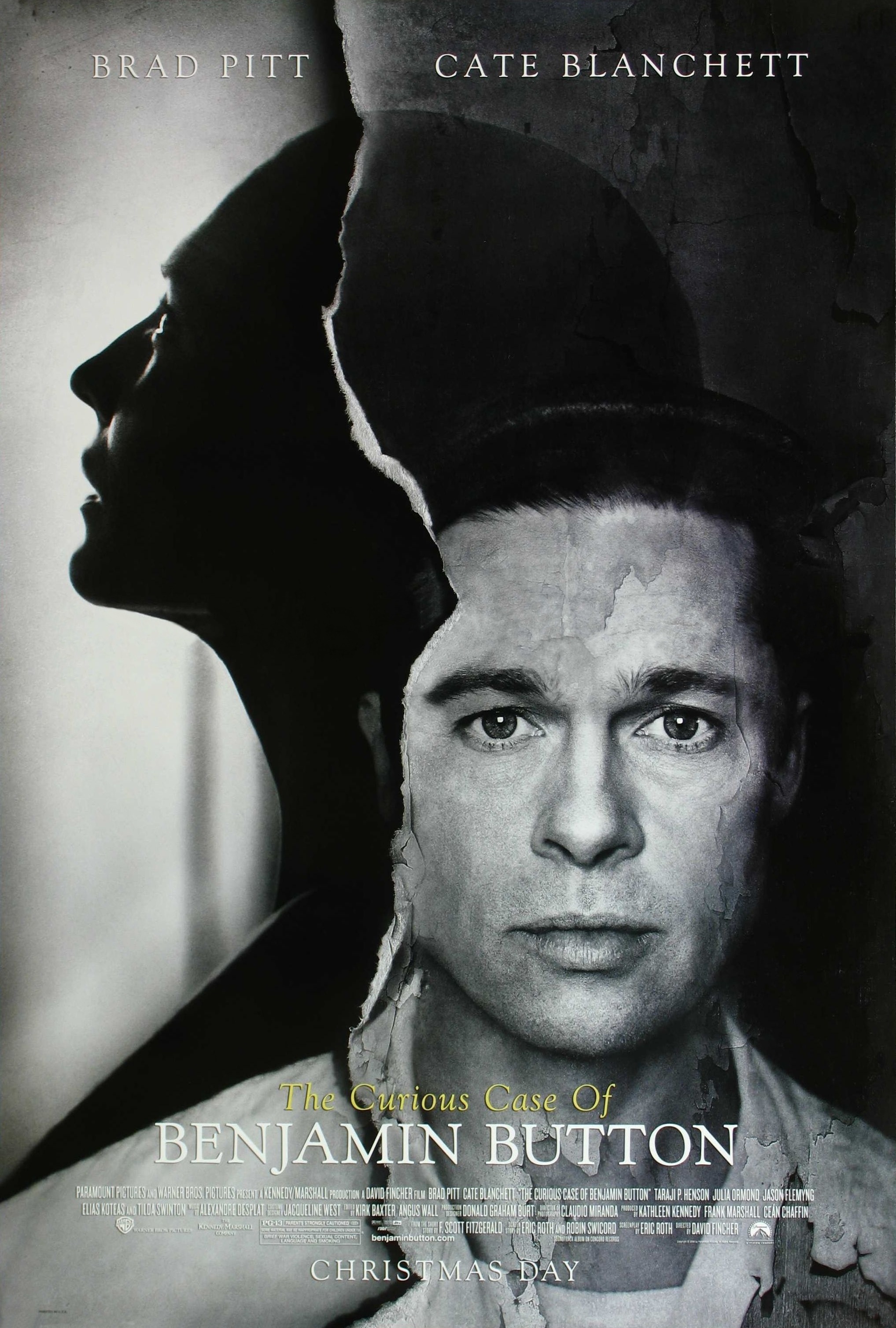
1
民國二十六年春,上海灘弄堂裡的一個無名小卒,叫做鄭樹森的,受他敬重的龐德龐大哥的委托,為中和堂的大佬,叫做虞中和的,送一份大禮。
這份大禮,早早地就被龐德置辦好了,包裹得嚴嚴實實,看不仔細。龐德是鄭樹森可信賴的人,現在自己又被這樣的人所信賴和委托,鄭樹森油然而生出一腔英雄氣,不疑有他。
進了中和堂,通報完畢,高朋滿座的大堂,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大禮被緩緩拆封了,衆聲喧嘩的場地,一時間鴉雀無聲。是一副棺材,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上好的材質打造,這份禮不輕,但這份禮,卻使得鄭樹森陷入了死地。
1918年,美利堅合衆國,馬裡蘭州最大的城市,巴爾的摩,建立成了一座火車站。
車站剪彩的那一天,名流雲集,就連羅斯福總統都到場了。
但最吸引人眼球是,是南方最好的鐘表匠蓋圖先生為火車站建造的大鐘,上緊發條,大鐘開始走動,時間開始流逝,流逝了,就再不回來。
同樣在1918年,同樣是火車站,11月11日,德國政府代表埃爾茨貝格同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在法國東北部貢比涅森林的雷東德車站簽署了停戰協定,德國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此結束。
結束了,作為世界曆史上破壞性最強的戰争之一,參展方兵力達到6500萬左右,超過3000萬人傷亡,終于,結束了,人們為之“送鐘”,鐘聲響徹雲霄,是那一首挽歌。
南屏晚鐘,鐘者,時間的皮囊。
2
2012年8月,海南藏族自治州,倒淌河鎮,彼時有風有雨,我的朋友葉開在風雨中飄搖,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葉開伫立在倒淌河畔,聽歌手張淺潛唱《倒淌河》,“在倒淌河水面,晚風吹着樹影,安慰着青春寂寞的美”,一遍一遍。
青春寂寞的美。是呵,因為在其深處,青春比年老更為寂寞。
因為一切都還正青春,一切都還未開始,一切又都已完結,風起于青萍之末,風止于青萍之末。
比如蓋圖的兒子,從軍行,乘坐火車而去,乘坐火車歸來的,卻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是以這個南方最優秀的鐘表匠,在受命為火車站建造大鐘的時候,建造好了的,是一口倒轉的鐘表,逆時針是順時針,順時針是逆時針,倒果為因,并非是蓋圖發揮失常,反倒是有意為之,也許如此做了,那些在戰場上死去的年輕人,就能夠死而複生,回到家中,生兒育女,耕讀傳家,從青春開始,過完他們漫長而充實的一生。
倒走的鐘,倒流的時間,好青春,好皮囊,一切都還來得及。
3
民國二十六年夏,北平内務部街,藍先生的宅邸,一夜之間成了北平市朱局長的特務第七支隊辦事處。
藍先生算是看明白了,自己個兒這是被朱潛龍囚上了。這還不算完,根本一郎和朱潛龍在房子中央重新砌了道牆,把藍青峰也給砌進去了,講明了三天時間要他交出李天然的下落。給砌牆裡面了,烏漆嘛黑的,藍先生發飙:“這他媽那麼黑,你說三天交人,我他媽知道哪天是哪天啊?!”
羅傑·巴頓繼承了家族的紐扣生意,各種各樣的紐扣,花花綠綠,五顔六色。百年家族,百年基業,而基業長青的秘訣,也是來自于一粒紐扣。
那是一個愛情故事,也是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
巴頓家族的一個世家子,聲色犬馬,風流倜傥,在又一次的一夜風流之後,他問那位妙齡女子需要什麼,動産的汽車,不動産的房子,可變現的首飾,還是直接的鈔票。
那女子沉默,在他就要走掉的時候,才開口:“我要你衣服上的第二粒紐扣。”這世家子有過一霎的錯愕,但旋即摘下第二粒紐扣給了女子,就此走掉了。
事後,這世家子也曾将此事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以飨食客,有位來自日本的博物學家恰好在座,在其他人都哄堂大笑的時候,他回應了這世家子:”第二粒紐扣,在心的上方,收了這紐扣,就是你在我心上。“那世家子聽罷,怅然若失,費盡千辛萬苦找回這位女子,就此浪子回頭,開始做紐扣生意,也就此創下一番基業。
而到了羅傑·巴頓這一代,很是有種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感覺。這麼多的紐扣,這麼多的财富,甚至于因為戰争而更加地發了國難财。這麼多的紐扣,羅傑·巴頓又如何知道哪粒是哪粒?
你不在我心上了,心為形役,塵世馬牛。
新出生的兒子,就因為是個怪胎,就要抱了去水中溺死,被人發現了,又鑽進漆黑的巷子當中,将皺巴巴的18美元連同在襁褓中的兒子一起,放在了一戶人家的台階上,就此隐沒不見。
紐扣縫綴起的衣服,是身體的皮囊,好一副皮囊,好一個衣冠禽獸。
4
忘記說了,作為南方最優秀鐘表匠的蓋圖先生,眼睛不能視物,皮囊已鏽,又何妨?真正好好用心建造如此美輪美奂的大鐘,恰是這位蓋圖先生。
皮囊已鏽,但污何妨。蓋圖先生故意将大鐘建造為倒走的方式,頗有些自暴自棄的樣子,反正我已然瞎了,糟老頭子一個,如有得罪,敬請諒解。話還沒說完,不諒解的總統已然擡步走出去了。
2019年2月15日上午10:02的時候,我的朋友葉開朋友圈有更新,是他一年一度的《自題小像》:
遠山漠漠秋天色,
琴溪潺潺東複西。
赤腳赤眉赤子身,
青山青海青袍衫。
亦信僧道亦敦儒,
何所往兮何所住。
十丈紅塵十年名,
亦負如來亦負卿。
靠窗的火車上,我坐着,越來越遠了,家,家鄉,故鄉,少時放牧的群山,漠漠含煙,臨時停靠,開關車門的時候,風灌進來,撲入胸懷,秋天了,風有輕寒。
家門前有一條叫做琴溪的河流,閑來垂釣碧溪上,且共從容祝東風,潺潺的溪流,會流進離家五百裡此刻身在十萬大山秦嶺深處蜷縮于角落沉沉睡着的我的夢裡面嗎?
會嗎?
經受傳統教育而出,冰心自有,懷抱了冰心,18歲自赤眉小鎮出門遠行,以熟人社會的粗淺社交技能突入陌生人社會,知行合一,談不上頭破血流,但也浮浮沉沉,一如《平凡之路》裡唱得那樣:我曾經跨過山和大海,也穿過人山人海。
風塵仆仆啊風塵仆仆,塵滿面,而皮囊已鏽,而鏽迹斑斑。
曾發力鑽研過儒學,自四書五經開始,沒日沒夜苦讀,我将要去往何處又住于何方呢?
曾在終南山裡尋訪隐士,在樓觀台下望紫氣東來,也發力鑽研過《道德經》,冥思苦想,輾轉反側,我将要去往何處而又住于何方呢?
曾去靈山拜佛,也拜谒北嶽大帝、西嶽大帝,在佛尊前汗如雨下而心神俱寂,我将要去往何處而又住于何方呢?
紅塵十丈,客居十年,一直都是那個局外人,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尴不尬,也曾自在笑傲也曾悲從中來。
所幸,還在讀書。
徐皓峰先生說,北方理念當中,刀的真意,在藏不在殺。刀法是防禦技,刀背運用重于刀刃,因為人在刀背後面。
讀書就好似一棱刀背,縱然皮囊已鏽,還好刀背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