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日本近代史書裡,倒幕運動是明治維新之前極為重要的曆史事件。以薩摩、長州為主體的改革派逐漸認識到自己國家的危機,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為明治維新鋪平了道路。自然而然,薩摩、長州為主體的“薩長同盟”就成了推動日本進步的重要力量。在這場運動中,也誕生了像西鄉隆盛、坂本龍馬這樣的維新“英雄”。
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半藤一利認為,這種叙述是基于“薩長史觀”的曆史叙述。曆史是勝利者書寫的,薩摩和長州的正面形象也是基于他們在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中的貢獻。是以,半藤一利提出了“反薩長史觀”。他認為,明治維新不過是一場暴力革命,隻不過後人根據自身的立場給它貼了正義的标簽。在“反薩長史觀”中,是如何看待倒幕運動的?半藤一利對“薩長同盟”的看法又是怎麼樣的?半藤一利認為,幕府若早幾年開國,曆史沒準會有不同的結果。
以下摘編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幕末史》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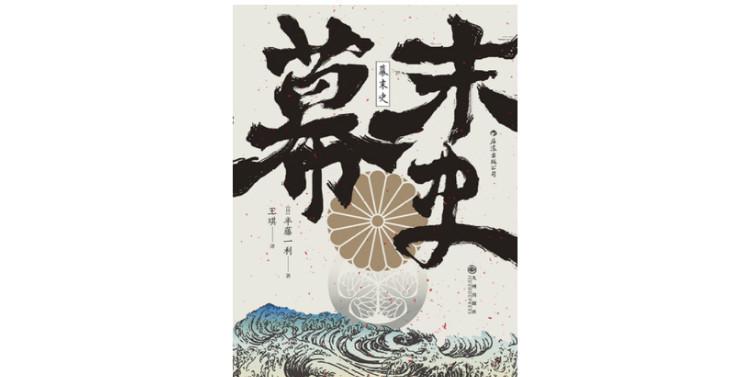
《幕末史》,[日]半藤一利著,王琪譯,後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原作者 | [日]半藤一利
摘編 | 徐悅東
高杉晉作“獨自一人的叛亂”
幕府得到朝廷的敕許,第一次向長州派遣了征伐軍隊。此時的總參謀長是薩摩的西鄉隆盛。西鄉認為發起戰争實屬愚蠢之舉,不如讓長州藩自己解決自己的事情,是以最後并未開戰。有關西鄉的想法,背後有這樣一個說法。在他與勝海舟見面之際,勝海舟對他說,今後的日本即便是由外樣大名執政也沒問題,必須起用強藩的優秀人才,實行共和政治,也就是今日所說的代議制度,如今的幕府已經不可依賴了。西鄉可能是聽取了他的意見,進而認為摧毀長州藩對日本沒有任何好處。但他雖讓長州藩自己處理,自然也提出了各種條件。不過其中并不包括降至五萬石或發配至東北某地的處罰,第一次長州征伐就這樣結束了。
此舉或多或少是對長州藩施以恩惠。是以之後的薩長同盟背後,可能也有此時長州對西鄉抱有的些許信任感吧。總之,攘夷熱橫行的長州藩就此崩潰。長州曾經一度奪取政權,引領時代,卻做出炮擊朝廷的大逆不道之事。由此,主張回歸自藩的保守派、守舊派(俗論派)開始得勢。而所謂的明治維新史就是勝者的曆史,從勝利者的角度來看,這些人就屬于“俗論派”吧。總之,眼下是俗論派的人奪取了天下。他們開始攻擊繼承松下村塾吉田松陰流派的攘夷派志士,依次對其進行處罰,讓他們切腹自盡,或将他們暗殺。
高杉晉作提前知曉此事,便藏身于九州。桂小五郎若是回來,也會被殺,是以他逃至隐蔽的出石居所。伊藤俊輔(博文)帶着 名叫阿梅的愛妾逃到了别府溫泉。幾乎所有領袖人才都離開了長州。剩下的井上聞多在逃跑之際被俗論派襲擊,以緻遍體鱗傷,差點一命嗚呼。我記得戰前的修身課教科書中曾經提到,井上當時十分痛苦,請求别人直接為他介錯。由于缺少醫療用針,醫生一邊鼓勵他,一邊用細針給他縫合傷口,使他最終撿回了一條命。
倒幕運動
如此一來,長州藩被完全排除在曆史舞台之外,回歸到過去邊境強藩的狀态。高杉晉作建立的奇兵隊、伊藤俊輔率領的力士隊,以及遊擊隊等過去引領時代的部隊,也被下令全部解散。衆人被趕出萩城,逃往遠方。
這些人聚集在長府的功山寺,商量今後該怎麼辦。但是并沒有什麼好點子。核心人物奇兵隊隊長赤根武人想讨好俗論派,來到萩城下向俗論派道歉,懇請他們留下奇兵隊。藏身于九州小倉的高杉晉作聽聞此事,認為一旦如此,過去的理想都将付諸東流。高杉說,如果現在還不有所作為,這個國家(對于當時的人來說,藩就是自己的國家,但高杉的意思是包含長州藩在内的日本國)不知會走向何處,于是他獨自一人偷偷傳回長州。送他離開的是一位名叫野村望東的尼姑歌人,她後來于高杉晉作臨死之際,在高杉身邊贈予他一首和歌。
高杉對望東說:“我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随後便離開了。接着他突然出現在衆人聚集的功山寺,并勸導大家說:“如今正是我們崛起之時,俗論派統治的長州藩已經不是長州藩了。”雖然遭到衆人反對,但他依然堅持陳述自己的觀點,表現十分精彩,這大概正是高杉晉作整個生涯中的最出彩之處。十二月十五日半夜時分,天空中下着小雪,十分寒冷,而他卻激情洋溢地高談闊論着。内容頗長,此處略做陳述。他首先提出:“你們完全被隊長赤根武人的調解政策騙了。赤根是何人? 他是大島郡的農民。“
這話聽來就是如今所說的身份歧視。聽及此處,如前所述,出身低微(從身份制度來講地位極端低下)的山縣狂介(有朋)生氣地表示:“高杉如此瞧不起我們,我們怎麼能跟随這樣的人呢?”于是不再理會高杉。除他之外,很多人也是以十分氣憤,大勢看起來難以動搖。而高杉的演說自此進入高潮階段:“我決定獨自去往萩城,向毛利藩主進言。途中可能會被俗論黨殺害。但是,不論生死,行一裡,盡忠一裡,行二裡,盡忠二裡。尊皇的臣子無一日清閑。”
高杉晉作
其中“行一裡”的名言流傳至今,使聽衆們備受鼓舞。另外,還有一封高杉寄給友人大庭傳七的信件,寫得很好。他說:“我願鎮守赤間關(今下關),在我死後,隻願請來藝伎在我墓前彈奏三味線。”即便死去,葬禮也要熱熱鬧鬧,正是這種覺悟推動他向前走。
動容于這番“獨自一人的叛亂”的精彩演說,伊藤俊輔——後來的伊藤博文——站起身來說道:“那好,我便也行一裡,盡忠一裡。”他率領的力士隊隻有十六人,隊長既然如此說,其他人便也決定同高杉一起去往萩城。随後,共鳴者越來越多,遊擊隊也加入其中。最終,總計六十餘人襲擊并占領了下關的代官所,作為自己的陣地,又得到了三艘船,以備失敗逃亡時使用。就此,他們在長州藩發起了革命(當時還沒有“革命”這個詞 ),揭竿而起。是否 的确為“六十餘人 ”,這一點不得而知,但仔細想來,六十人是個有趣的數字,古巴的卡斯特羅,是率領六十一人革命成功的。我覺得能夠聚集六十人已經相當不易了。
赤根武人去往萩城,不在長州,接手奇兵隊的山縣狂介寡不敵衆,又見衆人的激昂之勢,便決定加入他們,于十六日率領奇兵隊 的大部隊與其會和。此外,在濑戶内海沿岸駐紮的諸部隊也陸續加入其中,所謂的長州藩“革命”正式開始。
這是當年年底的事,很快就到了元治二年(1865),而這年四 月進入了慶應元年。曆史上一般認定 1865 年年初便為慶應元年,是以此處皆稱“慶應”,希望大家了解。一月十日,欲逆轉大勢的叛亂軍擊敗了俗論派的主力,之後越戰越勇,俗論黨的頭目們皆切腹自盡。
一月二十八日,藩主進行了藩政改革,長州再次變成“正義黨”,即之前以建立新體制為目的的極端攘夷派的天下。但是,此時長州藩已經放棄了攘夷思想。高杉晉作率先表示要轉變方針,提出眼下已經不是攘夷的時代了,為了攘夷必須開國,然後不斷吸收西方文明,增強實力之後再行攘夷。“為了攘夷而開國”,這與薩摩藩的想法一緻。是以,攘夷思想從此時開始在長州藩銷聲匿迹了。長州同時還打出了反幕的旗幟,表示早晚要和幕府軍大戰一場。奪取天下的正義黨曾與四國聯合艦隊戰鬥,他們認為如今已經不是舞刀弄槍的時代了,而需要現代化武裝兵力,是以決定在緊急情況發生之前加強水軍建設。于是他們很快叫來大村益次郎,進行軍制改革,開始建立并訓練現代軍隊。
長州的這番動向,幕府方面不可能一無所知。幕府了解到,長州藩又改變了态度,表現出比反幕更甚的、可以稱之為倒幕的敵對意向。于是,慶應元年春天,幕府方面決定着手組建第二次長州征伐軍,再次征讨長州,此次目标為徹底将其摧毀。
中岡慎太郎與土方久元
上述内容盡是圍繞長州發生的故事,此處稍微轉移話題。在國家動蕩之際,有兩個人認真思考了日本的将來。那就是土佐藩的脫藩浪人中岡慎太郎和土方久元。土方一直陪在三條實美身邊,是以繼承了三條的思想。二人都未見過勝海舟,在審視時代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認為若繼續無視如今國家的混亂局面,就難以抵擋西方列強的侵略,不久日本就會淪為列強的殖民地。兩人就此事商談,認為此時兩大強藩薩摩和長州應該緊密團結,建立新的國家。具體何時做出的這個決定不得而知,但兩人似乎在不久前就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開始行動了。
中岡慎太郎
二人都是極端攘夷論者,也是倒幕論者。普通的攘夷論者并未提出倒幕,但二人從一開始就堅持倒幕的觀點。後來,中岡慎太郎在京都近江屋二樓與坂本龍馬一起被刺客刺殺。龍馬當時認為沒必要倒幕,還不如将幕府納入共和制,以此形式管理國家。但中岡慎太郎堅持倒幕論。二人在近江屋二樓商談時,龍馬将刀放在稍遠處的壁龛中,中岡将長刀置于隔扇後方。是以,刺客殺入時,中岡隻能用小刀抵擋。為何将刀放得那麼遠呢?因為想法各異的二人在辯論過程中恐怕有吵架拔刀的危險,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就提前将刀放在了遠處——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想法。總之,中岡慎太郎是極端的倒幕論者。
按照中岡和土方所說,薩摩七十七萬石,長州三十六萬石(比第一次征伐長州之時多少有所降低),這兩大強藩擁有幾個共同之處:一、兩藩都是關原合戰的西軍,對德川幕府仇恨頗深。在薩摩,人們遭遇不幸時就會在口中念道“關原、關原”,默默忍受。在長州則有這樣的習俗,每年一月,家臣向藩主拜賀時都會說:“關原合戰之仇報了嗎?”藩公則回答:“大仇未報。”意思正是指關原合戰之仇至今未報。二、兩藩均成功完善财力(一半得益于走私貿易),擁有強大的國力。三、兩藩都位于遠離江戶的邊境地帶,地理上占據優勢。四、兩藩都有強烈的權力欲望。五、兩藩都熱衷于學問,人才十分豐富。如果擁有這些共同點的兩藩聯合,就能夠對抗七百萬石的幕府,這是他們二人的一緻意見。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中岡慎太郎在其著作《時勢論》中寫道:“為了建立國體,反抗外夷的輕蔑和侮辱,兩藩和解至關重要。”他有極強的使命感,以達成薩長同盟為使命四處行動。
土方久元
慶應元年春天,恰好幕府公布了第二次征讨長州的事宜,主要指令西日本諸藩出兵。對此薩摩藩表示,此次戰争與之前不同,沒有正當的名目,征讨緣由不明,是以不應發起戰争,于是明确表示不出兵。中岡和土方一緻認為,既然薩摩反對第二次征讨長州,便是時機,必須立即行動。已傳回鹿兒島的西鄉隆盛不久後就要來京都,若能借此機會說服他去趟下關,讓他同萩城過來的高杉晉作或桂小五郎見面,或許能通過兩藩領袖的會談消除仇敵關系,推進同盟事宜。
中岡立即前往鹿兒島的西鄉處。另一方面,土方則去萩城,準備說服從隐居處歸來的桂小五郎。其實我覺得土方本應去說服高杉晉作,但這就是曆史的有趣之處,恰好在此之前,高杉與他的愛妾藝伎谷梅逃到四國去了。他費盡千辛萬苦振奮奇兵隊、擊敗俗論派,重新讓正義黨奪回天下,是一位大功臣。但此人行事既有天衣無縫之處,也有容易讓他人誤解的地方。昨天還是強硬的攘夷論者,今天早上起來就變成了開國論者。他并未解釋開國也是為了攘夷,隻是堅持主張開國觀點,是以同伴中有人對他不滿,想要刺殺他。繼續留在藩内有被暗殺的危險,是以他彙集身邊人的資金,準備逃到國外,去往上海,卻又因“卷款潛逃”而被人盯上。不得已,他将籌措到的資金分給山縣狂介和伊藤俊輔,自己則逃至被稱為“四國保皇賭徒”的日柳燕石家中。這是四月下旬的事情。
另一方面,桂小五郎從出石回來,擔任萩城的政事堂用挂,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外務大臣職位。他依照土方所言,向藩主毛利詢問是否能同西鄉見面,毛利答:“可以會談。看情況,還可以去趟太宰府。”此處展現了他開闊的胸懷。而太宰府中有三條實美在。
曆史真是格外有趣啊。正如上一章所講:“曆史是擁有意志的。”在曆史洪流中,某項意志發揮作用時,就會出現恰當的人。正是如此。這個時候如果出現的是決斷力強大的高杉晉作,薩長同盟能否順利結成?這一點不得而知。但在薩摩表現出暧昧不明、拖延磨蹭之态時,若高杉在的話,他可能會說:“你們這群人在磨蹭什麼?還要等到何時?”然而,桂小五郎卻是一位穩健型外交官,也是一位堅毅的談判專家。此處介紹一個有趣的故事,中岡慎太郎評價高杉晉作和桂小五郎時曾這樣說道:
“有膽識,有知識,思慮周密,朝堂之上議論政治難事時,他會保持隐忍,不會直接拒絕,這是桂小五郎。有戰略,有謀略,臨變不懼,毫不拖沓,伺機而動,盛氣淩人,這是高杉晉作。”
正如中岡所言,作為戰略家,高杉十分優秀,但作為政略家,則桂小五郎更勝一籌。高杉是一個豪放不羁的人,他十分重視長州藩;桂小五郎卻與衆多其他藩的人交好,交際範圍廣泛,是一位超越自藩立場考慮事情的人。總之,若此時是分别作為外交官與參謀總長的二人中的參謀總長出現,事情會有何變化呢?而若是外交官桂小五郎出現,會使事态順利發展嗎?曆史總是在恰當的時機選擇恰當的人。
薩長聯合之基得以鞏固
閏五月五日,土方帶桂小五郎來到下關,住在富商白石正一郎的府邸。白石為奇兵隊提供糧食和武器,後來也一直對高杉晉作抱有期待,高杉在世之際他一直提供援助。說起下關,那裡也是源平合戰的古戰場,還是甲午戰争時期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談判簽訂條約的地點,史迹頗多。由于戊辰戰争與幕末史的關系,在日和山公園有高杉晉作的雕像、東行庵遺迹以及長州炮台遺迹。關于白石府邸遺迹,僅在竹崎町三丁目的中國電力下關營業所前建立了石碑。總之,幕末至維新的大轉折正式拉開了序幕。
龍馬偶然間來此白石府邸,這也許是“曆史的意志”吧。龍馬完全不知中岡和土方的計劃,但他贊成薩摩和長州摒棄仇敵怨念,結成同盟,為推倒幕府而努力。龍馬是一個對新事物十分感興趣的人。六日,他同桂小五郎會面。很多書籍記載二人是在江戶修行劍術時的好友,實際上我在為某本雜志寫稿時也曾這樣寫過。但最近經過調查發現,二人修行的時期不同,不可能見面——這應該是事實。桂小五郎自何時到何時待在江戶,當時龍馬是否在江戶,這一點我并未認真比對過。但若為了讓故事充滿戲劇性,讓二人見面之時像老熟人一樣說句“啊,好久不見 ”,然後開始交談,更能讓人開懷吧。不管怎樣,龍馬首次加入了薩長同盟的構想之中。
坂本龍馬
龍馬與桂小五郎以及土方交談了三日。要說龍馬和桂小五郎成了知己,還為時過早,但三日後,桂小五郎最終答應了他們的方案。不過,若參考過去薩摩的作風,可是見風使舵變化多端,毫無信用可言。而且,兩藩在蛤禦門之變中成為仇敵。到底能不能信任對方,實在讓人難以抉擇。土方告訴桂小五郎,中岡馬上就帶西鄉 來此,請再稍事等待。桂小五郎答複:“那我便在此等候。”于是留在了下關。
但是,閏五月二十一日,計劃來下關的西鄉最終并沒有來。來者隻有中岡一人。一問究竟才得知,原本二人是打算一起過來,但大久保一藏突然從京都發來消息,叫西鄉“速速來京”。事出緊急,西鄉無論如何也得去趟京都。于是,西鄉便未到下關,直接去了京都。
土方和龍馬問起西鄉是否對此事不感興趣?不,他很感興趣。 那為何不來?
衆人十分氣餒,其中最失望的是桂小五郎。他甚至想斥道:“你們到底要幹什麼?是耍我嗎!”
龍馬從中斡旋。他說:“你的憤慨我非常了解,但西鄉也有他的難處啊。大家都是為了國家的将來。在國家危難之際,薩長兩藩現在必須冰釋前嫌,團結一緻。這是最好的政策。事情并未到此結束,桂先生,今後請您與我們合作。”
被說服的桂小五郎提出一個方案,希望薩摩能夠表達對長州的誠意。即,目前長州與幕府敵對,不能與外國開展任何貿易。即使想買槍炮,在長崎奉行的監視之下也難以辦到。是以,長州希望以薩摩的名義購買需要的艦船、大炮和鐵炮等,為與幕府一戰,必須将這些武器送往長州。這當然不是無償的,若能辦到這件事,長州便認可薩摩的誠意。龍馬說:“這并不難辦到。”表示将會想辦法說服藩主,于是與中岡一同于閏五月二十九日前往京都。
他們到達京都後,與西鄉和小松帶刀(《笃姬》中的肝付尚五郎,小松家的女婿,是薩摩的重要人物)見面,請求他們以薩摩的名義幫長州購買武器。雖存在意見相左之處,但在充分交流之後,二人最終還是答應了,同時提出長州須将兵糧賣給薩摩,作為交換條件。龍馬和中岡認為長州應該不會有意見。這是六月二十四日發生之事。兩藩都為對方提供了實際利益,在确認利益的基礎之上開始正式進行協商。
當時的武器都是從英國商人格洛弗處購買的,龍馬建立的龜山社中(後來的海援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關于龍馬的書籍中一定會提及此事。
日本國策變更為開國之日
如此,薩摩和長州的交涉,在中岡、坂本、土方三人的斡旋之下暗地裡繼續推進。另一方面,幕府終于決定征讨長州,将軍家茂于五月十六日特意從江戶出發,閏五月二十五日進入大阪城,将此地作為大學營。家茂時年二十歲。他是否真心希望擔任總指揮,這一點不得而知,總之應幕府閣僚的要求來到了大阪。
另一方面,此次不打算投降的長州于六月六日表示,即使山野化為焦土,也要抗戰到底。既然長州明确表示不投降,慶喜、容保、定敬的“一會桑政權”隻好去京都請求朝廷的敕許。最終前去請求征讨長州,是在九月二十日,對決已然不可避免。如此看來,幕府雖一直叫着“征讨長州”,卻沒有實際動作。大規模出兵不是想象中那麼簡單,而與之相比,薩摩和長州的行動較早。這是一場大型戰艦對輕型巡洋艦的戰鬥。
二十一日,朝廷頒布了第二次征讨長州的敕許,“一會桑政權”向久留米藩、熊本藩、廣島藩等西部各藩下達了動員令,當然也向薩摩藩下了指令。大久保一藏等人來到朝廷,向關白二條齊敬大聲抗議,并采取強烈抗議行為阻止敕許:
“若要出兵必須明其大義,正其名分。若名義模糊不清,即便是将軍之命,各藩也無法執行。長州定會盡恭順之道,等候敕裁(如何處置藩主、是否沒收幾萬石、交多少賠償金)。眼下幕府征讨長州毫無道理。希望朝廷斷然下令阻止幕府征長。”
薩摩對此戰持反對态度,表示不出兵。聽聞此事的慶喜、容保、定敬三人再次來到朝廷,提出:“若不采納征長之建言,我們隻能辭職。”朝廷上争論不休,雖然最終決定高舉第二次征讨長州的大旗,但諸藩行動卻十分緩慢,并未做好準備。
此處還有一個大問題。此前同美國簽訂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與荷蘭、俄國、英國、法國也都簽訂了修好通商條約,約定開放橫濱、下田、箱館、新潟、長崎、兵庫為通商口岸。但如前所述,因種種情況,朝廷并不答應,請求推遲五年開放新潟和兵庫。而五年之約即将臨近,九月十六日,聯合艦隊的九艘軍艦在兵庫抛 錨,以此強硬要求在大阪的幕府按照約定開放兵庫。九艘軍艦中,有英國軍艦五艘,巴夏禮公使乘坐其中,法國軍艦三艘,羅什公使乘坐其中,荷蘭軍艦一艘,範波爾斯布魯克總領事乘坐其中。此處并無美國軍艦,美國代理公使博特曼搭乘了英國軍艦而來。美國軍艦之是以沒有來,是因為1861年至林肯總統被暗殺的 1865年間,南北戰争正值最激烈的時期,美國沒有餘力向日本派遣軍艦。
開放兵庫一事,必須想辦法解決。但是,京都隻有一會桑政權的三位首領,當然也有近十位老中,但強藩的藩主們都各自回藩去了。一會桑政權将九艘軍艦集合于兵庫一事上報朝廷,整個朝廷慌亂不已。此處再重複一遍,孝明天皇打骨子裡讨厭外國人,他不希望外國人來到距離京都如此近的港口。話雖如此,此時趕走外國人的強硬姿态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京都周圍的公家們提出盡量延後開放日期。一會桑政權的三人認為這根本不可能,事已至此,無法廢除條約。如今隻有開港,朝廷必須答應他們的要求。“若這樣一直反對下去,我們隻能辭職,你們可以盡情對抗軍艦,但如此一來,外國人可能會進入京都皇宮。”慶喜一面威脅,一面逼迫他們做出決定。
十月四日傍晚,為了說服公家,衆人于小禦所召開了禦前會議。孝明天皇坐在竹簾之後,傾聽每個人的意見。但是,此次會議沒有一位強藩的藩主參加。一會桑三人向公家闡述了自己的意見, 各強藩的禦用挂出席了會議。慶喜發揮了他流芳後世、熱情洋溢的雄辯之才,所陳述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們若還沉溺于攘夷的空想,就會引起戰端,外夷軍隊将會殺到京都,彼時一旦寡不敵衆,是無法輕易講和的。整個日 本都會化為焦土,恐怕天皇也難保住皇位。”
雖然他極力論說,但朝廷的意見仍不能達成一緻。孝明天皇一直保持沉默。入夜,事情依舊毫無進展。既然如此,衆人決定于明日再次集中在京諸藩的三十五位國是相關者,充分讨論之後再做決定。慶喜怒吼道:“無論如何,在條約敕許通過之前,我慶喜絕不離開朝堂!”
其他人都離開之後,慶喜獨自一人在京都皇宮内過夜,如此頑 強地努力動搖朝廷。五日,召開了人數衆多的大型會議。天皇依然坐在竹簾後。會議中進行了多次讨論,最後慶喜站起身來大聲恐吓公家們。其内容他曾親筆寫于信中:
“沒辦法。那我便于此處切腹自盡,完成對德川将軍的責任。我的一條命不算什麼。隻是不知在我切腹自盡之際,是否能對德川的家臣和諸位公卿産生一點觸動?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若是得不到敕許,就準備切腹自盡。”
如此一番威脅之後,他站起身來打算揚長而去。但這隻是他假意離開的騙術罷了。公家們覺得“此事不妙”,于是阻止慶喜離開,事态瞬間轉變。當天夜裡,孝明天皇說道:“就按照一橋中納言的請求,允許兵庫開放吧。”
不得已,朝廷正式下達執行條約的敕許。承認了此前幕府擅自簽訂而朝廷反對的通商條約,即決定采取開國的國策。此處留下了孝明天皇寄給關白二條齊敬的信件,闡述了他當時的心情:
萬民塗炭之苦難臨于眼前,不忍見此情形,着實令人痛心。如今隻能依一橋之舉,雖不願預設于此,推察現實,唯有認可。(朕在禦前會議上充分聽取了大家的議論,總之事态相當艱難。 維護皇室的延續是頭等大事,朕十分厭惡外國,但不能因一己私 欲,就斷送了整個皇室,如此朕将愧對皇室祖先。)
孝明天皇并沒有按照自己的好惡固執己見,而是相當看重皇室血統的延續。天皇家總是這麼有意思,将皇室血統的延續視作最為重要之事。其次是不願看到萬民受苦,二者綜合考慮,結論就是“沒有辦法”。
朝廷在開港問題上争論不休時,薩道義正走在大阪城的街道上。他在日記裡這樣寫道:“大阪的群眾十分善良,對我非常親切,他們很容易接受外國人。”自佩裡來航開始便争執不斷的糾紛,終于因朝廷的敕許得到解決,開國成為日本的國策。如今已經不可能繼續攘夷,幕府也無法擅自做主了。朝廷下達敕許,全面承認與外國簽訂的條約。日本國策達成了一緻,此後大家都以開國為基礎,重建立設國家。
我曾在《昭和史》(平凡社刊)中提倡“四十年說”。即日本近代史從慶應元年開始,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日俄戰争結束為止,是日本成為世界列強之一的四十年,之後到1945年的四十年,是日本帝國的衰落期。此外,經過了六年半占領期之後,戰後的日本從1952年開始建立新國家,于1988年及第二年迎來鼎盛期,泡沫經濟崩潰則是在1992年,這期間也是四十年時間。也可以說,建立一個國家需要四十年,毀滅一個國家也需要四十年。
總之,日本的國策于慶應元年(1865)達成了統一。本來不應在此時期提出倒幕,發動國内戰争,而是應該朝着同一方向齊心協力。但是已經太遲了,眼下即使做出決定也已經無濟于事。十幾年争論不休,幕府的權威和财力等基礎已耗盡,不僅不可依靠,還成為一個麻煩。要創立新國家,必須推翻幕府,在衆人逐漸朝這個方向靠攏之際,朝廷卻先下達了敕許。
曆史真是諷刺,若于兩三年前做出這個決定,形勢就全然不同了。眼下即使國策一緻,又有誰會按照國策行動呢?
總之,幕府閣僚告知四國聯合艦隊,已經得到了朝廷的敕許,之後可以按照規定開國了。眼下立即開放兵庫尚有些困難,是以希望他們稍等一段時間。四國艦隊得知堅持反對開國的朝廷終于同意,也就安心下來。日本已經決定徹底開國,剩下的就是等待開港了。次日,聯合艦隊起錨離開。
薩長同盟結成
如果故事就此結束,那就輕松多了,但實際上這時才即将進入幕末史的高潮。幕末結束,接下來就是維新,雖然我不願使用“維新”這個詞,但總歸是開始為建設新的國家而努力奮進。在龍馬、慎太郎、久元三位年輕人的政策的推動下,此前關系惡劣的薩長兩藩迅速交好。從格洛弗商會購買的武器已運送到長州,且薩摩堅決反對第二次征讨長州,對幕府不予理會。
十一月中旬,龍馬與其夥伴薩摩的黑田了介(清隆)一同來到下關,與等待于此的中岡一起會見了桂小五郎、高杉、伊藤、井上、山縣等長州的主要人物,再次提出了與薩摩和解的事宜。可能也有人會感到相當吃驚吧,不過,眼下總歸是薩摩反對征讨長州,且按照長州的意願購買武器,運送到了長州。目前除了摒棄前嫌,共同為建設新國家而努力之外别無選擇。不過雖然雙方勉強達成了和解,但此前對薩摩恨之入骨的長州人依然懷有不信任感。多虧了龍馬暫且解除了長州人的疑心,在雙方之間斡旋。
桂小五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帶着品川彌二郎、三好軍太郎等長州武士,從三田尻出發,于慶應二年一月八日到達伏見,在特意等候于此的西鄉和村田新八的引導下,來到了京都二本松的薩摩官邸。如果雙方直接開始交涉,事情可能就順利談妥了。但現實并沒有那麼順利,龍馬再次出現了。
一月二十日,因海援隊而忙碌的龍馬恰巧去往京都,他原本以為“事情已經談妥了 ”,于是高興地來到薩摩官邸,卻發現談判毫無進展。詢問桂小五郎後得知,到達此地之後他們每日都忙于應酬招待,結盟之事完全沒有提及。龍馬十分吃驚,詢問道:“究竟是怎麼回事?若是如此,不能由你們提出嗎?”
桂小五郎說:“自從到京都以來,我們确實受到薩摩藩美酒佳肴的厚待。但關于結盟事宜,薩摩隻字未提,我們也不便主動提出。長州被幕府軍隊打敗後一籌莫展,孤立無援。如果在此時提出結盟政策,好似在祈求他人的憐憫。你說得如此輕松,但從武士道精神來說萬萬不可。眼下我覺得款待已經足夠,明日便準備回去,與幕府展開全面戰鬥,即使防長二地淪為焦土,薩摩藩能夠存留下來 為皇國盡忠,我也就滿足了。”
龍馬斥責桂小五郎道:“胡說八道!什麼武士道精神,什麼藩的自尊,這些算得了什麼!此時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據說龍馬是個豁達之人,平時并不容易動怒。他一生之中僅發怒過兩次,這是一回,還有一回是“伊呂波丸”号被紀州藩船撞沉, 他在同紀州藩交涉時可謂怒發沖冠。
總之,如果不把握此次機會,就再也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什麼藩的名譽,什麼武士道精神,他又轉過頭去斥責了西鄉一番:“我們決不是為了貴藩挺身而出,也不是為了自己的名譽和金錢,而是為了這個國家。你們之間存在分歧,但就不能暫時放下這些區區小事,披肝瀝膽,為了天下而商讨日本的未來嗎?”
“我與中岡冒着生命危險,為國家做到此等地步,真心希望你們能夠攜手合作。”
聽及此處,西鄉說道:“我知道了。非常抱歉,我們會立即提出結盟事宜。”于是便同小松一起會見了桂小五郎等長州藩三人。他們默默聆聽三人陳述過去的苦惱,一一點頭表示認可,最後達成了結盟。
一月二十一日,薩長同盟正式形成。盟約包括六條,以下為其中最重要的四條:
一、第二次征讨長州開始之際,薩摩立即派出兩千多名士兵支援長州。此外,向大阪派出一千名士兵,堅決守衛京都和大阪。
二、戰争取得優勢之際也必須保持士氣高昂。到那時,兩藩要将所做的努力上報于朝廷,獲得朝廷的認可。
三、即使戰敗,長州藩在一年或半年内也不會徹底崩潰, 在此期間,雙方必須合作到底,戰鬥到底。
中間兩條省略,最後一條是最重要的:
六、在洗清長州藩冤屈的基礎上,兩藩必須真誠合作,為我日本國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我兩藩為了日本國,以弘揚皇威為目标,為不再重蹈如今之慘狀,必須互相幫助,合作共赢。
說起薩長同盟,很容易了解為雙方達成了攻守同盟。但實際并非如此,而是明确長州受到攻擊時,薩摩要竭盡全力提供支援,同時,兩藩要共同為皇國、為弘揚國威而鞠躬盡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