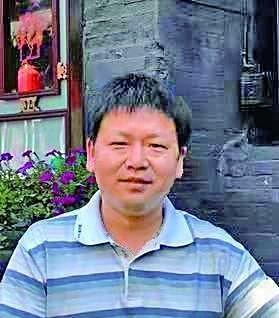
張春龍
裡耶古城遺址一号井發掘現場
兔子山遺址出土的漢律篇題木牍
在沈從文先生的筆下,他的家鄉湘西是一個清奇秀美、民風淳樸的地方,富有一種神秘的魅力。
2002年6月3日,正是在這裡——湘西龍山縣酉水畔,裡耶古城遺址一号井現場負責人鄒波平發現一塊木片上有奇怪的墨迹。由此,裡耶秦簡發掘和研究拉開了序幕,有人稱之為“21世紀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春龍當年隻有37歲,他親曆了這項考古研究的全過程,這段經曆也成為他從事考古研究的一項閃光記錄。
“湖南的重大考古,他都趕上了”
1986年,張春龍從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大學畢業,入職湖南省博物館考古部。同年,像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文物考古所一樣,考古部從省博物館分離出來,更名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從此,張春龍在這裡紮下了根。
他先後參加了湖南臨澧縣胡家屋場新石器遺址、澧縣彭頭山和城頭山遺址和龍山縣裡耶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主持發掘了張家界古人堤遺址、重慶江東嘴遺址和麥沱古墓群、郴州蘇仙橋古井群、益陽兔子山遺址和湘鄉三眼井遺址等。
一年又一年的風餐露宿,他的考古足迹遍布湖湘,發掘出一串串珍貴的文物。其中,有遠古的稻田、村莊、牆垣、房子、稻粒和陶器,更有記載着珍貴史料的大量古代簡牍,讓一批深埋于地下的古代遺址和文物重放昔日的文明之光,展現出湖湘文化的獨特價值與魅力。
有的同行說,“湖南的重大考古,他都趕上了!如此豐富的考古經曆和難得的機遇,不是一般人所能遇到的,在考古界也并不多見”。
張春龍自己則說,可能是因為自己一直待在湖南考古所沒動地方,如同“守株待兔”,都被自己碰上了。
對澧縣車溪鄉城頭山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讓張春龍深感幸運和震撼。
這處遺址發掘于1991—2000年,是國内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晚期古城遺址,距今約6500年。遺址中發現了儲存較為完整的城牆、房址、祭壇、窯址,除此之外,還發現了建有原始灌溉系統的大塊水稻田。“城頭山古城遺址有三百米見方,周邊還發現了護城壕和城外的稻田,在新石器時期就能達到如此之大的建城規模,真是很了不起!”張春龍感慨地說。城頭山古城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曾兩次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随着考古實踐的積累,張春龍的專業功底更堅實了,眼界也更開闊了。上世紀90年代,簡牍保護和整理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還是弱項。1997年,經簡帛學專家胡平生先生推薦,張春龍回到母校北京大學,敬拜在李家浩先生門下,研讀戰國文字。
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裡耶秦簡的出世以及此後在湖南陸續發現的一批古代簡牍,給張春龍帶來了事業發展的新機遇,使他能夠把回爐北大研習的古文字學派上大用場,漸漸地成為不僅能挖掘遺址和文物,還能釋讀和整理古簡的綜合型考古專家。
“裡耶秦簡的發現,改變了我的工作重心”
在沈從文的《湘西·白河流域幾個碼頭》一文中,他精美地勾勒了裡耶、遷陵等地的鄉土人情,尤其是以長長的文字,描寫了在曆史上曾以酉水而著名的白河,它從湖北經重慶進入湖南後,悠悠地流淌過湘西的一座座山嶺和村鎮,最終彙入洞庭湖中。
裡耶地處酉水岸邊,是湘西龍山縣的一個古老小鎮。用當地的土家語來解釋,裡耶二字就是開拓這片土地的意思。2002年,這裡還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火車到達湘西自治州首府吉首後,接着就是盤山公路,還得走四個小時才能到達。
令人意外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偏遠小鎮,竟偶然發現了大量秦簡,這使得裡耶似乎在一夜之間,回到了兩千多年前秦代的曆史舞台,成為考古研究的熱點。有人說,“北有西安兵馬俑,南有裡耶秦簡”,這并非誇張之詞。
“裡耶遺址出土的38000餘枚秦代簡牍,是秦朝洞庭郡遷陵縣的檔案,數量之大,涉及之廣,是繼秦始皇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張春龍說。
據專家介紹,這批秦簡最受關注的是2000多年前當地官府留下的日常公文,内容涉及人口、田地、物産、賦稅、倉儲、郵遞、軍備、司法、醫藥、教育等各個方面,集中反映了秦朝從建立到瓦解的整個過程,極其珍貴。
裡耶遺址共發現三口古井,秦簡集中在一号井内。這口古井的井口距地表約3米,井深14米多,發掘工作很有難度。“如果貿然下去會很危險。怎麼搭建撐架加強,井中堆積物如何由上往下一層層挖出來、運上去,都是難題。現場沒有什麼工具,就連一個小小的輪滑,也是從老鄉家借來的……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當時都是張春龍和龍京沙等同仁張羅解決的。”《裡耶秦簡研究論文選集》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曆史系教授張忠炜說。
裡耶秦簡的發現,極大豐富了此前幾近空白的秦朝曆史文獻。例如,世人皆知秦朝的“書同文”政策,但當時究竟是如何推行至全國的,後人卻知之甚少。裡耶秦簡出土的“更名木方”,提供了“書同文”的具體實物證據,使人們能夠更真切地複原它的本來面目。
以裡耶遺址的發掘和研究為标志,張春龍的考古事業有了新目标。“以前主要是做新舊石器時代的考古,裡耶秦簡的發現,改變了我的工作重心,工作興趣漸漸地轉移到簡牍保護整理上了。”張春龍說。
益陽兔子山遺址發掘,是繼裡耶秦簡出土之後又一重大考古發現。2013年,張春龍主持展開了兔子山遺址發掘工作,共出土戰國後期至三國時期的古簡15200餘枚,其中一批簡牍可往前追溯至戰國時代的楚國,為首次發現楚國縣衙文書檔案實物資料。張春龍認為:“這次考古發掘可以明确兔子山遺址是楚、秦、兩漢、三國吳各朝益陽縣衙署所在地,各時期的簡牍彌補了曆史文獻的不足。”
兔子山遺址還發現了大量當時古人的生活遺物,在張春龍和他的同僚們眼裡,這同樣是極其寶貴的。他解釋說:“其實這些東西并不進階,不過是被古人當作垃圾扔到井裡的廢棄物,比如陶盆、瓦罐、錐子和鋤頭什麼的,但能夠真實反映當年的實際生産水準和生活狀況。在考古發掘中,由于這些雜物同簡牍混在一起,是以我們不能用鋤頭刨,隻能用手一點點地去扒。”
“考古發掘很平常,但發現很重要”
日前,為紀念裡耶秦簡發掘20周年,中西書局出版了《裡耶秦簡研究論文選集》。作為裡耶秦簡的發掘者、保護者、解讀者之一,張春龍很欣慰地說:“将近20年了,當時對裡耶秦簡還有不少弄不清楚的地方,現在基本上看得明白了。”
把考古挖掘的東西看明白,是張春龍從事考古工作一以貫之的追求。
“考古發掘很平常,但發現很重要,而且各種考古發現都有自身的價值,是不可互相替代的。這些年雖然我有了一些發現,現在機關安排新的發掘工作也常常派我去,但這并不是自己的工作水準有多高,隻是說明我的運氣不錯,經驗多一點。”張春龍謙虛地說。
在整理秦簡時,張春龍總能通過一些看似平常的現象而有所發現。
在裡耶遺址一号井發掘出一種刻齒簡,它的形狀與一般簡牍沒有什麼差别,不同的是在左側或右側刻有刻齒。
長久以來,在整理簡牍資料時,學界多聚焦于文字。張春龍則不然,他對器物本身的特征也給予關注,這也許是他出身于考古訓練的專業素養使然。他敏銳地察覺到,刻齒簡上切割而成的符号,很可能與簡文所見數字存在某種對應關系,是以在整理簡牍釋文時,他特意做了标注。
這個重要發現,在後續研究中得到了印證。
在整理益陽兔子山簡牍時,關于漢律的記載也引起張春龍的關注。他注意到木牍将漢律劃分為“獄律”和“旁律”兩大部分,并記錄有44種漢律篇題,大多數是此前聞所未聞的。據此,可以超越以往關于秦漢遵循“九章律”的認識,從整體上進行新的分類研究。
回顧自己從事考古工作的經曆,張春龍有着這樣的感受:“這些考古發掘工作,是一個積累經驗和增長知識的過程,每件事都很平凡,但又都有其價值。這就像是一棵曆史文化的大樹,有的是枝幹,有的是葉子,有的是根部,哪一項都不能缺少。”
(本報記者 計亞男)(本文圖檔均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