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文化禁忌。在封建社會,庶人避聖人諱、臣民避皇上諱、百姓避官員諱、子女避父母諱等,俨然一套森嚴的避諱制度。這種避諱,有時為害甚巨,如文字獄,動辄以文字罪人;有時也令人噴飯,鬧出不少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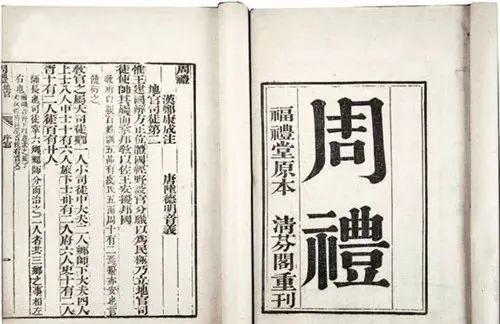
避諱以名諱為主
避諱,在封建社會裡是相當重視的一件事,特别是上層。所謂“避諱”,通常是指在寫文章或說話時遇到君主或尊長的名字不能直接寫出或講出,甚至連同音的字也不能提到。避諱制度起于周禮,但周代為防止避諱擴大化,仍作了種種限制,如“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二名不偏諱,已祧不諱”等。但自從秦始皇建立了君主專制制度之後,避諱的走向是趨于繁苛甚至形成法律,而且連帶形成了皇帝的語言霸權。例如“朕”字,本是古代的第一人稱代詞,自秦始皇後成了皇帝的專用代詞。極端的例子是《容齋續筆》卷四的《禁天高之稱》:“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為名字。于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将但名将……”這種情況曆史上雖持續不長,但反映了帝王們被專制制度扭曲的靈魂。
避諱以名諱為主,故命名的學問随避諱制度同時發生。《禮記·内則》說:“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隐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前三點是針對所有人講的,有普遍性,鄭玄注說:“終使易諱。”日月與國名皆常用詞,因難避諱而不可用;“隐疾”句鄭玄注:“難為醫也。”此條有不雅及使用不便之意。世子即太子,将為天子或諸侯王者,與世子同名易于觸諱。
歐陽修《歸田錄》
漢語諧音字是個汪洋大海,名字聯想的内容也可為人招來麻煩。歐陽修《歸田錄》卷一說:北宋詞人宋祁與其兄宋郊布衣時名動天下,時人稱“二宋”。宋仁宗時宋郊為知制诰,仁宗想重用他。有小人進言說:“姓符國号,名應郊天”。“郊”是冬至時天子南郊祭天之名,進言者的分析,是說宋郊之名有“踐天子位”的潛在含義。又說:“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詳(祥)。”此說使“宋郊”二字又成了宋朝滅亡的谶言。結果宋仁宗暫未重用他,宋郊就改名為“庠”,字“公序”。後宋郊仕途亨通,以司空職務退休,享福壽而終。“郊”字的分析屬于一詞多義,“郊”“交”聯想屬于一音多詞。這樣犯忌諱,是人起名時難以預料的。
有個學生在私塾裡讀書,因他父親名谷,每遇到“谷”字時,也都要改讀為“爹”。如讀到《管子·牧民》“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谷也”,“五谷”念成“五爹”。讀到劉禹錫《上杜司徒書》“百谷之仰膏雨”,“百谷”念成“百爹”。同窗聽了,取笑他道:“你一會兒‘五爹’,一會兒‘百爹’,到底有多少個爹啊?”
五代馮道,曆朝為相。有一次,他命一個門客講《道德經》。門客想這是要犯諱的,就連稱:“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馮道聽了也不覺笑倒。原來《道德經》起首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連犯馮道的諱。
宋時有個州官田登,諱言“登”字,連同音字也不許提,誰要是觸犯必被重責,很多吏役是以而受了笞罰。是以一州人都稱“燈”為“火”,不敢有所觸犯。元宵節晚照例張燈,于是大書通告張貼市上,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見者無不駭笑。流傳的“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語即源于此。
南宋錢良臣,諱言其名。他有個兒子據說很聰敏,每讀經史見有“良臣”二字,就改讀為“爹爹”。有一天,他兒子讀《孟子》有“今天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之句,就改口道:“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原為尊敬,不料反成辱罵。
還有奇者自改姓名而避他人諱者。北齊有個熊安生,去見和士開與徐之才,因為徐之才的父親名雄,而和士開的父親名安,他想自己姓名中“熊”’字犯徐諱,“安”字又犯和諱,于是就自稱“觸觸生”。無獨有偶,明末有個湖廣巡撫宋一鶴,去參見總督楊嗣昌,因為楊父名鶴,為避諱計,他就在名帖上寫上“宋一鳥”。
但是,也有相反的趣事。宋時有個徐申為常州知府,諱言其名。屬下有個縣令申報地方情況,一連三次報告未見批複,就親自去見徐申。徐申非常惱怒,責問道:“你身為縣令,難道不知道上司的姓名嗎?”這縣令不以為然,反大聲說:“我申報的事到府不理,便申監司,監司不理,便申戶部,申台,申省,申來申去,非到申死不止!”徐申拿他沒有辦法,隻好一笑了之。這倒頗有點“強項令”之風。
生活中的避諱
在中國人的生活習俗中,鯉魚有很多寓意,比如娶妻迎親時,聘禮中要有鯉魚;過年的家宴中,一定要有一道紅燒鯉魚;上梁、生子、做壽時宴客,也一定要有鯉魚。這樣既有“禮(鯉)”,又有“餘(魚)”,是個好彩頭。然而,唐朝時,律法規定禁食鯉魚,若捕到鯉魚,要立即放生,否則打六十大闆。因為,唐朝皇帝姓李,“吃鯉”就是“吃李”。
十六國時的前秦國主苻生,是個獨眼龍,是以諱“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等字眼。手下人無意犯了諱,就要受到剁腿、破肚、拉肋、鋸頸等種種酷刑。有一次他叫太醫令程延配藥時,問及所需人參的好惡與多少,程延回答:“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這“不具”可是犯了大諱,苻生勃然大怒,先将程延的雙眼鑿出,再将他殺死。是以帝王的避諱尤其要小心,弄不好是要掉腦袋的。後趙皇帝石虎,諱“虎”為“王猛”;唐代農民軍将領朱全忠,諱“鐘”為“大聖銅”;唐代監察禦史楊虞卿,諱“魚”為“水花羊”。諸如此類,巧言文過,令人啼笑皆非。
宋徽宗畫像
更有奇者,商人為避諱禁殺豬狗。如北宋崇甯年間,谏官範緻虛谄媚徽宗說,聖上壬戌年出生,生肖屬狗,世間不宜殺犬。昏庸的徽宗聽信了他的話,下令天下嚴禁殺狗。無獨有偶,明朝正德年間,太師鎮國公朱鈞曾下過一道禁止屠豬的禁令。這一年是朱鈞的本命年(出生年,生肖屬豬者),又因“朱”“豬”異字同音,權勢顯赫的朱鈞嚴令地方不許買賣、宰殺豬。如果有明知故犯者,全家發配邊遠地區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