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雜志 此刻晚上閱讀
睡前一夜讀,一篇漂亮的文章,帶你走進閱讀記憶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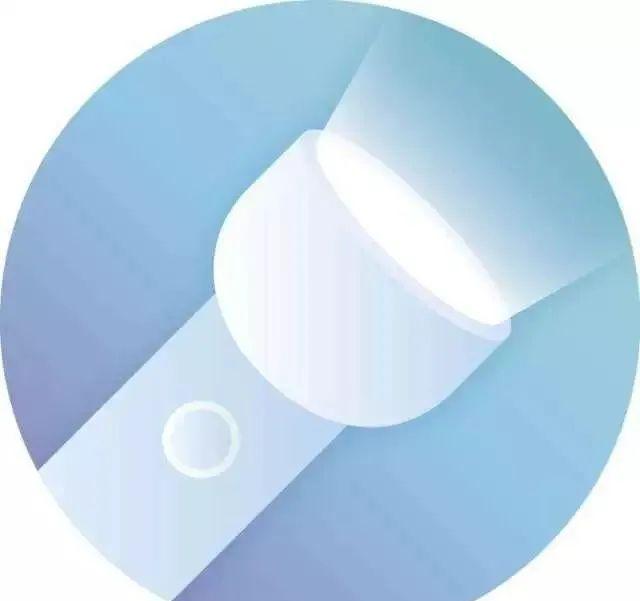
一千年前,蘇東坡,早春帶着新的茶葉野餐,歡快地寫下了《玉溪沙》,其中有一句話,"雪花飄浮,青蒿素芽試春盤"。世界的味覺是清歡。"
春天的美味有東坡的魯達,也是今天人們的思想。
你還記得18年末,《深夜毒藥》食品紀錄片《世界的味道》上線嗎,導演陳曉清,解說李麗紅,配樂敖...曾經用莎莎醬填滿公衆的三神的重新安裝,給了我們一種熟悉而誘人的味道。
團隊将真正挑選時間,四月将筋疲力盡,國家級城市和景區在有序重新開機,第二季《世界風味》深夜又回來了。
依然熟悉的味道,熟悉的人生旅程,不斷延伸着觀衆對家的記憶、美食、年輕人的味道。黃海設計的海報在視覺上傳達了這樣一種感覺,即在風味的星球上,人類從未停止追随美味的腳步。細心的觀衆也能感覺到,這種内容表達增添了不少感情,Y.A.貢察洛夫、帕慕克、王增軒等人與食物關系的作家也穿插在紀錄片中。
世界的風味,是真實感受的基礎,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從西藏白雪皚皚的地區到甯波的鹽田,從尼泊爾到挪威,無論是千年前第一位吃螃蟹的戰士,還是千裡之外生死存亡的甜蜜獵人,人類穿越時空,穿越地球,隻為飽腹。而這種"拗口"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後期的剪輯階段,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陳小青寫下了一句哀歎:"在我們的螢幕上:溫柔的笑容,緊握的雙手,深情的擁抱,親密的親吻和家庭盛宴......觀看節目,看看窗外。有那麼一刻我會覺得,節目中的生活是生活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我希望疫情早一天過去,讓我們的世界再次充滿美味和快樂。"
是以第一集的主題設定為"甜蜜的書"。
甜美,頭發在嘴唇和牙齒上,在嘴裡和舌頭上激起了風水,但在頭部的心髒上掉落了一千次。在第一集中,獲得懸崖蜂蜜的艱辛使人們欣賞它的甜味;在柔軟,嫩嫩的糖油之間,包裹在其中的原始小麥的香氣;以及油脂,碳水和糖,成為Barwon地區客人餐桌上的亮點。特别是,在采蜜過程中,評注提到了采蜜者"采蜜半到留半"的采摘原則,這樣的細節展現了傳統養蜂人與生态環境之間和諧相處的概念。
這一集的糖分濃度太高,但意味豐滿,不僅節目組"希望站在多事的2020年,回首往事,品味世界之美",更為這苦澀的春天,最大的糖選福。
今晚讀一讀,讓我們抓住紀錄片中的玉石燒賣,看看它背後的人類故事。
河流和湖泊燃燒的現狀
溫/沈佳路
(原載于2017年1月文學期刊)
在上海燃燒,江湖的處境已經比較尴尬。與鮮肉袋相比,它的身體明顯瘦弱,而且小籠鋤頭比,它的腰圍是一個大圓,但是一口氣吃了七八個也沒覺得飽。拿它來對付整條街的生油炸,人們一定更喜歡後者。
天地良知,做燒賣一點也不粗心,而且是皮,比生油炸皮要多加小心,要有薄薄的荷葉邊緣,用三根手指在頭脖子上捏一捏,頂部就像一朵花,會好看的。燒掉賣口,注意松動适當,緊緊,吃上僵硬,松動,裡面的腌料容易流出來。如果你不放松,這就像控制當下投入的金額,你正在學習很多東西。然後就把籠子蒸了,鐵鍋在水裡突然滾滾而起,爐膛裡的火,出汗,真硬!
這個生意不是心底底,師傅根本就不做。長期以來,上海人早起吃四金剛,吃生油炸,吃小籠子,吃鮮肉袋,但很難找到燒焦的商店。
如今,食品飲料市場風水、生炒、小籠子揮手穿過市場,鍋糊、油炸袋還切了一塊奶酪、三丁袋、幹菜袋、鮮肉袋、蘑菇蔬菜袋、豆沙袋等組成寶子家族,人頭攢動,在市場上拳打腳踢, 跑馬圈。這時,龍在深淵的燃燒和出售不再願意孤獨,重新從江湖中浮現出來!
轉售江湖,起初有些猶豫,先是賣米打民親牌,但富人不買賬。吃純肉,或帶春筍的鮮肉或蝦。總之,在美觀形式上需要一口,在品味上需要一個提升檔次,在銷售價格上要開放,合理的競争。
燃燒是一種蒸意大利面,皮帶上有熱面條。食品史專家經過考察,認為火賣元渡的源頭,也就是北京,慢慢流行到長江以南,是以燒的資格不老,還有面包和面包,也不像蛞蝓。燒賣名稱不時變化,一個會叫燒麥,賣,開鋤頭,開微笑,一個會叫小麥,鬼毛茸茸的頭,頂梅,在嘉定,曾經叫"紗帽"。有關于生産和銷售形式的描述,也有描述其頂部蓬松的形狀,更多的方言對其影響。
不過,随着我的閱讀經驗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古代第一美食"袁毅在他的《帶花園的美食清單》中記錄了55種小吃,有蛋糕配面條,湯圓用榛子,卻沒有燒焦。有紅科學家認為《紅樓夢》其實是一部中國美食史,卻沒有燃燒的影子,寶兄和林姐都沒有吃過。在"金瓶梅花"中我發現了燒賣的痕迹,比如應該數數等吃過桃花賣,西門慶給侯巡撫,宋巡吃的是大米燒。前者是肉餡,分為豬肉餡,羊肉餡或牛肉餡,後者是祖傳米飯烹饪。
現在,中國的食品飲料市場正在蓬勃發展,從北到南很多城鄉地區都熱銷往下,各有一個秘密。在田野裡,我吃過的燒火賣得面目各異,但核心競争力卻展現在餡心上。除了豬肉,我還吃過烤牛肉、烤羊肉、烤雞、燒蝦等。曾經在江蘇省某縣級市,還吃蘿蔔餡和卷心菜餡出售,味道不惡。北方城市的燃燒可能是大蒜毛,無味,有時含糖太重,這也會讓人失去食欲。
有一次,我和幾個最愛的朋友到南京夫子廟淘寶,在秦淮河的一家茶館裡喝茶吃早餐。五六種零食成一套,裡面有玉石燒賣,我驚訝地把它拿起來吃了。不?不是口燙,而是鹹的,咬一口就沒有食欲。
玉石燃燒是揚州著名的,由富春茶會創始人陳布雲率先提出,特點是薄餡綠,顔色如玉石、糖油口,香甜似香。關鍵是在餡心裡,用綠色蔬菜泥做成,加入蜂蜜、豬油,再蒸火腿,這樣甜加鹽,鹹不壓甜。唐恸珞在《甜苦鹽》一書中寫道,他在揚州月亮明軒吃玉的感覺:
糖蜂蛋糕和祖母綠燃燒
"胡哥要我在月明玄吃早茶,一扇門告訴唐,我剛從北平過來,做了一籠燒玉,讓我嘗揚州的名聲。人們以前見過,讓案件做得好。這種護理無關緊要,這種籠中小吃自然是特殊加工精細的,燒和賣餡是嫩嫩的綠色蔬菜切碎的泥,加上煮熟的豬油和白砂從基部攪拌,小蒸松針基質,燃燒褶皺捏得順滑,蒸熟,側花不像北方燒成的薄面條(幹面粉, 北方被稱為細面條)。我有吃川綠豆泥的經驗,它外表看起來不是很熱,但吃到嘴會把人燒死。夾着燒一甩賣,慢慢一下功,确實是玉溶性果肉,香味不油膩,從此熱甜餡蒸食品有了很大的變化。"
我打電話給服務員問的沒錯,服務員調侃着我無法回答,然後把廚師叫了出來,告訴他燒玉的起源:在邪惡的舊社會,揚州這個賣金洞的鴉片鬼相當多,吸食鴉片的人整天苦澀,需要甜食來調整,豐富的春茶館由引入的色彩賞心悅目, 現在熱氣騰騰,甜美的玉石燃燒滿足了這部分人的需要。今天,我們不吸鴉片,但這個功能似乎無法随意改變它。
撇開情感因素不談,純粹從産品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上海的燃燒比北方很多城市都好吃。今天,上海人提到燒賣,這些話一定要叫"沙子"。是的,康橋、趙家樓、七寶、新島等地的焚燒和網上銷售非常有名,他們都稱自己為"燒沙的右脈",被列入浦東新區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鮮豬肉丁配芽,并有濃郁醇厚的果皮冷凍,餡心的味道還不錯。
唐魯孫對玉石的焚燒也是在Z中讀到的,他在《糖蜂餅和玉石燒售》中寫道:"上海後來開了一家漂亮的餐廳,是揚州人經營的,什麼豆沙豌豆蒸餃、野鴨菜心面、五莳蘿蝦包、泥煎餅,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而且做精緻精緻,味道不丢揚州幾根面條。隻有玉石燒賣了一個,雖然貼玉燒應該很快應該是城裡的通知,但從來沒有出來回應市場,原因是什麼,雖然不知道,據推測大概不難問師傅!"
如果老一輩人提到的餐廳今天還在那裡,他寫的這些小吃肯定會和棚子一樣好。補充一點,我去過台灣很多次,在朋友的指導下品嘗了很多特色風味的小吃,隻是沒吃就賣了。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附圖:紀錄片劇情
元旦
郵編: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