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對于北京故宮而言是一個特殊的年份:紫禁城建成600年;從1925年成立故宮博物院至今,也已經走過了近一個世紀。對于故宮這樣一部大書,能通讀又能讀懂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守護故宮半個多世紀的著名文物專家、清史專家朱家溍不僅通讀了,而且讀懂了。捧讀新近出版的《北京聞見錄》,朱家溍對故宮的角角落落都能講得清清楚楚,他也是以被稱為“故宮活字典”。除此之外,對于北京城的曆史地理、地緣風貌、文物古迹,作者也熟稔于心。跟随作者的腳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老北京上至皇家文化、下至市井風俗的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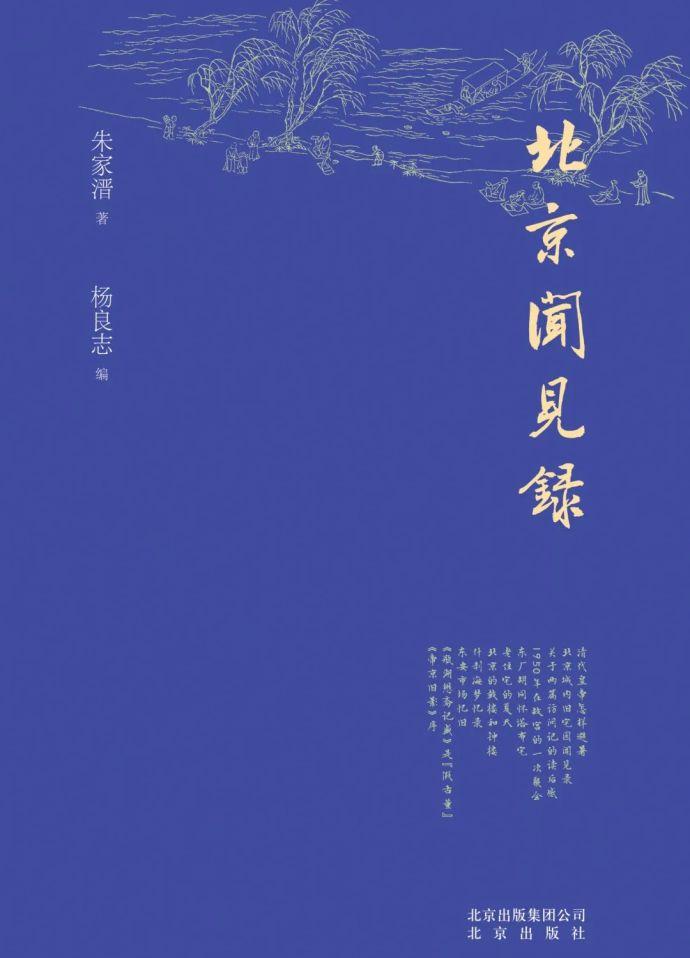
朱家溍《北京聞見錄》
本書以《一個參觀者對故宮博物院的印象》一文開篇,這篇寫于1985年的文章,回憶了朱家溍在60年前,跟随父母、哥哥、姐姐逛故宮的故事。當時的故宮保留着溥儀出宮時現場的原狀:寝宮裡,桌上有咬過一口的蘋果和掀着蓋的餅幹匣子;牆上挂的月份牌(月曆),仍然翻到屋主人走的那一天……乾清宮、坤甯宮等都開着門,允許走進去,皇宮總算是全部開放了。這對當時12歲的朱家溍來說,感到莫大的欣喜,“過去百姓是不能進來的,今天不但能進來而且每個院落都走遍了。”在此之後,作者又多次到故宮參觀。1943年,朱家溍來到故宮當臨時工。雖然他的父親朱文鈞是著名金石學家,他從小就對文物耳濡目染,但是把它真正當作工作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這個工作有一種魅力籠罩着你,能給你很大的快樂。”抗日戰争勝利後,朱家溍正式成為故宮博物院的從業人員。至此,他由一個參觀者成為了一個參與者,也與故宮結下了半個多世紀的緣分。
太和殿
對于衆多參觀者來說,遊覽故宮必須要去太和殿看一看,見識一下影視劇中經常出現的九龍寶座的真容。實際上,關于太和殿的寶座,書中還有這樣一段故事:1915年,袁世凱登基稱帝後,把雕龍髹金大椅不知挪到何處去了,在屏風前面安設一個特制的中西結合、不倫不類的大椅。椅背極高,座面很矮。據說因為袁世凱的腿短,但又要表現帝王的氣派,是以采用西式高背大椅的樣式。1947年,故宮博物院接收前古物陳列所,把袁世凱的大椅撤走,打算換上清代制造的龍椅。于是,朱家溍用了四五年尋找它的下落。他回憶說:“我終于在一個堆積着破爛房料,梁啊棟啊以及花牙子什麼的地方,找着一個破椅子,我看它像。四個柱子裹着龍,這都破了,這麼立起來,還是像個圈椅似的。同時我看見一個日本人照的相,是庚子年他們占領者在這兒照的相,照的就是這麼一個椅子。當時斷定,它可能是失蹤的那個寶座。後來又從康熙皇帝畫像裡看見有一個坐寶座的像,坐的也是這個寶座。”1964年9月,經過修複後的龍椅陳列在太和殿上。可以說,在研究和鑒定中,朱家溍所依靠的不僅是經驗閱曆,更是史料、檔案和實地調查。
太和殿寶座
明清兩代北京城内第宅園庭的傳統風格,久居北京的人感覺不到有什麼突出的特點。可是當我們看過南京、上海、蘇州、杭州、揚州及成都等地的宅園之後,就會意識到北京城内第宅園庭雖然也吸收了不少江南的造園手法,但還是有自己造園的特點。書中第二輯中關于北京城内舊宅的考證和記錄在今天看來尤為珍貴。其中,既有今天北京動物園的前身是樂善園還是三貝子花園的考證,也有博多勒噶台親王府、東安市場的舊貌,雖然很多宅園随着時代的發展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在作者看來,“今據記憶所及,追尋諸園的景物和履歷,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資料。”
有人說,藝術是相通的。朱家溍在平劇研究與表演上,也有很深的造詣。自幼喜歡戲曲的他,師從多位名家,是舉世公認的楊派藝術大家,更曾多次粉墨登場。書中第三輯中留下了很多關于平劇的史料,包括紫禁城内舊制升平署的承應戲、恭王府的堂會戲以及梅蘭芳的講述。尤為令人稱道的是,朱家溍與妻子趙仲巽都熱愛戲曲,兩人曾夫唱婦随合演《得意緣》,成為一段佳話。
在作者筆下,我們感受着他于故宮工作數十載的眷戀、美好與暢想,通過作者的娓娓道來,那些過往的歲月和掌故,不僅是過去的見證,還是曆史與當下的連接配接。這本聞見錄中記錄的人與景、世與情,今日觀之,依然令人欣喜和感動。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