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孫太後不可能輕易讓景泰帝朱祁钰歸還皇位給親生兒子朱祁鎮,為什麼當初在“土木堡之變”後要答應擁立朱祁钰為帝呢,當時的情況與景泰帝朱祁钰穩坐皇位的情況有着天壤之别。
明英宗朱祁鎮是孫太後的親兒子,還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嫡長子,他繼承皇位合乎法統,他當皇帝的時候才9歲,生母孫氏尊為太後,而左右朝政的是明宣宗留給他的“三楊”内閣,“土木堡之變”之前,朱祁鎮基本上不怎麼參與朝政,少年時期有三楊,青年時期有太監王振。土木堡之變是明英宗一生的恥辱,更是大明朝的恥辱。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親征瓦剌,率領二十萬明軍精銳在土木堡被瓦剌大軍殺得個幹淨,皇帝朱祁鎮也當了瓦剌的俘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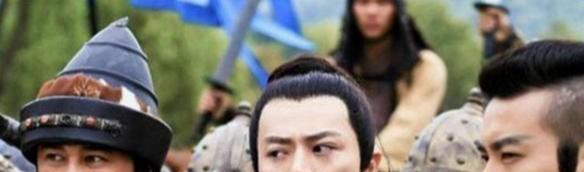
大明朝相當的危險,不要以為瓦剌也先隻率領了5萬人馬,對明朝形成不了威脅,這是個非常錯誤的觀念,瓦剌部不一定要颠覆明朝,他們隻要攻下北京城,明朝基本上就可以歇菜了。帝國的行政中心被占領,朝中自皇帝到官吏被俘虜,給天下人的信心是毀滅性的打擊,保不齊有藩王甚至異姓權勢者起兵造反,這幾乎是肯定的。明朝廷的當務之急是保住北京城,至于被俘皇帝明英宗的死活那是其次的問題。大明的國祚命懸一線,大多數的朝臣都建議遷都南京,以避瓦剌鋒芒。隻有于謙等少數忠義大臣挺身而出,堅守北京,力抗瓦剌。
堅守北京很簡單,但是誰來扛這杆大旗非常的重要,說簡單點就是,明朝是老朱家的買賣,掌櫃的被俘虜了,要把這個攤子支撐下去,必須要有個朱家人出來主事。朱家人來主事相當的重要,這對于國家來說,關乎法統,于謙與衆多主戰派和當時皇室當家人孫太後商議後,決定擁立朱祁鎮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為帝,繼承大明法統,扛起抵抗瓦剌的大旗。
孫太後作為朱瞻基的正妻(廢了原正妻胡皇後,再立的孫氏為後),在皇室的法統傳承上有一定的話語權,卻絕對沒有決定權,她當時希望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繼位,開始因為朱見深當時太小了,才幾歲,于謙等重臣不同意。在那麼危機的關頭,立一個幾歲的娃娃當皇帝,這給天下人的抗擊異族信心是一種打擊,更讓各地藩王對朝中重臣有猜疑,主少國疑,就是這個道理。
孫氏同意了立朱祁钰為帝的方案,景泰帝朱祁钰也非常的能幹,與朝中主戰大臣上下同心,力挽狂瀾,擊敗了瓦剌大軍,保住了北京城,大明江山算是穩當了。如果明英宗朱祁鎮不回來,估計景泰帝朱祁钰的皇位會一直傳承到他那一支。鬼使神差,朱祁鎮被瓦剌給送了回來了。這個時候,大家都很尴尬。既然朱祁钰的皇位是非常時期得到的,大位正統皇帝朱祁鎮又回來了,為什麼不歸還給朱祁鎮呢?這裡面涉及到一個法統問題。皇位傳承不是一個簡單物件,想給就給,想讓就讓。更不是孫太後手上的如意,想給誰就給誰。自古以來,皇位的争奪本就是成本最大,獲利最高,風險最大的事情,沒有哪個皇帝想把皇位平白的讓出去,權力是所有人的靈魂,皇帝是所有權力的權力,更不會平白出讓。
皇位的傳承也不單純是皇帝自己的事情,這關乎到衆多的利益方。朱祁钰的皇位關乎到北京保衛戰主戰文官集團的利益,首先是他們不會輕易的答應皇權歸還給明英宗朱祁鎮;孫太後雖然是皇室的宗族共主,但是後宮不得幹政是老祖宗的鐵條,她更不可能出面讓朱祁钰把皇位還給自己的親兒子。她有那個心思,卻沒有那個權力。
最重要的是朱祁钰本人根本就沒想過要把皇位還給哥哥朱祁鎮,論能力來說,明英宗朱祁鎮給景泰帝朱祁钰提鞋都不配;按傳承,自朱祁鎮在土木堡被俘後,大明朝的皇位就從朱瞻基嫡長子一系傳到了庶次子一系中,沒有換位歸還的先例和祖制。當然朱祁钰對權力的控制欲才是最關鍵的,無論是孫太後也好,還是明英宗朱祁鎮也罷,不可能在正常的狀态下讓朱祁钰把皇位讓給朱祁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