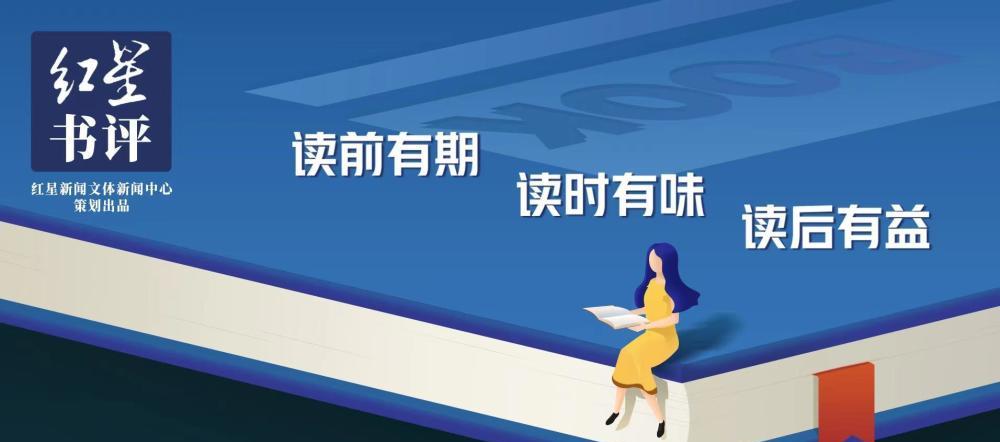
讀志筆記:時間的叙事
——序《成都市龍泉驿區文物志》
凸凹/文
時間把人類的事體浸泡、過濾、塑造成文化,文化又讓時間将自己滋養、窖藏、打磨成文明;而那些有色澤、有氣息、有斤兩、有尺寸的文明,又被時間風化、剝蝕和吹散;而一雙雙撲滿泥塵、浸漬汗水的手,又拼命在時間的大風中發掘、打撈、拼接,以愚公移山、螳臂擋車般的決絕讓時間慢下來——讓文明回到有形,讓文物回到文物。
讀《龍泉驿區文物志》付梓版,我看見了時間的量尺、刀片、書蟲、速度和易容術,更看見了一雙在時間的大海中撈針的手——龍泉驿區文物保護工作者的手。
這雙手,2003年,為龍泉驿捧回“全國文物工作先進縣(區)”招牌,今天,又為龍泉驿這片土地編了一本史無前例的書:一本收錄全面、事象公正、體例規範、行文精準的書。
這是一雙對得起時間、對得起先祖和後人、功莫大焉的手。
現在,讓我開始讀爬行在這雙手掌紋裡的岩石、陶瓷、銅鐵、土木和繁體字。
一、從非虛構到虛構的證詞與和解
“洛帶公園,成都市文物建築,1928年由時任洛帶團總、袍哥舵把子劉惠安集資修建,四川省最早的公署之一。園内的‘女茶社’,是過去客家婦女集中休閑品敬聊天的地方,不納男賓;淩翠樓為小青瓦四合院,樓上曾是龍泉驿區第一座圖書館,曾藏有《萬有文庫》等書籍,峨亭平劇社也曾在該處。”(《第五篇 其他文物保護工作》)
這段文字中的“劉惠安”“洛帶公園”“女茶社”,是非虛構的,搬遷到《甑子場》這本書中,就成了虛構,因有《甑子場》是一部比上邊摘錄文字長若幹倍的體量達三十多萬字的小說。劉惠安在小說這種虛構藝術中不叫劉惠安,叫安。他建公園,置藏書,修路搭橋,不準兵匪軍隊入場鎮,對保護古鎮會館等文物做出了自己事實上的貢獻。他的小老婆叫扣兒,龍潭寺客家女,則在公園女茶社倡新學,教一群鄉婦識文斷字,偶爾倚窗望鎮公所方向,懷想一位老男人的愛情。
我剛剛出版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湯湯水命——秦蜀郡守李冰》,則在這樣一段完全及物的叙述中找到了靈感與證詞:
龍泉驿區北幹道秦群墓于1992年3月20日在平安鄉永遠村8組(龍泉街道驿河社群)平天壩工地發現。共發掘清理墓葬34座,其中M1-M4已被破壞。
共出土遺物315件(不包含錢币和桃核),其中完整器物169件。随葬物均以陶器為多,次為銅器、鐵器、漆器、木器等,個别墓出“半兩”錢币。陶器有罐、都、釜、甕;漆器有孟,盒或厄;銅器有戈、矛、钺;鐵器有斧、鑿、铧等。所有這些出土物均具有戰國時期關中秦人遺物風格。在個别墓的木椁底闆上發現已與椁闆色澤相似的桃核、李子核及黃瓜籽,說明距今2300年左右這一地區的果木、蔬菜已有一定的發展。出土的帶倒鈎銅钺,體型不大,但具有極強的殺傷力。
這段出現在《第二篇 文物勘探與發掘》中的文字,在《四川通史》(羅開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成都通史》(羅開玉、謝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戰國晚期部分中,則是以十餘處文圖并茂的式态予以呈現的。為蜀地先秦砣砣霧一般的資訊提供物證,出土文物從成都東側方向斜插過來,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正是這束大地的證詞,讓我有了将《湯湯水命——秦蜀郡守李冰》中的好些場景東進至龍泉驿一帶的信心。于是乎,龍泉山、涼風垭、載天山莊、桃林坡、桤木河、牛鞞等地名走入了書中。我甚至将李冰與桃枭初戀的濫觞之地,設定在了可西眺成都城和雪山的長松山莊。
虛構的文字,遊魂一樣四處飄浮,終于找到自己非虛構的劃線、編碼與坑位。
二、文物從文物中走出
《第二篇 文物勘探與發掘》曰:
“2010年11月中旬,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在龍泉驿區十陵鎮青龍村文物勘探過程中發現一座大型磚室墓,在上報上級主管部門同意後,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進行搶救性發掘。據墓志記載,墓主人為後蜀宋王趙廷隐。”
趙廷隐,何許人?一代名将是也。五代時期,甘肅天水人,後蜀開國功臣。智謀雙全,後蜀高祖孟知祥麾下無人能及,建功累累。孟知祥去世,他與趙季良等受诏輔政。後蜀後主孟昶上位,加兼侍中,為六軍副使,晉升太傅。後趙廷隐申請退休隐居,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
最後的歸宿地在龍泉驿地層裡的趙廷隐,其長子叫趙崇祚。正是這個趙崇祚,編輯印行了在中國詞壇有着赫赫地位的《花間集》。該書收錄了溫庭筠、韋莊等18位花間詞派詩人的經典作品,開創了詩歌拓疆、再生一派的大革命。
趙廷隐古墓的出土,成為繼前蜀王建墓、後蜀孟知祥墓後,五代墓葬考古的第三大發現。
“明蜀王陵”是龍泉驿最早的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十年後的2006年,獲得這一殊榮、享受其待遇的是“洛帶會館建築群”。
“大明蜀僖王圹志”七個大字豎刻在碑額上,所有碑文字型隽永而清癯。正是這尊圹志,糾正了清代所修《明史·諸王世表》中把僖王朱友壎稱作朱友黨的訛誤。石碑是實心的,敲擊它,聽到的卻是中空的聲音,這讓遊人百思不解。
2017年8月25日,龍泉驿區洪河村14組,施勞工員在綠道改造過程中掘地兩米多後,發現了兩尊三彩俑。文物專家随後初步判斷,此處應有一片宋代墓葬群。8月28日,經國家文物局準許,搶救性發掘正式開始。至11月下旬,共清理宋代高氏家族墓葬14座。考古人員意外發現,其中一座,是北宋仁宗時期著名山水畫家高克明的墓葬。
現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溪山雪境圖》,正是出自高克明之手。高克明的繪畫成就,在當世便已得到公認。《宋朝名畫評》将其作品列為“妙品第一”。
結合出土文字材料,考古人員得知,高氏後裔本是山東渤海人,北宋時居于山西,後在南宋初年南遷至成都。
一鋤頭挖出個蜀王,一鋤頭挖出個武将,又一鋤頭挖出個畫家。龍泉驿土地到底埋藏有多少神奇與秘密,還有多少活兒在等待文物工作者去幹?
三、順流而下溯源而上的高光
現如今的龍泉驿是沒有一條像樣的河流的。但最早在龍泉驿山中鬧騰出動靜的,恰恰是兩條魚。
據《大事記》記載,第一條魚出現在一億年以前,細鱗、單尾、雙翅。“1992年3月:天峨鄉(後并入茶店鎮)成渝高速公路采石場,發現魚化石1件,長21厘米,寬8厘米,細鱗單尾雙翅,鑒定形成時間約1億年以上。”
第二條魚遊弋在七千萬年以前,它有着堅硬的鱗甲。“1975年11月:茶店鄉古井村4組出土7000萬年前(白垩紀)的硬鱗魚化石,魚體長34厘米,今存成都市博物館。”
與龍泉驿有關又被記載的,那個最古老的人叫蠶叢。龍泉山脈最高峰長松山周家梁子曾高高矗立着一座蠶叢王廟。後來,又坐落了一座長松寺。龍泉驿在唐天寶元年(742年)由東陽縣易名為靈池縣。《全唐詩》中現已查證無疑的與靈池有關的詩系李德裕、鄭谷和吳融三人所寫,計五首。其中三首,寫的就是長松寺的人與事。我多次踏勘現場,古垣肌理,殘磚碎瓦,至今猶存。目前的建築是原始楠木叢林中的一幢中西合璧的别墅“唯仁山莊”,由龍泉驿本籍著名軍閥田頌堯于1935年築,次年成,劉存厚題書莊名。此處還有一顆千年銀杏,當是龍泉驿地盤最古老、最粗大的植物。在成都地區極目遠眺、俯覽岷江流域、沱江流域和杜甫見過的一衆雪山,此處是上佳的選擇。周家梁子地望,既是龍泉驿地理的高點,又是文化的高點——它甚至還是龍泉驿得名的依據源。
“東漢末年(189-220):劉焉、劉璋割據政權下屬官宦,捐獻自己在獅子山上的房屋為家廟。蜀漢(221-263):漢将趙雲承襲該家廟,命名為靈音寺。”(《第三篇 不可移動文物》)靈音寺,也就是李劼人在《死水微瀾》中描寫過的至今香火綿盛的石經寺。
接下來出場的人物當是朱桃椎了。朱桃椎生活在隋末唐初,他先是學者型官員,後辭官落戶龍泉山中,千呼萬喚不出山從仕。“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他是有唐一代著名隐士,其文章代表作為《茅茨賦》。朱桃椎的事迹《大唐新語》《新唐書》《全唐文》等有記,而《二十五史 舊唐書》則列有其個人專傳。
《大事記》說:“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四川安撫使兼成都知府王剛中受宋高宗之命,到靈泉縣重修朱真人祠,即安靜觀。因為有皇太後懿旨和皇帝親自安排,人們稱其為‘皇家道觀’,也是龍泉驿古代所有祠堂當中最氣派壯觀的建築。” 朱真人,即後人對朱桃椎的尊稱。
唐、宋時期,龍泉驿來了兩個任武職(縣尉)的文人,前者段文昌,後者李流謙。段文昌,山西汾陽人,早年入韋臯幕府,後曆任靈池縣尉、登封縣尉、監察禦史、翰林學士等,官至宰相。任西川節度使期間,為成都女詩人薛濤建墓并撰墓志銘。段文昌著有文集三十卷、《诏诰》二十卷,還曾自編《食經》五十卷。《全唐文》收錄其文章四篇,《全唐詩》收錄其詩作四首。李流謙,德陽人,約宋高宗紹興中前後在世。蔭補将仕郎,授成都府靈泉縣尉。任職十六年後,去雅州履新學官之位。著有澹齊集八十一卷,有《國史經籍志》傳于世。
遺憾的是,這兩位父母官在龍泉驿留下的文物被時間收走了。所幸,殘破的古籍又用鐵定的文字鎖死了他們留在龍泉驿的蹤迹。
墓志銘為段文昌撰記的薛濤,其墓似有建在龍泉驿的可能。行走中國大地的美國著名學者比爾·波特在《尋人不遇——對中國古代詩人的朝聖之旅》一書中說,薛濤在望江樓的那處葬所是座虛墳。他根據清代《華陽志》所載之成都東南薛濤葬地“薛家巷”,請導航帶路,來到龍泉驿區大面街道青台山路“薛家巷”,找到“薛濤後人墓”,拍下了照片。
……順流而下,溯源而上,文物的出沒、行止,是時光大河跳出的高光,更是大浪淘沙蝶變中的吉光片裘。
四、文明走在大路上
一些文明沿着河流走,一些文明沿着驿道走。
龍泉驿的驿道叫東大路,由中路、南支路、北支路一主二輔三條構成。這個,連同堪輿學中的風水,大抵構成了龍泉驿文物的來路、走向和分布圖。
中路從成都東門“迎晖門”出發,過龍泉路,經牛市口、沙河鋪、黉門鋪,進入龍泉驿區境後,沿大面鋪、界牌鋪、龍泉驿、山泉鋪、柳溝鋪、茶店子,到南山鋪,出龍泉驿區境入簡陽境,過石盤鋪、赤水鋪、九曲鋪、石橋井,到陽安驿(簡州)。
北支路起自成都雙橋子,經萬年場、多寶寺、保和場、西河鎮、洛帶鎮進入龍泉山,再經馬口堰、陡溝子、義興場到止馬店。此後分為南北兩道:南下一道沿謝家溝、蘇家溝,經石盤鋪到簡州;東進一道,經蘭家溝、學堂灣至金堂五鳳,沿沱江西岸北上達金淵郡治同興場,再經養馬河抵簡州。亦可從五鳳溪乘船順沱江經内江、泸州入長江。
南支路上起成都東門,行至黉門鋪分路,經中和場、新店子,由雙流小堰口、龍泉驿柏合寺進入龍泉山。越過山脊又分為二道:南一道,過張家岩、高家場到達仁壽;東一道,經簡州老君井至賈家場,大體沿今成渝公路直達簡州。
清末,一位叫傅樵村的人遊走了一遍成渝古驿道,并把他走的裡程和站點記在了《成都通覽》一書中。彼時,東大路寬5—8尺,石闆路面,途經地域有龍泉驿、簡州、資陽、資州、内江、隆昌、榮昌、大足、永川、壁山、九龍坡,全程1071華裡。這位簡陽石盤鋪人氏累死累活走了114個站點也沒能将東大路走完,因為他隻走了東大路成渝段。要走完東大路全程,就得在重慶府朝天驿宿一夜起來繼續走,向東北方向走,經分水驿、墊江縣、梁山驿、萬縣、雲陽、奉節,抵達巫山小橋驿,才算走完。過巫山,一擡腿就踏入湖北境巴東縣了。東大路全程共設驿站17處。
能夠為東大路的曆史提供物證的,多虧了鄰縣的一塊古碑。資州獠井壩出土文物《陳君德政碑》載:“漢安長,蜀郡青衣陳君,省去根閣,令就土著郵亭。”古碑告訴我們,作為驿道的東大路最遲在漢代即已成形。至于它到底于何時成路、成驿道,則需要挖出另外的文物來發言。
一條東大路,連通了西南成渝兩座大城的血脈,打通了蜀文化與巴文化、成都平原與長江的關節。傳遞文化,架構文化,居功至偉。全國三千餘個縣級及縣級以上地域中,以驿命名的,僅龍泉驿一地而已。龍泉驿幅員556平方公裡,經濟總量居四川區縣第一。今天看來,沒有哪個驿的行政級别高于龍泉驿、地盤大于龍泉驿、影響強于龍泉驿。翻開《現代漢語詞典》,有對“驿”的注釋:“驿站。現在多用于地名:龍泉~(在四川)。” 這是說,在中國,能代表驿、說明驿、呈現驿的,隻有龍泉驿。稱龍泉驿為當今首驿,名正言順。
由是,談及龍泉驿文物,驿是繞不開的礁石。
1911年農曆八月十九日(公曆10月10日)夜,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昌打響。之後,各地紛紛舞旗應和,噼裡啪啦響起了推翻滿清的起義的槍聲。四川(川渝)起義的第一槍是九月十五,在一個驿站的所在地響起的,這個驿站就是龍泉驿。
我移居龍泉驿二十三年了,但我知道龍泉驿,卻是因為讀了李劼人先生的非虛構小說《大波》。先生對四川首義的發生及發生前後的情狀作了生動而細微的描寫。先生不僅讓我知道了龍泉驿站,還讓我知道了成渝古驿道——我第一次聽說時人口稱東大路的成渝古驿道就是《大波》告訴我的。
《大波》(第三部)在《在彙為洪流的道路上》《重慶在反正前後》兩章中,寫了随東路衛戍部司令駐紮龍泉驿的夏之時(留日歸來,革命黨人,時任四川新軍十七鎮步兵排長)如何在場上高升官站打響第一槍,如何起義,起義後又如何在短短時間内出任了蜀軍都督府副都督。
起義成功後,夏之時帶着6個大排共三百多号人的隊伍撤離龍泉驿,打着牽藤火把,在場東土地祠大黃桷樹處集合出發,朝着遠離省城成都趙爾豐的方向疾走,這樣就上了東大路。順東大路,過山泉鋪、石橋井,到了簡州。本欲經資州去自流井的夏之時,聽說清廷大臣端方率領的來川鎮壓“保路運動”的湖北兵沿東大路西行已到了資州,就決議避之而走川北道。義軍本欲繞樂至縣城行,卻在童家壩攔截了一郵差,拆開打了蠟印的郵袋看了密信後,便冒充省城援軍順手牽羊拿下了樂至縣城。因追兵逼近,到了安嶽後,本欲去川北或川南的夏之時,陰差陽錯向東南去了重慶方向。隊伍自驿道旁逸斜出,從潼南乘船順涪江而下,經銅梁,在合川入嘉陵江達重慶。兵臨城下時,隊伍已達八百多人,加上非戰鬥人員,共有一千四百餘衆。見義軍到,城中同盟會立即宣布重慶獨立。十月初二日,隊伍過浮圖關,經通遠門(西門)入重慶城。
《第三篇 不可移動文物》落地有聲指出:“辛亥革命四川首義舊址一共包括2個地方,分别位于龍泉中街99号附近及龍泉驿區鷗鵬大道街原龍泉第一人民醫院黃葛樹旁。”
位于東大路旁邊的北周文王碑,是龍泉驿最早(1961年)被評定公布的、級别最高(省級)的文保機關。在一塊岩石上刻字的主持人叫強獨樂。強獨樂的官位有幾多呢?大周使持節、車騎大将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軍都縣開國伯。嗯,就這麼多,六個。刻碑的字有幾好呢?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贊其“精美之獨樂”。此碑文史價值有幾高呢?碑文糾正了後世對北周政權創始者宇文泰生平事迹記載的諸多謬誤。
在車辚辚馬蕭蕭的聲浪中,我們看見明将成都衛指揮翟英,以戰死的豪氣扼守着敵軍進犯成都之路;看見朱德、劉伯承在柳溝鋪一帶彰顯着鐵血與軍事才幹;看見1910年,九歲的陳毅沿東路走來,随父遷家成都上國小;看見1913 年赴日留學的二十一歲的郭沫若,在《初出夔門》裡給父母信中寫道:“男第八号由成都出發……是日即宿茶店子。九号由小東路進行,宿龍泉寺……”;看見駐石經寺的國民黨胡宗南部一個團就地起義;看見國民政府軍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在大面鋪通電起義,使龍泉驿得以與成都城同一天和平解放……
而盤坐在四百裡龍泉山脈最高峰長松山頂的蠶叢王廟的瓦楞及牆磚,則看見了這樣的壯麗畫面:一隊又一隊人馬,沿着古今道路,從四面八方湧向龍泉驿。最先湧來的是入蜀的秦人及遷蜀的山東六國人(富豪、工匠與罪犯),跟着是建立蜀漢政權的異鄉人。在荒無人煙、虎豹滞城的時代,迎來了湖廣填川的洪流。改革開放後,尤其成都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後,來龍泉驿創業、開發的隊伍更是源源不斷氣勢如虹。由此實作的,一汽、二汽、吉利、大運等企業的入駐,讓漢代成都的“車官城”得以玩了個穿越式的東進,并以時尚現代的形态成為閃電般的燦爛複活。
其實,早在龍泉驿設立官馬驿道之前,就有了路了,就有了人衆了。那條路覆寫在東大路北支路上,被稱為最早的南方絲綢之路東路。
從南絲路始點成都錦官城出發,沿着“蜀-身毒道”南去,共有西路、中路、東路三條路可供行旅。東路,又稱沱江道,沿東大路北道至簡陽,經資陽、内江、自貢達泸州,之後分東西兩道。東道從貴州畢節、遵義穿過到達廣西,再到交趾(越南)、廣州出海向太平洋;西道過永甯河,通過貴州畢節和六盤水,到達雲南昭通,再過曲靖、大理。之後,走永昌道,經緬甸八莫抵印度。再行,則可至中亞、歐洲。
五、作為文物的讀者
《第一篇 機構與管理》在“經開區文化體育和旅遊局文物相關内設科室曆屆上司”一節中顯示,2001—2012年,該局沒有設定文物科。而本人大約在2001—2009年,正擔任着該局文化科負責人一職。就是說,我也曾兼幹過一點文物保護工作的活兒。但更多的是讀者的身份。
作為文物的讀者,從《龍泉驿區文物志》中,我讀到了美好、愉悅、欣慰,但也讀到了一些遺憾、惋惜和疼痛。
《大事記》載:“1956年10月:成都市人民委員會發出《關于在工農業生産建設中注意保護文物的通知》。同年,紅衛兵損毀石經寺楚山紹琦禅師肉身像。”又載:“1985年8月1日:成都市政府頒發《成都市文物保護管理辦法》。同年,區糧食局拆除龍泉武廟修建宿舍,餘下臨街吊腳樓七間。”
一雙手在拚命保護、修複,一雙手在拚命不保護甚至拆毀。
《大事記》載:
“1988年5月:龍泉驿區人民政府準許公布藥王廟、桃花寺大殿、蘇家溝摩崖造像、木魚山摩崖造像、觀音岩摩崖造像、清音溪摩崖造像、玉皇觀石像、湯家河崖墓群、四十梯崖墓群、田氏支祠、董朗故居為文物保護機關。”
董朗,何許人?龍泉驿人董朗,1923年在上海大中華紗廠做工運時加入中國共産黨,龍泉驿首位共産黨員。黃埔一期學員。曾參加平定商團、兩次東征、北伐、南昌起義、上海中央特科等革命活動。曆任省港大罷工勞工武裝糾察隊隊長,黃埔軍校教導團騎兵隊副隊長,葉挺獨立團參謀、黨支部組織幹事,國民革命軍24師70團團長,紅二師師長,中央軍委特派員,紅四軍(軍長為賀龍)參謀長等職。中國工農紅軍早期上司人之一,海陸豐、湘鄂西兩大蘇區重要建立者與上司人(與彭湃共同上司)。成都地區最進階别紅軍将領。離世後,毛澤東為其妻兒簽署頒發烈士家屬證。周恩來、董必武、陳赓、賀龍、徐向前等上司和戰友先後寫材料回憶和贊頌。聶榮臻元帥為其題詞。
但現在,我們又能在哪裡找到“董朗故居”的一磚一瓦?
但這或許隻是個别現象。但我真希望此類現象今後不再發生。
作為文物的讀者,我從《龍泉驿區文物志》中更多的是讀到了一顆一顆釘死時間的釘子——文物工作者的那些匠心、艱辛與努力。謝謝編者。
謝謝編者。作為文物的讀者,你們讓我從遙遠、殘損、冰冷的文物身上,讀出了睫毛、顔值、骨肉與溫軟。
我知道,文物是你們的親人。
《成都市龍泉驿區文物志》
編撰:龍泉驿區文化體育和旅遊局
出版:成都時代出版社
本文作者簡介:
凸凹,本名魏平。詩人、小說家、編劇。成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紅星新聞記者 邱峻峰
編輯 段雪瑩
(下載下傳紅星新聞,報料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