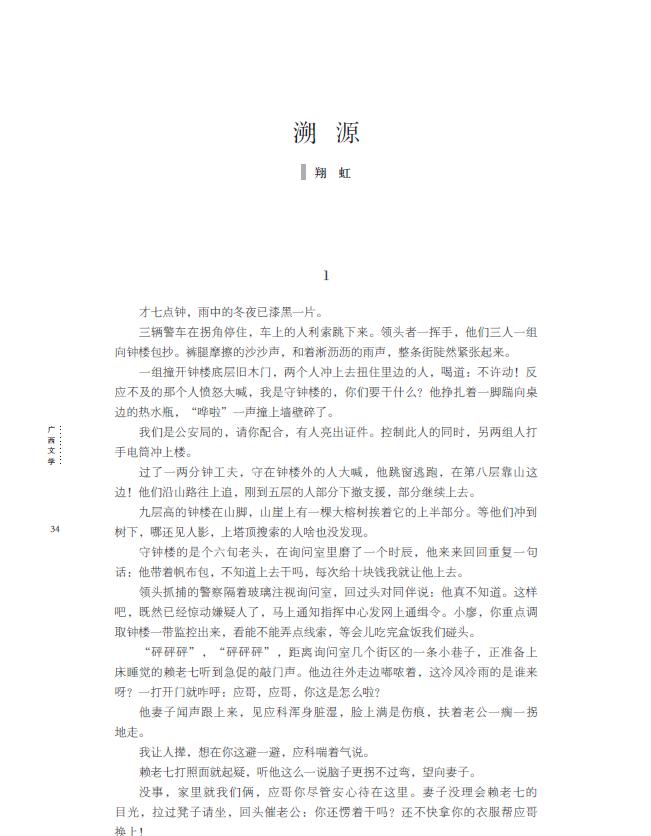
《廣西文學》2021年第10期刊發廣西作家翔虹小說《溯源》。《廣西文學》供圖
小說不得不撲朔迷離。撲朔迷離仿佛是小說的最初标配和最終必須條件。
廣西的很多小說家都迷戀撲朔迷離。凡一平的早期作品《尋槍》因為撲朔迷離主旨深藏而被陸川、姜文他們青睐有加,搬上銀幕大獲票房;東西近期的長篇《回響》因為撲朔迷離,令人猜想不已,欲罷不能,且好評如潮;就是朱山坡也熱愛撲朔迷離,他的《陪夜的女人》白霧迷離、大地蒼茫、河水纏綿、老船漂浮,我看一次高興一次,看兩次點贊三次。他們仨不像黃佩華他們仨:黃佩華也有引人入勝的壯鄉舊事,譬如《河之上》;紅日作品不乏妙趣橫生的山間橋事野徑,《碼頭》就是;李約熱總有溫暖、溫馨、幽默慢慢溢出故事外面的野馬鎮新事舊聞,盡在《人間消息》。
翔虹明顯地有别于他們六位:《溯源》颠覆了我對翔虹小說的所有認知——撲朔迷離的現代故事,涉及鄉村鄉野、城鄉結合部、礦井礦窿,鐘樓、别墅、官場以及黑社會,還有保護傘,不一而足。
《溯源》把世界的暗角呈現得有如小說中的鐘樓,一層有一層的秘密,一層比一層危險,當然是一層比一層驚心,一層比一層動魄,層層有機關,步步可驚心。危機四伏,八方有耳。包抄和脫險;逃離到省城;舉報,以及帆布袋;被拘,戴上手铐和那場械鬥;舉報和舉報材料;實話實說還是不實話實說……誰是最應該戴上手铐的人?難道是貫穿小說的應科?
關于《溯源》的撲朔迷離,存在多重隐喻是毫無疑問的。
通緝犯應科在鐘樓被包抄,賴老七幫助應科脫險;應科喬裝打扮乘坐機車逃到省城;應科攔車向首長舉報,舉報材料就在帆布袋裡;應科被拘在飯店裡;應科遭遇一場導緻血案命案的械鬥,應科以為源頭之外另有源頭;應科企圖溯源到豪宅卻挨揍,應科老婆關荷被劫持綁架下落不明;應科繼續企圖溯源卻發現豪宅另有秘密;應科老婆、孩子安全脫險;應科和賈軍堪稱生死之交,但賈軍可能是源頭之源,應科要不要說出賈軍以完成自我救贖?
小說注重對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通過描摹應科夫妻面對災難性攻擊時的狀态,将他們對世道變故的畏懼與無奈細緻而透徹地展露出來。店鋪被暴徒摧殘甚至摧毀給他們帶來心靈的創傷,他們或是尖叫着,或是哭着……他們百思不解,他們想方設法找到原因源頭。當所有的生命和意義之源被摧毀,他們依然勇敢地追尋希望尋求慰藉。
翔虹的《溯源》讓我想起了博爾赫斯的小說名篇《南方》。
《南方》隻有四千多字:達爾曼在回家的樓梯上額頭被割破,差點得了敗血病,住院治療後終于好了。他要遠離布宜諾斯艾利斯,回到南方自己的莊園去休養。 一路之上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馬上就要到家了,他在一個小酒館裡由于誤會,介入進了一場毫無希望的單挑,拿着别人給他的匕首,向決鬥的平原走去。故事就此結束。應科有點像達爾曼。
《溯源》以“溯源”為寫作任務,在讀者以為看到源頭的時候,宕開一筆,使得“源外有源”“洞中有洞”,仿佛生物多樣性——《溯源》的隐喻性非常明顯:應科隻是人性善惡的一個代表而已。人性無論善惡,總有源頭可溯。源外還有源,或者源外另有源,才是我們追溯的目标,以及方向。事實上,翔虹并沒有把他追溯到的源頭告訴讀者,我讀完之後也還是雲裡霧裡,不見謎底,這就是撲朔迷離小說應有的效應:應科戴的手铐戴到别人手上了。誰知道那個後來戴手铐的不是應科呢?真的是應科他嗎?我第二次拜讀《溯源》之後就冒出這樣的疑惑:也許應科早就死在飯店裡,逃出來的不過是他的幻影,也可能是他臨死前太過于強烈的欲望。
《南方》的達爾曼要到南方去休養——這是一次平淡的旅程。達爾曼當然希望如此。他安穩地坐在車廂中閑适地浏覽風景,享用午餐。他的心理雖然有着病後初愈的興奮,卻又深沉緩慢,沉浸在那種安穩于平淡中(在我第一次并不細緻的閱讀中,我一直認為他是個上了很大年歲的老頭,到第二遍細讀時才發覺未必如此)。《溯源》的應科被圍捕,卻幸運地逃脫,他要到省城去舉報他知道的一切。他到底知道什麼?他的帆布袋裡有什麼?翔虹不動聲色也不露聲色。他故意讓小說有如謎語,或者是歇後語。
博爾赫斯在細膩的文字裡埋下的張力,就像是達爾曼的一生。南方是回歸血性的象征,也是對命運抗争的象征。看似不動聲色實則充滿暗湧,語言精彩,故事也是。老博把一個看似平淡的故事寫成了奇葩。《溯源》何嘗不是奇葩?
其實,《溯源》和《南方》頗為類似。或者可以這樣說,作為短篇精制的《溯源》,叙述上惜墨如金,語言上精雕細刻,頗有博氏風格。翔虹從頭到尾,守口如瓶——也很像博氏。
我們對惡之源的追溯往往是淺嘗辄止的。翔虹的《溯源》為我們提供了溯源的全新模式。在這個全新模式的引領之下,我們逐漸發現,原來惡之源别有洞天:高大巍峨的宅院裡隐藏着巨大的不為人知的秘密,仿佛古代宮殿裡的刀光劍影,長期在現代螢幕銀幕上閃閃爍爍,真相很難大白,千年前後依舊如此。《溯源》警示我們:溯源不能也不應該淺嘗辄止,那是一種徒勞,一種無用功,甚至可能會是另外一種助纣為虐。
《溯源》告誡世人:這個世界的惡,譬如恐怖集團恐怖分子的為非作歹,其源頭絕不在我們可以想象的範圍之内。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惡,來自遠古,來自遠方,那個遠古有多遠?那個遠方有多遠?誰都不知道。惡制造的無辜者有時永遠是無辜者——他們自始至終無助無力無望,也無奈,并且無能,他們渴望渴求的公平正義常常遲遲不到,也可能永遠都不會到來,就像那個一直被等待的戈多。
人類和所有的源頭周旋,殊不知源頭永遠是源頭,逆流而上尋尋覓覓人們依然空手而歸。翔虹能夠給予人類的答案是:源頭好像是應科看見或者戴過的那副手铐,手铐從此手移動到彼手:“應科仍然清楚看見為首那位指間的手铐,那是才離開自己雙手不久的鐐铐。”源頭是那雙誰也看不見的黑手吧?
《溯源》用汪曾祺式的短句善意叮囑世人:溯源路漫漫,而且荊棘密布,而且,權衡研判如影随形。最為饒有意味的句段莫過于此——
他剛回到房間,兩個從業人員後腳跟了進來。為首的給應科倒了杯水,嚴肅地問,你和岑西市警察局緝毒支隊長賈軍熟悉嗎?
我、我和他不太熟悉……
真的嗎?你知道規矩,必須如實講話。
我們認識,但真的不熟悉。應科不結巴了,但聲音仍然細如蚊叫。
看來你還沒想好。這樣吧,你慢慢想,想起什麼了明天早上再告訴我們。他轉身之前,饒有意味地看一眼應科,帶上門的聲音挺響。
就是這個句段,把應科推到進退兩難的境地,他為此飽受煎熬寝食難安,他“撓頭捶肩”,不知如何才好。
以下是新聞報道關于黑惡勢力和官場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司空見慣的描述——
上述官員告訴記者,李本人究竟和李氏兄弟有沒有聯系,還有待進一步調查。但作為一市之長,讓治下的黑惡勢力發展到如此觸目驚心的程度,李本人起碼要承擔失職的責任。還有毛某烈、譚某和等人,也是李一手提拔的。
遺憾的是,新聞報道基本上沒有,也無法溯源。
小說《溯源》的溯源,也隻能在應該戛然而止的時候戛然而止。
無法戛然而止的,隻能是讀者。
(作者簡介:藍寶生,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文藝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