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泰山文藝獎(文學創作獎)出爐,濰坊市文聯推送的高玉寶的長篇小說《白銀火車》、黃浩的詩歌《時光錯》、王威的短篇小說《如果你看到易生在笑》、李桂華的報告文學《種·夢》均獲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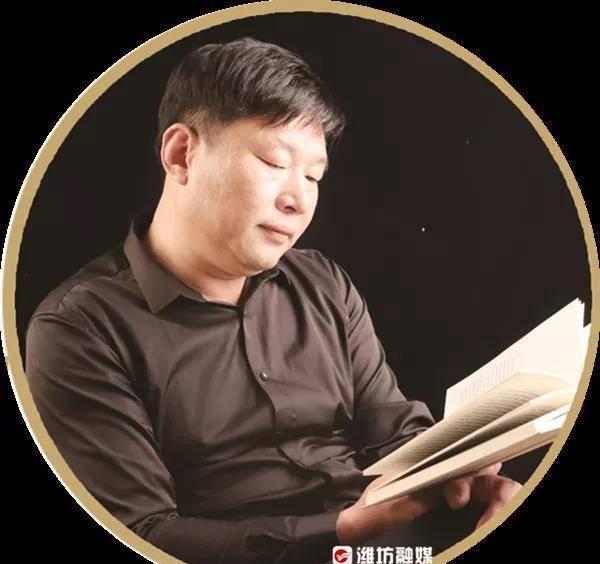
47歲的高密作家高玉寶是一名鐵路職工,二十多年來,他在一道道鐵軌上感受社會發展的速度,見證時代變遷。一直熱衷于文學的他,以鐵路生活為背景,刻畫人性,記錄時代,創作出了長篇小說《白銀火車》。
曆時三年創作
獻禮中國鐵路
“寫作既是生活經驗的一種積累,也是一種提煉。”高玉寶說道,《白銀火車》是一篇關于鐵路的長篇小說,來源于他多年寫作和生活經驗的積累。
高玉寶在學生時代喜歡寫詩歌,在學校成立文學社,還曾發表過多篇詩歌。“我的創作時間與我的工齡相近。”1995年,高玉寶從學校畢業後成為一名鐵路勞工,剛參加工作時就在一個四等小站上,四面曠野,田間種了許多農作物,當地的村民非常善良質樸,這些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鐵路生活本身就是創作的富礦。高玉寶在小站幹車站值班員,上一個白班和一個夜班,就可以休息兩天,因而有大把的時間可以讀書和寫作。
二十多年時間裡,從綠皮火車到風馳電掣的高速鐵路,中國鐵路發生了巨變,高玉寶是一名親身經曆者和見證者。2014年,他突然有了想寫一部鐵路題材小說的想法,于是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白銀火車》。
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創作過程中着實吃了不少苦。三年間,高玉寶仿佛與《白銀火車》談了一場戀愛,他一面專注寫作,一面考證推敲寫作中的細節,費盡心思把時間挖得更準,把人物刻畫得更真,把時代诠釋得更深刻,最終才寫成了這部15萬字的小說。
立足現實生活
寫好身邊故事
《白銀火車》背景發生在改革開放初期,講述了在膠濟鐵路線上一個四等小站——白雲火車站上,扳道員、段長、站長以及職工等人之間,工作、生活和愛情的故事。
“鐵路隻是時代的背景,人物才是這個時代的主角。”高玉寶說,《白銀火車》裡的人物可以說在現實中都有一個原型,他們有職責和擔當,也有迷茫和彷徨。“這部小說我改了許多次,也許改動的空間仍然很大,但我對于小說的結局非常喜歡。”高玉寶表示,他的作品沒有所謂的“劇終”或者“大圓滿”的結局,經曆了這樣那樣的人生之後,他們一直在懷揣夢想前進,這就是他想表達的。
談及未來創作,高玉寶表示還是要立足于現實生活的點滴,從形形色色的小事件、小人物中,挖掘平凡又有意義的題材,為讀者獻上具有生命力的文學作品。
王威是齊魯文化(濰坊)生态保護區服務中心文藝創作部的一名創作員。從發表第一篇作品《槐根》到獲得“泰山文藝獎”的《如果你看到易生在笑》,王威總是用樸素的叙事,洞察并挖掘底層人物悲喜,展現人性關懷。
作品反映少年兒童的悲喜
王威所著的短篇小說《如果你看到易生在笑》于2019年刊發于《上海文學》。小說以第一人稱的形式講述了兩個家庭環境特殊的小男孩的故事:他們的友誼,他們的悲傷、喜悅以及他們用弱小的身軀和信念來對抗生活中的不滿意。整篇小說以一種類似于旁觀和畫外音的形式展開,叙事冷靜,節奏輕盈跳躍而又顯得從容不迫。
王威的作品通常是反映社會底層的生活,勾勒底層人群悲喜交集的命運狀态。前幾年,王威在生活以及新聞中時常看到一些問題少年的事迹,這些事情總是讓她揪心。于是王威想寫一部關于青少年題材的作品。2018年年末,她用一周的時間,寫出了近萬字的短篇小說《如果你看到易生在笑》。
“我希望通過作品讓社會關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他們可能叛逆,但是他們也有善良和無助的一面。”王威表示,在集中寫作的一周裡,自己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在作品中的少年身上。“我不會提前設定提綱和故事走向,在寫作時随着感情和人物走。”王威說。
從《紅樓夢》進入文學世界
王威真正開始邁進文學大門是從看《紅樓夢》開始的。國小四年級時的一天,她去給家裡買豬肉,肉攤的隔壁是租賃舊書的小書屋。書架前,她提着用麻繩拴着的一斤豬肉,轉來轉去找書看,在書屋裡發現了一套程乙本的《紅樓夢》。不記得那塊豬肉下場如何了,王威隻記得站在書架前,被林黛玉的“偷得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驚得呼吸不暢。世界上怎麼可以有這麼美的詩?語言已經不能表達她那刻的心情了。于是,一天5分錢的租賃費,她一本本往家租借。後來小書屋要關門了,她以後就不能繼續看《紅樓夢》了,她決定将這套書買回家。這套書老闆賣10元錢,當時買一斤豬肉才1.1元。她拿出了全部的零花錢,并靠爸爸的一部分資助将其買回了家。“随着年齡的增長,我寫了很多東西,也丢失了很多東西,可是這套《紅樓夢》卻一直留在我身邊。時光把紙張烙黃變脆了,可它們依舊滿腹經綸,陪伴我在文學的路上孤獨前行。”王威表示。
胖胖的身材,白皙的皮膚,這樣形象的黃浩令人很難與詩人聯系到一起,而且是有點俠氣的詩人。年輕時愛寫金戈鐵馬、快意恩仇的他,在四十歲後關心起了身邊的人、事、物。《時光錯》更多的是講述這些年他在時光裡的遇見和錯過。
從小熱愛詩詞
自诩“梁山第109人”
“浩幼時家貧,中年後汲汲于富貴,常著豪放或婉約小詩,熱愛世俗生活,因向往水浒故事,故自号‘梁山第109人’,聊以自慰。”這是黃浩在他詩集作者介紹部分自我評價的一句話。
1972年,黃浩出生于諸城,一直對詩歌情有獨鐘。1991年,他聯考落榜,就在諸城一冷清的街角開了一家叫做“星星”的書屋。書屋是用水泥預制闆組合起來的,也就十多個平方米。黃浩總是依偎在簡易的櫃台旁,捧着一本書,興緻盎然地閱讀着。在小書屋裡,黃浩把青春的彷徨、苦澀、無奈以及對未來的豪情壯志,變成了一句句詩行。他和小夥伴還組建了一個名叫“五月”的文學社,漸漸地,黃浩的詩歌在同學朋友們的小圈子裡也開始小有名氣。他的一些文字,開始零星出現于國内的文學刊物或報端。
1992年,父親因工作的原因決定全家搬到陝西生活,20歲的黃浩選擇獨自留在諸城老家。為了生計,他在諸城市的龍城市場擺過地攤兒,賣過筆和本子,做過很多工作,積累了一定财富。2000年,他在諸城着手創辦工廠,主要做與污水治理行業相關的器械裝置。過去的20年裡,黃浩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條的同時也沒有放棄小說和詩歌的創作。
想寫一部關于家鄉的長篇小說
近兩年,黃浩身邊發生了很多事情,親人離世,疫情影響下身邊不少企業面臨破産等,黃浩在寫作靈感與素材的選擇上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年輕時候,寫詩歌的素材都是憑空想象的,比如英雄豪傑的事迹。過了四十歲寫的更多的是最基本的東西,家鄉悲憫的小人物、山上的小草小花、八月十五的月亮,母親的唠唠叨叨,都能讓我寫出東西。”黃浩說,《時光錯》這本詩集更多的是這個時期的作品,他将自己生活中的所感所悟和内心的掙紮用詩歌的形式呐喊出來。
作為一名有着詩意情懷的企業家,黃浩有自己的期待和規劃:“我正在寫一本長篇小說,這是我20年前開始寫的,我想要把濰河灘上的故事、諸城英雄人物的喜悅、憂傷、善惡、愛恨情仇都寫出來。現在所有的素材都準備好了,并且也着手寫了一部分。但是我不急于出版,因為我覺得自己還需要繼續沉澱和積累。”
生于農村、長于農村,鄉村情感成為李桂華生命裡流動的基因和密碼。“要為國産蔬菜種子寫一本書”,采訪人物、翻閱書籍、親自試驗,積累十年後,她完成了《種·夢》。
積累十年後才動筆寫作
1971年出生的李桂華生長于中國蔬菜之鄉壽光,從小聽老人們講着農業故事長大。1998年,李桂華成為了一名媒體工作者,她也把關注點放在鄉村、農業和農人身上。
說起寫《種·夢》這個作品,要追溯到2006年4月,李桂華在壽光一家良種試驗基地見到三個品種的五彩櫻桃番茄,一串一串躺在展示托盤裡。每一個彩色番茄的身上都反射着光點,這“點燃”了她的眼,内心紮根了一個念頭:要為國産蔬菜種子寫一本書。她從壽光的國産蔬菜種子研發作為切入點,從2006年開始,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機會和時間,采訪人物,翻閱書籍增強專業性,一直持續積累了10年時間,2016年10月才動筆寫,2017年8月完成了這部22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著名評論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李炳銀評價道,這個題材的長篇報告文學,《種·夢》是他目前見到的國内第一部,特别是像這種問題性報告文學,也展現了作者的國之責任和為民情懷。
為獲素材自己租地種菜
為了采訪到更加詳實、準确的素材,她想盡了辦法。“寫報告文學必須到現場,必須真實,掌握的是第一現場,第一手資料。像我這個上班族,就必須利用周末、節假日以及年假等工作之外的業餘時間。”李桂華說,為了自己能随時跑村子和蔬菜基地,原本拿着駕照卻開車不熟練的她硬是把車技也練出來了。
為增加對蔬菜、農業的深入體驗,李桂華當起了“農民”,在離壽光城區20公裡的一處農莊,租下了幾分地,種植二十多種蔬菜,通過種植、管理、收獲這個過程,更具體、直覺地了解、驗證自己采訪過的相關素材資料。在這個過程中,李桂華還和周邊農民交流、和技術人員溝通。種菜,變成了一種采訪,她對相關素材資料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
最終,她積累了60多萬字的相關資料,采訪人物170多位,留下了7萬多字的采訪筆記和閱讀筆記,足迹遍及省内濟南、萊州、聊城等地,省外的雲南、湖南、河北、北京、上海等地,直接采訪了從院士到種菜農民等大量相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