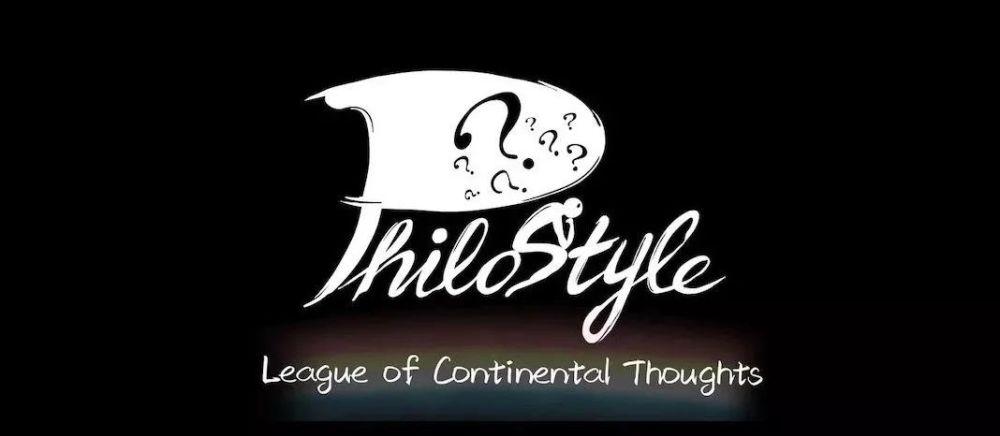
序章
魯迅寫過一句話,“隻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1929)。
如今回想魯迅的一生,腦海中浮現的便是這句話。這短短的一句中包含了一種生存方式。我想要闡述的,也正是這句話呈現的生存方式的具體内涵。換言之,在思考魯迅的人生時有幾個可以被料想到的視角,而我試圖思考的立足點是:作為一個将過渡性中間物視為自身命運并加以承擔的人,他是如何在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
我們人類的曆史,會出現一種正如其字面意義那樣可被稱為 “過渡期”的時代。在長達三千年的時間裡,位于亞洲東部、幅員遼闊的中國一直以周邊各國難以匹敵的文化為傲。然而,19 世 紀中葉的鴉片戰争以來,中國在西歐的沖擊下動搖、苦悶、摸索,這一長達百年的激蕩曆史或許正是這種過渡期的典型代表。出生于1881年、逝世于1936年的魯迅,恰恰生活在這段過渡期當中。在魯迅的一生中,與其說他常常不得不意識到自己是一種過渡性的中間物,不如說他主動背負了自己作為中間物的命運而活着。
作為一名文學家,魯迅有意識地開始創作是在他迎來二十六歲的 1907 年(明治四十年),當時他正在東京留學。魯迅這一時 期的代表作是《摩羅詩力說》(1907),這篇評論第一次向中國系 統地介紹了八位歐洲浪漫派詩人的詩作及生平。在文章的末尾, 魯迅談到了花的意象。
俄文人凱羅連珂(V.Korolenko)作《末光》一書,有記老人教童子讀書于鮮卑者,曰,書中述櫻花黃鳥,而鮮卑 沍寒,不有此也。翁則解之曰,此鳥即止于櫻木,引吭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處蕭條之中,即不誠聞其好音,亦當得先覺之诠解;而先覺之聲,乃又不來破中 國之蕭條也。然則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最後的光芒》是柯羅連科根據自己流放時期的經曆寫成的 《西伯利亞故事》中的一篇,描繪了一個流放者家庭的生活。正如 “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楚辭·遠遊》)的詩句所詠, “蕭條”與“寂漠”都表示毫無生機的荒蕪景象帶來的凄涼感覺。在魯迅的作品中,“寂漠”一詞頻頻出現。盡管寂寞是潛藏在魯迅 早期作品中的底色,但此處青年魯迅為了沖破當時重重封閉的中國而尋求新聲和光明時的寂寞與渴望,與那少年身在荒涼的西伯 利亞,思念着素未見聞的櫻花和鳥鳴時的身影重疊,令讀者深思。緊接着在《破惡聲論》(1908)中,魯迅闡述了他對新聲和光明的希望。
“吾未絕大冀于方來,則思聆知者之心聲而相觀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聲者,離僞詐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發于孟春,而百卉為之萌動,曙色東作,深夜逝矣。”“心聲”意為 精神的呼聲,“内曜”是指精神發出的光芒。“心聲”“内曜”這簡潔有力四個字,是當時的魯迅對文學最根本的定義。而“百卉為 之萌動”的季節,則是他心中描畫的沖破寂寞之後的光景。然而, 他們在東京的文學運動早早夭折。滿懷悲傷的魯迅選擇回國。在其後将近十年裡,除了辛亥革命(1911)前後發表的幾篇文章外, 魯迅一直處于沉寂。而打破這一沉寂的,是 1918 年他以“魯迅” 之名寫下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在寫給日本人青木正兒的書信(1920 年 12 月4 日)中,魯迅留下了一段直接談及《狂人日記》寫作動機的話語。自 1917 年起,身在日本的青木正兒就非常關注中國的“文學革命”,其發表于 1920 年的《将胡适漩在中心 的文學革命》詳細論述了中國新文學誕生初期的文學創作,是一篇值得紀念的評論文章。青木正兒将登載這篇文章的《支那學》雜志贈與魯迅,魯迅的信是對此的感謝函。他在信中也談到了歌與花的意象。
我寫的小說是極幼稚的,隻是為本國如凜冬一般既無歌唱,亦無鮮花而悲傷,是為沖破這寂寞而寫的……
為了沖破當時中國如凜冬一般既無歌唱亦無鮮花的寂寞,魯迅以這篇《狂人日記》為開端,不斷寫作直至去世。
魯迅留下的著作、翻譯多達700 餘萬字。在此先将其列舉如下(括号内時間為出版年份,* 号表示逝世後出版):
(一)小說集三種,《呐喊》(1923)、《彷徨》(1926)、《故事新 編》(1936);
(二)散文詩集一種,《野草》(1927);
(三)回憶文集一種,《朝花夕拾》(1928);
(四)評論、 雜文集 16 種,《熱風 》(1925)、《華蓋集》(1926)、《華蓋集續編》《墳》(1927)、《而已集》(1928)、《三閑 集》《二心集》(1932)、《僞自由書》(1933)、《南腔北調集》《準風 月談》(1934)、《集外集》(1935)、《花邊文學》(1936)、《且介亭 雜文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且介亭雜文末編 *》(1937)、《集外集拾遺 *》(1938);
(五)詩 70 餘首;
(六)輯錄、校勘古籍十餘種,《唐宋傳奇集(上·下)》 (1927—1928)、《嵇康集 *》《古小說鈎沉 *》(1938),等等;
(七)學術著作兩種,《中國小說史略(上·下)》(1923— 1924)、《漢文學史綱要 *》(1938);
(八)翻譯 33 冊;
(九)書信集一種,《兩地書》(1933,與許廣平的往來書信集)。
在被公認為過渡期或啟蒙期的時代裡,總是會誕生一些堪稱 “巨人”的人物。一般來說,這些巨人關注的并不局限于某個狹窄 的特定領域,而是指向整個社會與曆史。魯迅亦是如此。魯迅的評論和雜文主題涉及文藝、美術、思想、曆史、民俗、自然科學、社會、時事等多個方面。翻譯是魯迅年輕時起就最為重視的工作。通過他的譯筆,14 個國家、近百位作家的作品被介紹到中國,體 裁涉及小說、童話、散文、文藝理論、美術史論,甚至還有《藥 用植物》這類科學書籍。晚年的魯迅還曾計劃翻譯法布爾的《昆蟲記》。魯迅主編或參與編輯的雜志共有 20 多種。不僅如此,他 還是中國美術界成果最豐富的木刻(版畫)運動的理論指導者。
魯迅逝世後,名為《魯迅全集》的著作集曾分别于 1938、1958、1973、1981 年四度出版。1973 年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 命”時期,盡管這一年出版的《魯迅全集》不過是 1938 年版的重 印,但也是出于當時的需求。無論如何,全集能在其去世後的45年裡四度出版,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魯迅在中國的地位。尤其是 1981 年為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而發行的最新版《魯迅全集》 (全 16卷),不但收錄了上述著作清單中除(六)(八)之外的所 有作品[僅将(六)(八)中作品的序、跋彙編為其中一卷],還增加了魯迅 1912 至 1936 年(缺1922 年)的日記及 1456 封書信。包括書信、日記在内,所有魯迅作品中合共添加了 2.3 萬條注釋, 完成這項工作需要耗時大約十年。魯迅的文章旁征博引,涵蓋古 今中外,而且措辭大多帶有文言色彩,讓年輕一代對魯迅的作品敬而遠之。其中涉及的人物、團體、曆史事件、出版物、引用句 子的典故、已成為過去的風俗習慣,但對這些内容加上注解後, 隻要讀者肯花些工夫,或許就可以輕松地走入作品并與其共同思考。
在論争文章中大量引用對手的話是魯迅作品的一大特色。這 也是魯迅本人在晚年的雜文集中嘗試的做法。曾受過魯迅親自教導的增田涉寫道,“他将自己的人生意義寄托于寫作以及将作品呈 現給世界”,“他對所寫的文章,并非經選擇後再出版,而是将所 寫的一切原封不動、一字不落地投向世間”(《魯迅的印象》)。魯迅就是這樣一位文學家。如将最新版的《魯迅全集》、1958 年出 版的《魯迅譯文集》,以及上述清單(六)中的作品結合在一起, 10 明暗之間:魯迅傳 我們就能接近魯迅創作生涯的全貌。此外,由于很多人都寫過關 于魯迅的回憶文章,我們能夠從中了解魯迅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活的時代。
《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濫觞之作。青木正兒在上文提 及的論文中評論了《狂人日記》,認為“魯迅在小說方面是一位頗 具前途的作家”。這部小說的日譯版在文庫本中的篇幅不足 20 頁, 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它的問世所呈現的劃時代意義已變得愈發顯著。魯迅的代表作《阿 Q 正傳》已被翻譯成 40多個國家的60 多種語言,它與魯迅的名字一同在世界文學中占據着不可動搖的地位。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為中國現代小說研究開辟道路的學術著作,作為一部基于獨創性曆史觀和實證性研究的通史,時至今日仍未被全面超越。
不過,魯迅的著作無一不是在背負生活重擔的情形下寫成的。面對劇烈動蕩的曆史洪流,他并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在旋渦中颠簸輾轉地不斷創作。是以他的小說都是短篇作品,曾在心裡構思 的幾部長篇小說均未能實作。中國文學史的寫作計劃終未成型, 畢生難以割舍的中國字型史最終也未能問世。他的文章中大約有三分之二被他自稱是雜文、雜感的時事評論所占據。為此,甚至常有人揶揄他是“雜文專家”。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 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 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
這是雜文集《華蓋集》(1925)題記中的一段話,該書具有強烈的論争性。中國北方有一種現象名為“沙塵”——風将地上的 沙礫卷起,形成遮蔽天空的沙塵。魯迅愛惜這些雜文,将其喚作自己摸爬輾轉于“沙塵”中、被飛沙走石擊打而流血的“傷痕”。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魯迅将自己寫于“彷徨”時期的散文詩集《野草》中的諸篇文章,稱為“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譯本序》,1931)。與《野草》幾乎同時期編纂的評論集,被他取名為《墳》。
魯迅認為自己的文章不可能是盛開的薔薇,也不是香氣濃的蘭花。而他甘願忍受這種命運。為了讓中國這片大地有朝一日能夠迎來百花齊放的季節,他甯可選擇成為泥土。而要化為肥沃 的泥土,就必須首先變成腐朽的雜草,這便是本文開頭的那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