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穆蘊秋與該院首任院長、交大講席教授江曉原此前梳理了關于地外文明的主要“科學幻想”和科學探索,相關成果于近日出版。觀察者網科普作者岑少宇就這本新書《地外文明探索——從科學走向幻想》與兩位學者聊了聊。 在此前刊發的兩部分對話中,學者們從“月球文明”,一直聊到蟲洞與翹曲飛行,還穿插着對宇宙觀、科學标準等等的探讨。在最後這部分中,将繼續從“地外文明探索”出發,探讨“唯技術主義”,科學與科幻的邊界,以及科學直覺等問題。
觀察者網:之前我們聊到的蟲洞、翹曲飛行确實還比較科幻,尋找地外生命的真正高潮應該是向外發送信号的METI項目。主流學界對其中蘊含的風險,應該說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還出台了《準則聲明》。
但這類東西對支援METI的人來說,并沒有多少限制力,從目前的國際格局看,人類短期内似乎無法避免METI的冒進,我們是否也能“科幻”地想象下,未來可能出現怎樣的管控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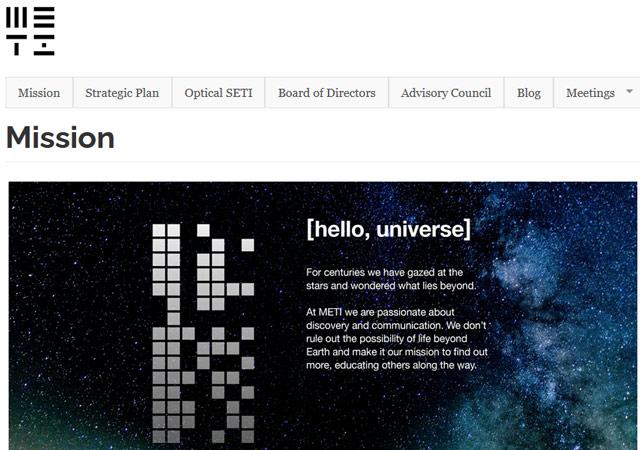
meti.org網站頁面
江曉原:這種事情很難管控,我知道一個例子,沒直接關系但有點類似。1972年聯合國通過了《防止傾倒廢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的公約》,1993年,其中37個公約成員國,又表決支援全面禁止在海上傾倒核廢料。這個公約到現在還是有點限制力的,美國這些國家确實不敢倒了。當他們想要繼續倒的時候,“努力”的方向是把這個公約推翻或規避,要是它完全沒有限制力,幹脆不理它就好了嘛。
日本現在要排核污水,它也在找借口,比如說不是“傾倒”,或者廢水不是“廢料”。我們當然堅決反對日本的做法,但從它找借口的行徑也可以看出,還是有點忌憚《公約》的。
但我覺得公約本身也沒有什麼強力保障,它就是一個大家願不願意遵守的問題,不遵守也隻能譴責一下。回到METI上,我覺得大家還沒有完全接受這樣的限制,現在願意搞類似活動的人其實還是很多的。
2017年11月,位于挪威特羅瑟姆附近、隸屬于EISCAT科學協會的天線組向太空中發射了信号,包含特别譜寫的電子音樂,以及關于幾何與二進制的教程,圖檔來源:EISCAT,攝影:Craig Heinselman
觀察者網:書中将METI的支援者們判定為“其實有着一種‘唯技術主義’思維傾向,所考慮的隻是想盡辦法要在技術上達到目的”。為什麼會這樣定性?
從字面上看,“唯技術主義”更多地是指那些認為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人。而他們像是為了好奇心不顧一切的人,我更願意把他們叫作“好奇主義”。
打個比方,一個孩子不顧洞裡可能有蛇,非要把手伸到洞裡探索,如果把伸手視作孩子的“技術”,他或許并不認為伸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隻是想滿足好奇心。METI的支援者也是類似的,并不想“解決問題”,而隻是解答疑問,滿足好奇心。
穆蘊秋:他們也算是“唯技術主義”,就是說定了一個目标,不考慮它背後的倫理、可能帶來的災難之類,一心一意去實作它就行了。
江曉原:“唯技術主義”甚至可以不考慮目标,隻考慮技術。當然,他們可以說自己是有目标的,是要跟外星人建立聯系。
但在具體開展的過程中,會吸引世界上各種各樣迷戀技術的人,他們其實對于目标是不思考的。現在有人在搞METI是吧?行,我也來搞,你們功率還不夠大,我就給你搞大,你之前發出去的信号别人看不懂,咱們再發讓人更容易看懂的信号。
1970年代,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把這些圖像資訊發往太空
觀察者網:但追求更高更快更強,本來就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之一。METI項目裡展現的好奇心,同樣也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動力之一。在METI上遇到的問題,可能是它們的邊界究竟在哪裡。
江曉原:人類的欲望和好奇心推動了科學發展,這是我們現在所接受的主流的說法,但其實想一想,這兩個東西到底好不好?其實這兩個東西都是非常有害的。
觀察者網:對,它們到一定程度肯定會有害。欲望的邊界可能讨論得比較多了,是以我想聊一聊好奇心合理的邊界在哪裡。
江曉原:“好奇害死貓”,這個是西方人的諺語。但其實仔細想想,好奇心害死的貓在現實生活中是很少見的,你見不着吧?那為什麼會産生這樣一句話?這就表明人們知道好奇心是有害的。
我覺得當科學家要用納稅人的錢給自己造“大玩具”,又講不出任何用途來的時候,他們就說要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其實是要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對不對?
你想要造對撞機,讓我們納稅人拿錢給你造,說要滿足好奇心,滿足誰的呢?我沒這個好奇心,我沒想造對撞機,現在要把我納的稅給你造,這合理嗎?是以好奇心這種理由,它在倫理道德上是有問題的。我們就要問他是誰的好奇心?你的好奇心,還是我們的好奇心。
觀察者網:但是我們如果回到科學早期階段,确實很多科學家個人他真的就是好奇心推動……
江曉原:對啊,但他們沒用納稅人的錢,牛頓一分納稅人的錢也沒用過。那個早期階段被我稱為科學的“純真年代”,科學家不用納稅人的錢,你随便有啥好奇心都沒問題。
穆蘊秋:小科學時代你随便好奇,幾乎是無限的邊界,自己在一張紙上怎麼算都行。但那時候,你能力也有限,無非就是推導公式,或做做小實驗。
江曉原:我覺得現在就可以明确地畫一條邊界——隻用你自己的錢。
穆蘊秋:但是不能是社會資金,那樣就要有資金評估了,要看錢花得值不值。
江曉原:我就知道我們國内現在有一些企業家,有點小錢,他們自己搞什麼永動機,你愛搞就搞去。你如果不用别人的錢,就自己弄是可以的。當然還有限制,比如說你不能犯法犯罪對不對?你在這些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關着門在家裡弄,當然沒人管你了。現在事實上社會也是這麼操作的。
觀察者網:最後還是讓我們回到書裡最核心的科學與科幻的問題。書中在近結尾處舉了一個赫歇耳論證太陽宜居的例子,認為他的論證方法,“完全符合西方天文學發展的根本思路:在已有的實測資料基礎上,構造實體模型,再用演繹方法,嘗試從模型中預言新的觀測現象”。
但是,按書裡先前引述的,赫歇耳的論證“采用的是‘認真考慮過的’類比方式”。後面一種說法,好像就沒有前一種形容的那麼嚴謹。科學家如何去建構一個類比,倒讓我想到了他們的“直覺”。
現在科學家也要用到直覺,然而我們可否說其實僅僅指引了一個方向,結論與“預言”都需要得到比赫歇耳當年更嚴謹的科學驗證?或者說他們不像赫歇耳那麼“自由”了?
江曉原:我倒覺得也沒多大的差别,現在有些事情想象的空間被壓縮,隻是因為确切的知識多了……
穆蘊秋:或者說儀器更精密了。
江曉原:對。其實光譜分析對科幻來說絕對是一個“殺手”,它出現以後,我們就知道太陽表面溫度6000多度,再也不會想象太陽上的居民了。
觀察者網:書裡提到,赫歇耳當時想象的是雙層雲,上層雲發出亮光,下層雲可以為太陽生物擋住亮光,但6000度的高溫确實會打破這樣的構想。
穆蘊秋:威廉·赫歇耳是恒星天文學的權威了,太陽作為天空中最亮的星體,他當時最關注的問題,就是要搞清楚太陽的結構。他想象太陽可能是宜居的表面,因為當時主流的思想認為天體的光和熱是分裂的,就是說它發出亮光也不一定産生高的熱量。
江曉原:Nature創刊于1869年,第一任主編洛克耶就是一個太陽天文學家,用光譜分析方法發現了氦。他的時代太陽實體學非常熱,光譜分析剛剛發明不久,就到每一顆恒星上都去用一通,一下子很多東西都分析出來,這個時候就知道太陽那麼熱了。
洛克耶制作的光譜分析圖,出自1878年的《光譜分析研究》,圖檔來源:sciencemuseum.org.uk
而赫歇耳要比他早一個世紀,在18世紀的時候想象太陽上有人是合理的,因為并不知道太陽到底有多熱。
穆蘊秋:當時他也隻能用到那樣的類比和直覺。而且,赫謝耳的這兩篇論文還發在《哲學彙刊》上,它是第一份科學期刊,到今天名頭也很大。
觀察者網:你們覺得科學直覺,是不是可以了解為聯系科幻與科研的直通車,或者是兩者邊界上真正的“模糊地帶”?
江曉原:我覺得直覺可能并不扮演科學和科幻之間的橋梁。即使不在科學和幻想的邊界上,而在非常傳統的科學領域内,直覺也是非常需要的。
穆蘊秋:科研肯定是要直覺的,像靈感、頓悟之類的,寫科幻,可能也要直覺,但功能不一樣。
直覺也是一種很普遍的認識事物的方法。比如平時跟人打交道,也會用到直覺,有些東西他沒告訴你,突然你就感覺到了,就是調用了直覺。
江曉原:直覺哪都有,拍拖也有直覺,跟老闆講工資談價錢的時候也有直覺。但科研裡有些直覺确實是大師才有的。
比如伽利略的理想單擺,軸的摩擦力等于零,繩是沒有品質的,球是剛體,在空氣中擺動的時候是沒有摩擦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弄出一個定律來,非常完美。但為什麼要忽略空氣?為什麼要忽略摩擦力?為什麼要忽略繩的品質呢?沒道理啊……大師才知道要忽略這些,忽略了以後就能得出這個定律來。要是不忽略,以當時的實體和數學手段,根本得不到這個定律。
看上去很簡單,但在他之前,為什麼别的人假設不出理想狀态?這就是大師,隻有他知道該忽略那些因素。
比薩大教堂中,描繪伽利略觀察吊燈擺動的壁畫,作者為Luigi Sabatelli (1772-1850),圖檔來源:thoughtco.com
觀察者網:這種直覺能訓練嗎?你們覺得科幻對這種直覺的形成有幫助嗎?
江曉原:我不認為會有幫助,我覺得這種直覺可能是天賦,娘胎裡帶的,要是爹媽給了你就有,沒給你,你努力死也沒用。
我覺得各種直覺,是個體化的,很難在後天通過一種什麼課程或者教育訓練來養成。
穆蘊秋:别的方法比如說邏輯性的方法,實證、實驗這些可以訓練,但是這種直覺性的頓悟沒辦法訓練。
江曉原:科學與科幻确實有交界,但直覺完全是一個工具性質的事情。而我們在書裡強調的是,科學和科幻的邊界是開放的。因為早期的很多科學活動,其實在今天看來就是科幻,但是在那個時候人們是當成科學看的。
兩者邊界開放這種觀點,即使拿到今天的科學現狀裡來看也沒有害處,我們也沒必要認為今天的科學活動和科幻有明确邊界。沒了邊界,大家放開了想就很好,科學家要頭腦風暴的時候,找兩個科幻作家來聊一聊也是有好處的。
(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内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将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