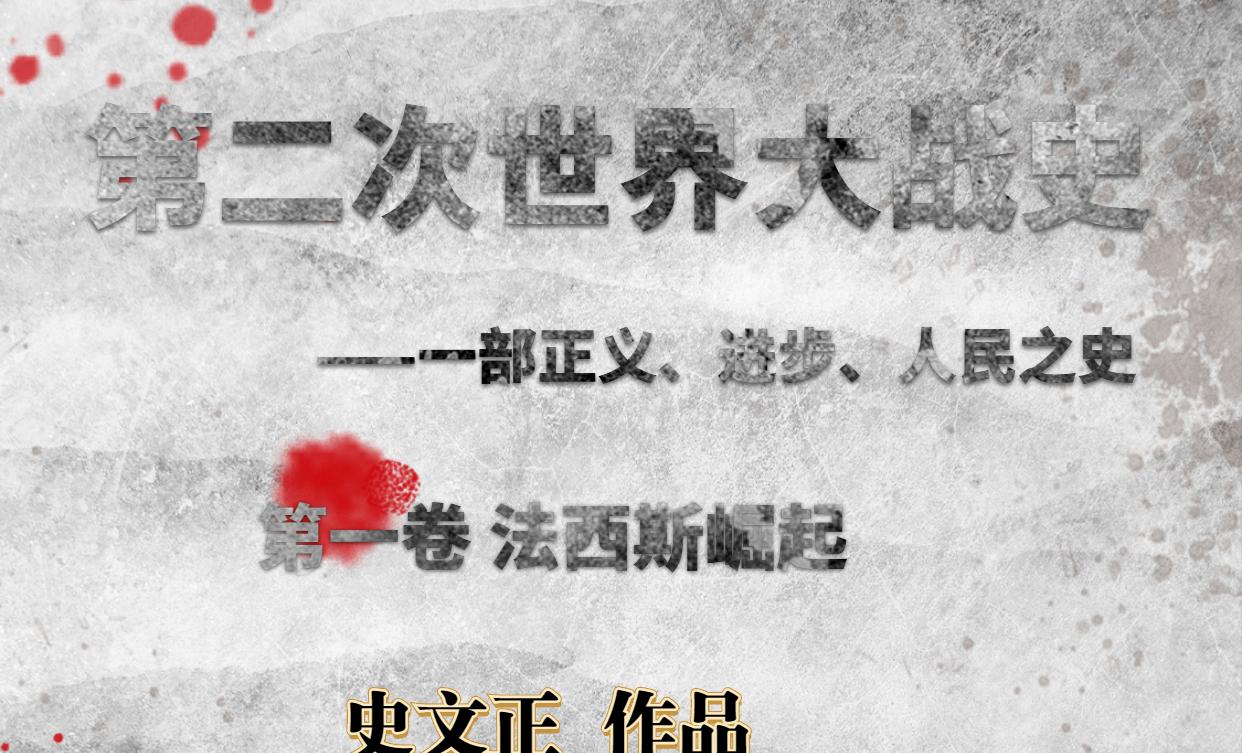1931年12月,犬養毅政友會内閣接替若槻禮次郎民政黨内閣,這自是一個對軍部聽話多了的内閣,這是法西斯化“開局之年”的“必然結果”,也是日本法西斯化程序加速的起點。新内閣在法西斯化程序中大約有如下“貢獻”:
一是在以一夕會為代表的軍部法西斯分子的策動下,在以下層軍官為代表的民間法西斯分子的鼓噪下,各派法西斯勢力的共同代表人物荒木貞夫出任陸軍大臣。政友會内的一批親軍部的分子也紛紛入閣。犬養内閣一改前任之“消極政策”,對軍部侵略行動給予積極支援。在這一個内閣期間,軍部順利完成了對東三省的占領,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并在這一事變的掩護下,完成了僞滿洲國的炮制。
二是犬養内閣一改前任的緊縮政策,重新禁止黃金出口,大張旗鼓地擴張财政。當然,擴張出來的财政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使國家的發展步入正軌,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援軍部的擴軍備戰,支援它的侵略擴張。在這種“軍需通貨膨脹”政策的支援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突飛猛進,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不斷上升,而輕紡工業則持續下降,日本經濟結構急劇發生變化。
日本向來是一個農業依然保留殘酷封建剝削、輕工業比重極高的落後帝國主義國家,盡管多年來不斷對外發動戰争,但是那些與戰争相關的産業在經濟體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這是專制封建帝國主義的必然結果,越是反動的,就越是落後的。不過此時此刻情況不同了,這是一個工業化戰争的新時代,是一個反動邪惡的新勢力登台亮相的時代,兩者一結合就出現了強力推動下的前所未有的可怕發展局面。
于是,當其他帝國主義還深陷危機中時,德日這兩個帝國主義卻逆勢而動地“興旺”起來。而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實力迅速增強還伴随着工業化水準急劇提升的結構變化。于是,盡管它依然處于帝國主義末流水準,但表現出更加氣勢洶洶的擴張之勢。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個日本帝國主義的二戰直接準備期内,重工業特别是戰略原料和軍事工業這些戰争相關的産業成數倍、十數倍甚至數十倍增長,一些産業從無到有也被強力發展起來了,到1937年它發動全面侵華戰争時,重工業特别是那些戰争産業開始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産業。
這是一個戰争刺激出來的、迅猛的、畸形的發展過程。和德國帝國主義一樣,伴随着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發展,财政緊張、外彙緊張、原材料緊張等一系列緊張局面也在日本帝國主義那裡出現了,确切一點說,對一向資源貧乏的日本帝國主義來說,緊張程度要遠高于它的德國同夥,而伴随着經濟的畸形發展,一直以來作為财政和外彙根基的輕紡工業相對衰落,進一步加重了這一局面。戰争刺激起來的東西隻能通過戰争途徑獲得發展,膨脹起來的戰争經濟隻能通過新的掠奪獲得擴張管道。
殘酷的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日本帝國主義戰争準備的題中應有之義,對北韓、台灣以及新到手的滿洲,還有接下來要侵略的華北,日本帝國主義都是将其納入戰争經濟範圍,通盤考慮予以掠奪的。尤其是對滿洲這塊最大的殖民地,它到手之前,各種掠奪計劃就紛紛出爐出籠了,其核心就是如何實作“日滿一體化”,讓滿洲“盡其所能”為其戰争準備服務。
當然光靠竭澤而漁地掠奪貧弱到了極點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是根本無法滿足其戰争經濟欲壑,必須有新的來源為其戰争準備服務,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提供了這一來源。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和戰争準備無疑又是一大“商機”,以美國壟斷資本為首的力量無疑又找到了“貢獻”其力量的良機,大量的戰略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給日本帝國主義戰争經濟,日本帝國主義缺什麼,它就提供什麼,它的“服務”是相當到位。它繼續以中立之名拒絕承擔國際義務,“中立”這個東西真是個“好東西”呀,在它之下,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什麼肆意妄為,什麼傷天害理,在這裡都是稀松平常,對戰争幫兇的角色,美帝國主義是“當之無愧”的。
好了,侵略擴張是日本法西斯化的一翼,而以重工業和軍工業為主的戰争經濟大發展則是另一翼,光有侵略擴張這個法西斯化的“龍頭”不行,還得有經濟基礎,我們馬上就會看到,戰争經濟的大發展開啟了軍部法西斯與壟斷資本的結合過程。
好了,說了犬養内閣的“好”,我們還要說說它的“不好”。這個内閣顯然為日本法西斯化立下了不少“功勞”,不過仍然不是一個令軍部滿意的内閣。首先它依然是一個政黨内閣,其次盡管它傾向了軍部,但依然不願意乖乖服從軍部,還不時制造一些小掣肘。是以,搞垮它,建立更聽話的内閣已經在軍部的謀劃中。恰在此時,左翼民間法西斯制造的政治恐怖事件幫了它的忙。
之前我們說了,左翼民間法西斯早就想采取行動了。面對“江河日下”、民不聊生的日本,他們是焦慮不安,特别是來自危機最重的農村地區的井上日召的日本主義派、桔孝三郎的農本主義派更是如此,他們屬于左翼中的左翼,對日本侵略擴張不感興趣,而對實作他們心目中的“改造日本”充滿期待。不知出路何在的他們以及受他們影響的一些海軍下層軍官最終無可避免地走向了暗殺這條政治恐怖道路,先後制造了“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暗殺直指政黨和财閥,恐怖制造者們宣稱要“清君側”,去除隔在天皇和國民之間的“障礙”,實作天皇親政。
事件的直接結果是,除了包括首相犬養毅在内的幾位政界财界要人命喪黃泉外,對日本現有政治經濟體系并未造成太大沖擊,但是對事件的處理就截然不同了。軍部法西斯立刻抓住機會,對事件進行前所未有的包裝,力圖把它打造成一場強有力的法西斯宣傳狂潮。對恐怖制造者的審判變成了他們對包括政黨政治在内的資産階級民主制度的控訴,他們的愚昧無知被當作“獻身精神”加以頌揚,他們對天皇的迷信被美化成“憂國憂民”、“愛國赤誠”的效忠天皇的典範加以仰慕。這是事件的必然結果,恐怖制造者從來沒有跳出統治階級為之規劃好的路線,因而隻能為統治階級服務。這樣的“獻身精神”、這樣的典範,正可被法西斯用來驅使人民充當戰争的炮灰。
依仗這場法西斯狂潮,軍部一舉終結了政黨内閣,不過軍部還無法一口吞下内閣。新的内閣雖然不再是選舉産生的議會多數黨内閣,但又回到了天皇身邊的元老重臣推薦内閣的時代。帝國主義體系内的穩健派政治力量,包括以西園寺公望為代表一批元老重臣,還不願把政權交給冒險急進的軍部法西斯,而法西斯本身羽翼還不夠豐滿。于是在各派力量的妥協下,帶有中間派色彩的齋藤實内閣于1932年5月26日誕生了。新内閣是由軍部、官僚、政黨三方組成的号稱“舉國一緻”的内閣,實際上是各派勢力不穩定結合的大雜燴内閣,因而是一個帶有過渡性質的内閣。
軍部在這一内閣中的發言權無疑是主導性的。1932年9月,内閣正式認可了軍部一手扶持的僞滿洲國。在這一内閣期間,軍部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争中“再立新功”: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之後越過長城,不斷在華北地區挑起事端,開始了蠶食華北的侵略行動。與此同時,在軍部的主導下,日本帝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一樣正式退出國聯,這樣一個懦弱的機構也成了它侵略道路上的絆腳石。日本帝國主義準備侵略道路上越走越遠,建立更強有力的獨裁體制也就勢所必然了。
在内閣中,法西斯勢力代表者荒木貞夫留任陸軍大臣。有強大軍部的支援,荒木無疑是内閣中的活躍人物。他一方面整頓其管轄下的陸軍,大搞任人唯親,那些曾經支援他的法西斯分子包括一夕會分子紛紛榮登高位,軍部這個法西斯機構的法西斯化程度進一步提升了。另一方面,為了更徹底消除政黨對國策的影響,同時提高軍部的影響,在荒木的主導下,内閣确立了新的決策機制,即有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參加的五相會議。新決策機制的意義在于決策的獨裁性提高了;五相中有兩相是軍部大臣,同時軍部不但可以參與與之有關的軍政大事的決策,更可以參與到一般國事的決策,軍部的地位提升了,日本的法西斯化又前進了一大步。
不過,在最初的五相會議中,軍部并未取得主導地位,主張在國際國内都走協調路線、反對一切為了“國防”的穩健派占了上風。這也表明新内閣依然不是一個乖乖聽話的内閣,它還不時與政黨勾勾搭搭,掣肘軍部。而政黨還想“死灰複燃”,重新奪回内閣大位。這表明日本帝國主義在整體走向法西斯的同時,還不時出現一些“遊移不定”,穩健派的主張還有一定的影響力。
齋藤實内閣因帝國人造絲公司事件總辭職,在西園寺公望為首的元老重臣的推薦下,岡田啟介于1934年7月8日接掌内閣大位。岡田内閣實際上是齋藤内閣的繼續,繼續反映元老重臣穩定政局的期待。在岡田這個新的大雜燴内閣中,官僚的成分上升明顯,政黨的成分繼續下跌。當然,不管如何,軍部在内閣中的發言權繼續穩步上升。元老重臣推薦這屆内閣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想讓它處理好《倫敦海軍條約》續約問題,確定日本繼續留在裁軍條約内。然而在海軍的強大壓力下,軟弱的岡田内閣顯然無法承擔這一重任,最終滿足了海軍的一切要求,徹底退出了裁軍條約,這是日本在戰争道路上越走越遠的又一嚴重步驟。
陸軍向岡田内閣提出的要求是統一在僞滿的機構,僞滿将由陸軍獨家掌控,内閣其他部門不得介入,這顯然是軍部獨裁的雛形。盡管遭到内閣其他部門的反對,陸軍的要求還是在岡田内閣中得到實作。
當然,我們的軍部不會就此罷休,它不斷把新的要求送到岡田内閣面前。在1936年度的預算中,陸海二省提出了高達十億元的軍費要求,這一要求接近總預算的一半,而之前一直實行的30%左右的占比已經使日本帝國主義在列強中獨占鳌頭。這一預算無疑又是一個加重人民負擔、讓财閥大得其利、讓軍國主義将日本推向戰争深淵的預算。在帝國主義、專制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民的要求不可能出現在預算中,岡田内閣更不是代表人民的内閣,除了屈從軍部的要求外,它不會做出别的選擇。
1934年10月,陸軍省發表題為《國防的意義及其強化》的小冊子,公然宣稱:“戰争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國防是國家發展壯大的基本動力”,主張建設“國防”國家,擴軍備戰,建立“總體戰”體制。這本帶有綱領性質的小冊子既是軍部野心的公開表達,更表明它離建立獨裁隻有一步之遙了。
在這一内閣的幫助下,在中國反動派的不斷妥協退讓下,軍部繼續以政治經濟手段蠶食華北政權,侵略行動是順風順水。繼東北之後,華北也正在成為軍部的囊中之物。新的侵略“功業”讓軍部是“光輝耀眼”得很。
岡田内閣依然不是一個真正服從軍部的内閣,這可以從元老重臣創立這個内閣的目的看出來。盡管它滿足了軍部的一切要求,但不是痛痛快快滿足的,軍部總是要施加很大壓力。其實,回顧“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各屆内閣,它們一個比一個更加聽命于軍部,但是又與軍部保持一定距離。它們不斷向軍部妥協退讓,表面上的原因是它們生怕軍部這個不擇手段的“冒險家”惹是生非,攪得政局不甯,于是為了穩定,它們就不斷向軍部妥協,滿足它的要求。但是,我想,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它們作為一般帝國主義,缺乏軍部敢走極端的“勇氣”、敢于冒險的“魄力”,它們既期望軍部“再立新功”,又害怕它冒險過猛,極端過度。它們不斷地遊移于遏制和縱容之間,但是總的趨勢是遏制的成分越來越小,縱容的成分越來越大,直至它們本身也變成“軍部”。
進入1932年,在内閣不斷向軍部靠攏這個首要法西斯化程序外,日本法西斯化在更廣領域内展開了,已經不隻是民間法西斯和軍部法西斯了,财閥開始與法西斯結合了,法西斯官僚開始出現了,工農運動開始“轉向”了,法西斯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展開進攻、實施掌控,一場真正的、徹底的法西斯運動開始了。
首先我們要說一下财閥與法西斯的結合。按理說,财閥與法西斯的結合是必然的。财閥從誕生之初就與國家政權緊密結合在一起,就與戰争結下“不解之緣”。新的曆史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再次選擇戰争,無非是它的經濟基礎财閥尋找新的發展空間的必然結果。不過,雙方的結合依然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一個“磨合期”。“軍需通貨膨脹”刺激下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突飛猛進無疑讓在這一領域占優的财閥再次大得其利,經過多年的遊離後,财閥與戰争再次建立直接聯系。不過這一過程同時伴随着日本産業結構的猛烈調整,一些輕紡工業比重高的舊财閥并沒有馬上趕上這一步伐,它們的經濟體系與戰争經濟體系出現了差距,盡管它們很快意識到了這個“錯誤”,不過調整依然需要一個過程。與此同時,軍部法西斯在其發迹之初和民間法西斯一樣也有濃重的“反資本主義”傾向,不但反對政黨政治,也反對壟斷财閥,他們甚至不允許财閥進入其新開辟的僞滿殖民地,于是雙方就有了隔閡。當然軍部法西斯也很快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它認識到沒有财閥這個最深厚、最強大的階級基礎,自己就是無根之草、無本之木,于是軍部法西斯開始主動消除隔閡,加強與财閥聯系。軍部法西斯開始将财閥視為其獨裁統治的真正階級基礎,财閥也開始改變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放棄政黨這個日益無用的代理人,全力以赴支援軍部法西斯掌權。
當然,軍部法西斯與财閥結合不隻展現在“理念”上,更展現在實踐中。軍部建立“總體戰”體制,核心的一環是統制經濟,即建立戰争計劃經濟體制。那麼建立這樣一個體制,最可依靠的力量就是最渴望戰争的财閥。在統制經濟上,雙方又找到了共同點:法西斯全力維護财閥利益,财閥則全力支援統制經濟。
進入1932年,在民間法西斯和軍部法西斯之外,一支新的法西斯勢力——法西斯官僚也開始在日本政壇活躍起來,我們之前說了,進入二十年代,專制官僚集團在日本帝國主義體系内的地位開始下降,一部分官僚轉向政黨集團,成為政黨化官僚,但更有一部分轉向更加反動的法西斯。危機到來後,特别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内閣各部、貴族院和宮廷集團等官僚組織内出現許多“革新派”人物,有近衛文麿、廣田弘毅、木戶幸一這些後來在日本法西斯化道路上叱咤風雲的人物。他們通過金雞學院、國維會等組織進行集會,加強與軍部法西斯和财閥的聯系,共同商讨“改造日本”的種種計劃,這标志着法西斯官僚作為一個整體開始出現于日本帝國主義體系内。法西斯官僚也和其他法西斯一樣以“反資本主義”的面貌出現,當然它反對的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而不是它的獨裁專政。它支援軍部獨裁,支援“國家統制”,支援“總體戰”體制,同時也支援在這種體制下加強财閥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掌控,總之一點,它支援的是各派法西斯勢力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強大的獨裁體制。與“實幹家”軍部不同,法西斯官僚更具有理論色彩,它不但鼓吹“總體戰”體制,更為其制造出一個深厚的理論和哲學基礎,使之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
迄今為止,我們尚未全面介紹軍部法西斯與廣大人民群衆的關系——之前雖有軍部法西斯利用民間法西斯,但并不全面代表這一關系。有了财閥作階級基礎,有了官僚法西斯作左膀右臂,并将廣大人民群衆俘虜至麾下,才算軍部法西斯化的完整版本。法西斯将人民群衆納至麾下,首先依靠明治維新以來形成的強大的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傳統,其次依靠由戰争和民間法西斯掀起的一次又一次法西斯狂潮,再次依靠“軍需通貨膨脹”帶來的短暫繁榮對人民群衆反抗情緒的消弭。
當然依靠這些仍不足以敉平人民群衆的反抗情緒,軍部法西斯給出的根本出路是把這種不滿情緒引向戰争,但在這之前要消滅上司人民群衆走向反抗的左翼革命力量。1932年,以共産黨為首的左翼革命力量逐漸糾正了自己的“左”傾錯誤,革命運動又開始出現興旺之勢,然而新一輪的鎮壓迅速而至。法西斯主導下的鎮壓是前所未有的,革命力量遭遇滅頂之災,組織機構基本被摧毀。共産黨無法承受住這樣的打擊,變節者大量出現,紛紛宣布脫黨,擁護天皇制,向法西斯投降。
左翼力量遭到毀滅性打擊,工農群衆的右翼政黨則全面“轉向”,開始由帝國主義在群衆中的台柱轉化為法西斯在群衆中的台柱。右翼政黨部分上司人完全退化為法西斯分子,給法西斯運動披上社會主義的外衣,以更具蠱惑性的方式宣傳法西斯,公開向軍部法西斯獻媚。革命進步力量被嚴重打擊,反動倒退的東西就會迅速高漲起來,人民群衆就會被更大規模地驅入法西斯的罪惡洪流。
法西斯運動開始向縱深發展,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展開猛烈的沖擊,一場由民間法西斯主導、由軍部法西斯助推并充分利用其成果的思想統制運動展開了,不獨共産主義、就是資産階級民主自由也要被徹底消滅。“罷黜百家、獨尊天皇”的“明征國體”運動開始了,思想學術界的法西斯運動開始了,“司法官赤化”和“教員赤化”被嚴厲鎮壓,泷川幸辰的法律學說被禁止了,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被取締了。依靠天皇這個至高無上的金字招牌,法西斯思想是壓倒一切,一切不合意的東西都被扣上“赤化思想”“破壞國體”的帽子,逐出日本帝國主義世界。法西斯一統天下,将皇國史觀,将極端民族主義,将一切适合侵略擴充的東西,統統灌輸給人民,使之成為馴服的戰争奴隸。
在介紹了法西斯的“節節勝利”之後,我們現在有必要回顧一下法西斯的内部沖突,這一沖突并不是法西斯的破壞因素,而是促使它更加法西斯化的因素。法西斯内部的沖突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軍部法西斯内部皇道派和統制派的沖突,二是作為法西斯右翼的軍部法西斯和民間法西斯左翼的沖突。
皇道派和統制派作為軍部法西斯都強調軍部獨裁,強調侵略擴張,不同之處是前者強調隻需依靠日本帝國主義所蘊藏的強大的、反動的精神力量就可以赢得軍部獨裁和侵略戰争,“皇軍”憑借着對天皇的愚忠就可以無往而不勝;後者則比前者更現實一點、辯證一點,強調指出,“皇軍”的愚忠固然需要,更需要建立“總體戰”體制,軍部獨裁,統制經濟,與财閥和法西斯官僚合作,動員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力量才能赢得戰争。顯然,統制派全面繼承了當年一夕會的東西,是軍部法西斯的正宗和主流,軍部法西斯也一直都是這樣做的,隻因為出現了皇道派這個支流和阻礙,軍部法西斯才需要統制派這個主流與之對抗。
荒木貞夫擔任陸軍大臣期間,皇道派開始形成。荒木一貫鼓吹皇道論和國體論,也就是皇國史觀那一套東西。荒木任職期間任人唯親,排斥異己,于是很快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鼓吹狂熱精神主義的新派閥。後來林銑十郎接替荒木貞夫擔任陸軍大臣,任用統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鐵山為軍務局長,大肆排擠皇道派,兩派的沖突由此産生。
軍部法西斯和民間法西斯左翼的沖突實際上與軍部内部的沖突密切相關的。在對待天皇問題上,民間法西斯左翼與皇道派實際上是有“共同語言”的,民間法西斯左翼相信天皇會拯救他們,而皇道派則大肆鼓吹皇國史觀,是以它們之間表面上是沒有沖突的。如果我們對皇道派加以擴大,民間法西斯左翼可以視為皇道派的下層,而軍部中的皇道派可以視為皇道派的上層。但是民間法西斯左翼與統制派之間就不同了:前者強調日本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内部問題,是以首先内部改造,後者強調日本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外部問題,是以對外侵略第一;前者強調“天皇親政”,後者強調軍部獨裁;前者反對财閥,後者與财閥結合。是以,民間法西斯左翼與軍部法西斯的沖突,實際上就是與統制派的沖突。
經過“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後,民間法西斯左翼實際上就剩下了受北一輝影響的那批下層軍官。他們“信賴”的荒木貞夫上台了,于是就沒有參與這些事件。後來,荒木貞夫下台了,于是伴随着軍部法西斯内部沖突的尖銳,他們對統制派的不滿也急劇上升,事實上,他們與統制派的沖突遠比軍部内部的沖突尖銳。于是雙方展開了鬥争,統制派堅決要去除日本法西斯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礙,而它的對手也與之展開了鬥争。鬥争的高潮就是“二·二六”事件。
讓我們把時間再轉到1936年,這一年無疑将以極其醒目的“二·二六”事件載入史冊。受北一輝影響的下層軍官發動的這場政變,較之前的“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規模更大,組織性更強。一支1400餘人的隊伍——他們是守衛京畿部隊的一部分——在下層軍官上司下,突然行動,刺殺多名政要,占領國家要害部門,并通過“同情”他們的政界軍界上層人士将訴求反映至天皇。事件基本夠得上政變級别,對統治集團的震動無疑是巨大的,算得上是民間法西斯左翼的“巅峰之作”。
不過政變者依然沒有跳出民間法西斯左翼所具有的劣根性:愚昧、無知、反動。他們在政變中提出的東西就是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那一套東西,他們依然幻想着統治階級中會有“聖人”出來拯救萬民于水火。他們懷着極其真誠的願望發動了政變,隻想“上達天聽”“請求聖斷”,然而“天聽”和“聖斷”就沒有這麼真誠了。“天聽”和“聖斷”的嗅覺是靈敏的,它迅速意識到這次政變不同以往,盡管方式上是愚昧無知的,但政變者所代表的下層群眾已經出現了威脅統治階級的迹象。是以,鎮壓成了統治集團對待此次政變的主調。
當然,軍部不但要代表統治集團鎮壓政變,清除已經對它構成威脅的民間法西斯左翼,将想利用政變渾水摸魚的皇道派排擠出去,更要像對待“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那樣,充分利用政變的“法西斯效應”,将日本的法西斯化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階段。
“二·二六”政變的第一個“法西斯效應”就是法西斯分子對軍部展開大規模的整肅運動,進一步提升軍部的法西斯化程度。參與政變的下層軍官被秘密地迅速判決,為首者處以極刑。另外,北一輝和西田稅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政變,但無疑是政變者的思想靈魂,是以也遭到同樣的對待。秘密判決決定了左翼民間法西斯分子無法利用審判講台宣揚自己思想,“血盟團”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結局沒有重演。大權在握的軍部法西斯已經不需要這樣的宣揚了。
大規模的人事調動開始了。不獨與政變有瓜葛的皇道派分子,就是支援過統制派的那些人物也被法西斯分子看做是老朽人物,統統打入預備役這個“冷宮”。更加反動、更加極端的法西斯分子掌握了軍部大位,以一夕會分子為代表的那批法西斯分子在軍部法西斯體系中地位更高了,能量更大了,更能左右一切了。對他們來說,軍部面貌可謂是“煥然一新”。巴登巴登密約中展示的“消除派閥、重新整理人事、改革軍制”的局面終于出現了,有更大作為的時刻到來了。
當然,“煥然一新”的不隻是軍部,而是整個日本帝國主義世界。新成立的廣田弘毅内閣盡管依然是元老重臣推薦的,但此時的元老重臣對軍部是唯命是從。新内閣一成立,軍部就為它規定了行動方針:
加強國防——實質上是加強軍備,為更大規模的侵略戰争做好準備。
明征國體——繼續推進思想統制運動,確定法西斯掌控一切。
安定民生——這是一個蠱惑人心的口号,實際上是“國防”加強了,民生就不可能“安定”。
革新外交——外交要百分之百服從侵略戰争的需要,要按照軍部的路線走。
軍部要求内閣人選要按照上述方針決定,一切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物堅決摒棄不用,政黨人物則要嚴格控制任用。軍部力圖把新内閣打造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軍部内閣”。
上台伊始,新内閣就發表了“全面革新政治”的政綱,它要革除的是帝國主義穩健統治方針,興起的是極端冒險的法西斯統治路線。1936年8月7日召開的五相會議可以看作是一次全面貫徹“革新政治”方針的會議,也是一次開始用五相會議代替内閣全體會議決定軍國大事的會議。軍部在齋藤實内閣期間的五相會議中沒有滿足的要求,通過此次會議全部獲得滿足。會議通過了名為“國策基準”的綱領性檔案。該檔案就其内容來說并沒有新意,無非軍部法西斯多年來宣揚的那些東西:一方面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再次展現一番,它要“排斥列強對東亞的霸道政策”,要充當“東亞的安定勢力”,并“向南洋發展”;另一方面為了實作這樣的野心,就必須建立“總體戰”體制,“革新”政治、經濟、文化,實施大規模擴軍,發展實作這一野心所必需的“産業和貿易”,實作“國防和産業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和燃料的自給自足”。
問題的關鍵不是檔案的内容,而是檔案來自哪裡。它不是出自軍部之手,而是出自内閣之手,它表明内閣也“法西斯化”了,表明軍部獨裁的大廈基本建成,下一步就是為這個大廈添磚加瓦,使之成為一個森嚴殘酷的法西斯戰争體系。
秉承軍部意旨,廣田内閣不遺餘力地推動日本帝國主義向這個體系邁進。它宣稱要“革新财政”,徹底打破前任“健全财政”的底線,無限制地擴張财政,全力滿足軍部擴軍備戰的要求;它宣稱要實行“廣義國防”,不但要發展軍工産業,更要發展與之有關的重工業,向自給自足的戰時經濟體系邁進;它宣稱要“改革稅制”“合理負擔”,于是把前所未有的軍費負擔更大規模地轉到人民的頭上;它宣稱要“改革教育”“統一輿論”,繼續推進法西斯思想統制;與軍部獨裁相适應,它全力推進官僚獨裁,繼續打壓政黨政治,徹底鏟除資産階級民主殘餘,意在建立“舉國一緻”的法西斯政治體制;它繼續推進對華政治經濟侵略,加大對僞滿殖民地的掠奪力度,千方百計逼迫國民黨政府走親日路線,力圖實作鲸吞中國的侵略“夢想”;它與德國法西斯簽訂《反共産國際協定》,法西斯軸心同盟體系開始出現,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擴張道路上又邁出了堅定的一步。
經過這一番猛烈行動,一個準戰時體制終于在日本帝國主義體系内形成了。對言聽計從的廣田内閣,軍部法西斯是滿意的,不過對整個日本帝國主義體系來說,這個内閣仍有“不足之處”:問題不在于它秉承軍部意旨全力向縱深推進日本法西斯化,而在于推進得過猛,立刻導緻日本帝國主義體系内各種沖突的猛然激化。人民群衆當中再次掀起反法西斯的波瀾,而在統治集團内,排擠出權力中樞的政黨力量也突然“正義”起來,在議會内對軍部獨裁展開猛烈攻擊。剛登上獨裁之位的軍部一時間成了衆矢之的,大有再失江山之虞。
面對突然來臨的法西斯獨裁,面對準戰時體制對人民利益的掠奪,不但工農群衆中的左翼力量,就是已經開始“轉向”的右翼力量也表現出反抗情緒,工農運動似乎又要走向高潮。于是共産黨被鎮壓後遺留下來的左翼組織響應共産國際“七大”的号召,效仿法國和西班牙,也想在日本展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運動。他們已經做出好了同右翼組織合并的準備,共同展開鬥争。然而,當真正的反法西斯運動來臨時,右翼勢力很快就恢複了它的本來面貌,它絕不會偏離帝國主義群衆台柱的角色。盡管稍有不滿,但它很快就遵從帝國主義的意旨服從法西斯獨裁,并最終徹底向它投降。共産黨遭到鎮壓後遺留下來的左翼組織本來就是力量弱小,意志不夠堅強,面對掌握群衆大多數的右翼勢力的反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運動隻能走向流産。
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未能形成,不過政友會、民政黨兩大資産階級政黨突然不依不饒起來,它們擺出絕不會向軍部獨裁低頭的姿态,在議會内與其展開“殊死搏鬥”。面對此種局面,廣田内閣也支撐不下去了,隻好辭職。1937年2月2日上台的林銑十郎内閣依然是一個軍部獨裁下的内閣。新内閣對前任政策作出一些調整,力圖消除這一政策不利于财閥的成分,確定軍部擴軍備戰的需要同财閥企業生産能力的提升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使日本帝國主義經濟體系被更大規模地納入統制經濟軌道。但新内閣依然無法消除軍部和政黨的沖突,這一沖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堅持了近四個月的林内閣也成了這一沖突的犧牲品。
面對此種局面,我們顯然不能把軍部與政黨的沖突簡單地了解為争權奪利的沖突,因為之前政黨對軍部不斷妥協退讓,軍部不斷搞垮政黨内閣,甚至政黨都要走上追随軍部的道路,而此時政黨勢力突然反彈,連續推翻兩屆軍部獨裁下的内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大盤”中,軍部的“股價”突然下挫,而政黨的“股價”卻要上揚了。政黨與軍部是在争權奪利,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導向法西斯戰争體制所激化的各種沖突也從中反映出來了。人民群衆的利益訴求雖然沒有通過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條正義途徑表達出來,卻通過政黨這個反動途徑曲折地反映出來了。
由此可見,軍部雖然掌權了,但是還沒有穩定地掌權,而且如果它找不到新的出路的話,這種不穩定性還會繼續增大。軍部的出路或者說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出路,毫無疑問,隻能是發動戰争。它一直都是這樣做的,奪取政權靠發動戰争,此時鞏固政權同樣需要發動戰争。随着全面侵華戰争的到來,随着更反動的人物走上内閣舞台,軍部法西斯最終會把自己的獨裁統治推向登峰造極的地步,而日本帝國主義也将徹底走上一條不歸路。
※※※※※※※※※※※※※※※※※※※※※※※※※※※
道路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道路就是靈魂。有各種各樣的道路,有尊重客觀規律、自覺選擇的正義進步之路,有隻顧眼前利益、盲目發展的邪惡反動之路。前者無疑是一條艱苦卓絕之路,但更是一條確定我們永遠繁榮昌盛的康莊大道,正确的利益根基一旦鑄就,創造的發展之魂必将大放光芒。後者往往具有捷徑的迷惑性,我們總是會盲目地順着它走下去,但是邪惡的利益格局一旦固化,強大的反動力量終将把我們推入罪惡的深淵。
曆史早已翻過了那血腥罪惡的一頁,完全迥異于過去的新的時代、新的未來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已經做出選擇,我們堅信我們的選擇是推動我們永不停息、勇往直前的偉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