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槐蔭書話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APP動态
在大時代的風暴中,一個覺悟了的新女性,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熱血澎湃,彷徨猶豫,不知該往哪裡走。
五四運動爆發的那一年,丁玲和好友王劍虹正在湖南桃源的省立女子師範讀書。她們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帶頭剪辮子,讀新文學作品。到上海後,她和王劍虹進入上海大學文學系學習,認識瞿秋白。六十年後,她寫了一篇回憶瞿秋白的文章,詳細記述了這一段的生活。小說《韋護》,就是以瞿秋白王劍虹的愛情生活為題材,用滾燙的文字镂刻瞿王的生死戀。王劍虹病逝後,丁玲來到北京,參加一個補習學校的文化課學習,還去北京大學旁聽,打算去法國留學。認識戲劇家洪深後,夢想當電影演員;認識南國劇社的田漢後,想當戲劇演員。但是 ,接觸藝人圈子,又厭惡那種生活。年輕、對未來充滿無限憧憬的丁玲,此時胸中漲滿豐盈的情感,有許多話要盡情傾訴;于是,她拿起筆,創作第一篇短篇小說《夢珂》。小說投寄上海的《小說月報》,正好是葉聖陶主編,隻把她的處女作改動幾個錯别字,就刊發在突出位置。葉聖陶發現了這位文壇新人的創作潛力,寫信讓她再寄新作。不久,丁玲寄出《莎菲女士的日記》。這兩篇作品,如清代詩人趙翼說的:“古來傳世人,出手爆雷電。”早期的兩篇作品,出手就驚動文壇,是丁玲的成名作,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上大學時認識瞿秋白這個引路人,投稿時遇到葉聖陶這個伯樂,丁玲對從事文學創作堅定了信心。多少年後,她的“問題解決了”,想起曾扶植她走上文壇的葉聖陶,登門拜訪,談話間對葉老說:“您要不發表我的小說,說不定我就不會走這條路。”葉老感懷舊誼,填詞一首,喟然長歎他與丁玲的文字因緣。
在現代文學史上,有哪位女作家曾得到同時代的兩位偉人的贈詩?隻有丁玲,沒有之一。按丁玲的性格,隻拿起筆寫點于事無補的小說,是不可能的。她加入左聯,認識魯迅,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創刊時就去魯迅家裡征求意見,從魯迅那裡找刊物插圖。胡也頻犧牲後,她又被國民黨逮捕,魯迅聞傳言,以為丁玲被殺,就寫了“《悼丁君》:如盤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出獄後,丁玲輾轉潛入陝北,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由一個在大城市裡從事小說創作的新女性,大幅度轉身,成為民族解放大軍中的一員。剛到陝北,黃土高原上開歡迎會,歡迎這位來自上海的名作家。在黨的支援下,丁玲籌備文協,并當選中國文協主任。曆史上中共上司的首屆文藝家協會,是丁玲一手創辦的。天下英才盡入彀中,毛澤東多高興!丁玲随彭德懷到了三原前線,毛澤東填詞,用電報發到前線,詞牌《臨江仙》:“壁上紅旗漂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軍。”魯迅、毛澤東為丁玲寫的詩詞,是一位女作家在人生道路上的兩座裡程碑,也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
1949年後,丁玲在文學界擔任上司,主編《文藝報》《人民文學》,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還是中宣部文藝處長。那時的中宣部建制,處就是司局層級。不管是在協會還是在黨的上司機關,丁玲以她的文學成就和革命資曆,都處于很高的地位。她在河北參加土改的收獲,是創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自從到陝北參加革命後,她漸漸掌握了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既熟悉一個政治集團的語言文化,又熟悉農村和農民的生活。一個知識女性,一位大城市裡的名作家,在選擇了新的生活道路後,她的世界觀和文學觀都發生根本變化。《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得斯大林獎,在五十年代初,這個獎的分量是由中蘇友誼的熱度衡量的。在文學所,丁玲關心青年作家的創作,熱情扶植文壇新秀,至今還有那時的學員懷念他們的所長。不幸,一場暴風驟雨,折斷文苑大樹 ;丁玲停下了手中的筆。
回頭看,我喜歡丁玲早期的三篇作品:《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韋護》。這三篇作品,是青春期應季開的花朵 ,自然、熱烈、亮麗,一開始就袒露人的内心世界,把新時代女性的迷惘、戀愛和追求用火一般的文字烙印,一開讀就感到書頁湧出情感的熱流。這三篇作品,通過藝術形象,還寫了人的真誠,寫了有知識,有高尚情操的人對人生的态度。在《韋護》裡,有一段寫道:“他在自己身上看出兩種個性和兩重人格來!一種呢,是他從父母那裡得來的,那一生潦倒落拓多感的父親,和那熱情,輕躁以至于自殺的母親,使他們聰明的兒子在很早便有對一切生活的懷疑和空虛。是以他接近了藝術,他無聊賴的以流浪和極端感傷虛度了他的青春,若是他能繼續舞文弄墨,他是有成就的。但是,那新的巨大的波濤,洶湧的将他卷入漩渦了,他經受了長時間的沖擊,才找到了他的指南,他有了研究馬克思列甯等人著作的趣味。”這就是真實的瞿秋白。比照瞿秋白《多餘的話》,丁玲的小說也是曆史。
我讀過的兩部《丁玲傳》,周良沛的一部關注丁玲冤案的還原,出于正義感,主觀色彩較濃;王增如李向東的一部,特色在史料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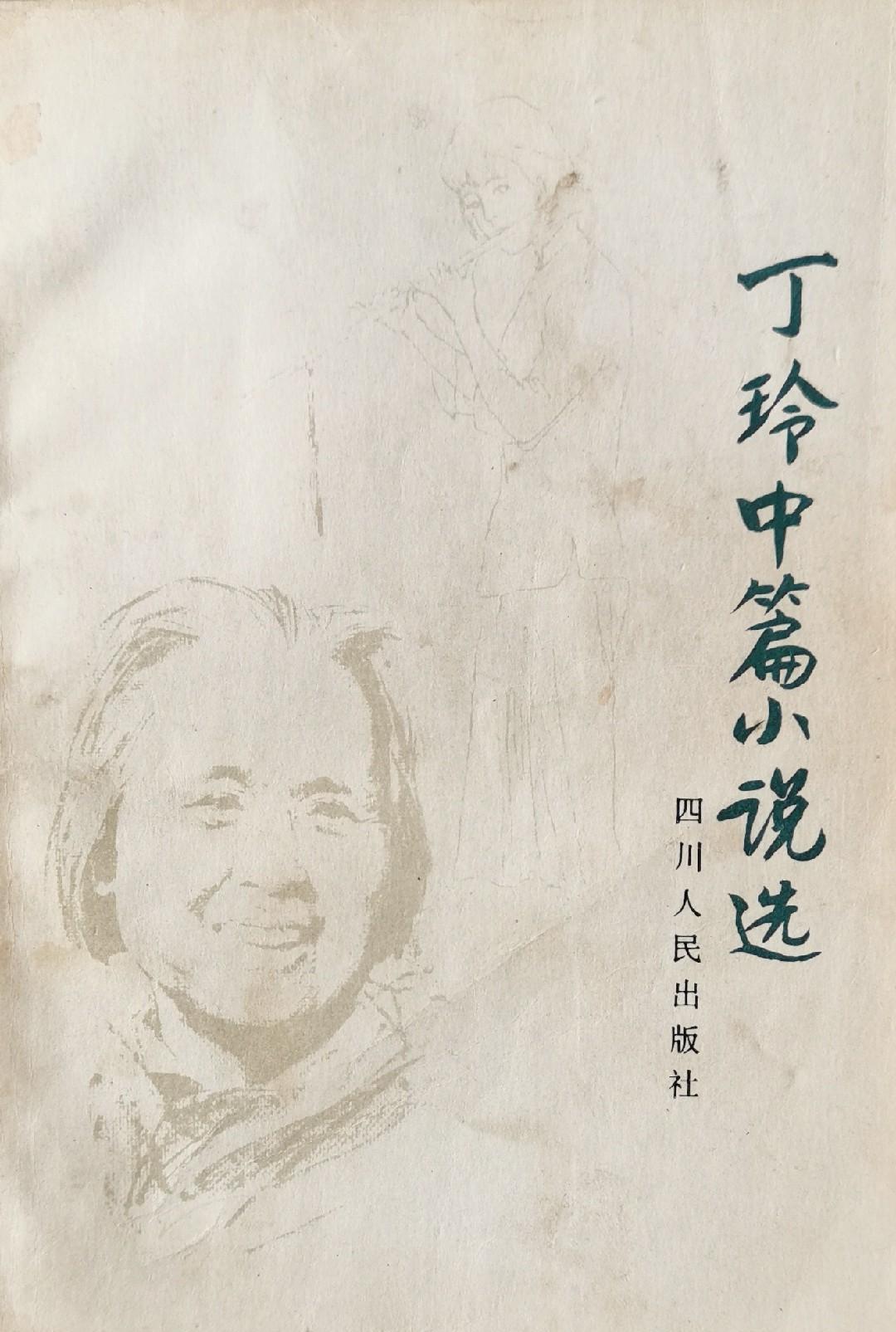
(此處已添加小程式,請到今日頭條用戶端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