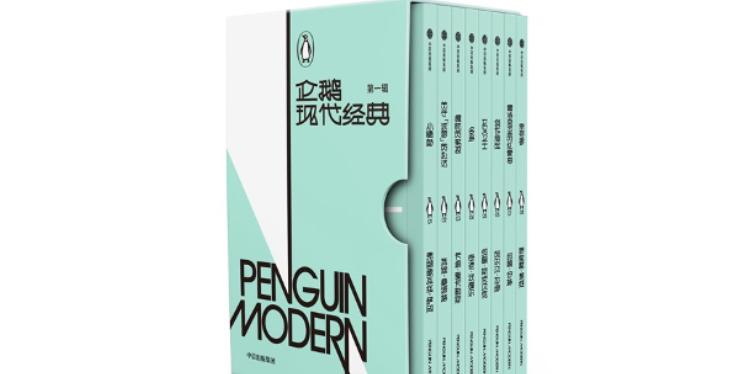
《企鵝現代經典(第一輯)》,作者:加缪、蘇珊·桑塔格 等,譯者:陳劍 程巍 等,版本:企鵝蘭登中國|中信出版社 2021年9月
如果把我們剛剛指出的那些背信棄義和敲詐勒索的案例放到一起來看的話,我們可以預料,總有一天歐洲會被集中營充滿,所有人都會被關起來,除了那些獄卒,于是他們将不得不互相關押。到最後隻剩下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被稱作“至高獄卒”。在這樣一個理想社會裡,“反對派”這個讓所有二十世紀政府感到困擾的難題,将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
當然,這隻是一個預言而已。盡管世界各國的政府和警察機關都懷着極大的善意,力圖實作這個幸福的局面,但我們距離實作它還很遙遠。比方說,目前在我們這些西歐國家裡,自由還是會受到官方的贊許。但這種自由總讓我想到某些中産階級家庭的窮苦女親戚。她成了寡婦,失去了她天然的保護者。于是,這個家庭好心地收留她,讓她住進頂樓的房間,家裡的廚房也向她敞開大門。有時,她會在禮拜日被拉出去公開展覽一圈,以證明這家主人的善良慷慨,沒幹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但在其他一切事情上,特别是在重要的場合,她都被要求緘口不言。另外,即使某個警察一時興起,在黑暗的角落裡對她動手動腳,也沒人會太放在心上,因為她之前也不是沒遇到過類似的事情,特别是在一家之主那裡。而且,畢竟,為了這點小事去找執法機關的麻煩太不值當了。我們必須承認,在東方,人們要更坦率。他們會直接把女親戚關進小儲藏室裡,然後插上兩條結實的門闩,進而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關于她的麻煩。看上去,約莫五十年後她就會被放出來,到那時理想社會将被徹底建成。然後,人們還會以她的名義舉辦慶典。但在我看來,那時她可能已經變成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古董了,我非常懷疑她是否還能有一星半點的剩餘價值。如果我們停下來思考這兩種關于自由的觀念,即儲藏室那種和廚房那種,并決定強行把兩者合并到一起,并在所有這些喧嘩之中被迫進一步壓縮這位女親戚的活動空間,就馬上可以看出,充斥在我們曆史中的是奴役而非自由,而我們所生活其間的這個世界也正是如此。每天早上,這個醜陋的世界都從我們閱讀的晨間報紙裡一躍而出,直撲到我們面前,讓我們日日夜夜都始終被憤恨和厭惡填滿。
最簡單,是以也最具誘惑力的做法就是去責怪政府,或是某些隐秘勢力的放肆行徑。何況他們也的确有罪,他們的罪責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們已經忘記是如何開始的了。但他們并非唯一應為此負責的人。畢竟,倘若自由始終必須依賴政府的鼓勵才能茁壯成長,那麼它很可能至今仍在搖籃裡,或者早已被埋葬了,墓碑上刻着“另一個小天使去了天堂”的字樣。據我所知,從來沒有人聲稱由金錢和剝削所主導的社會確定了自由與公正的勝利;也從來沒有人懷疑過,警察國家會将法律學堂開設在他們用來刑訊逼供的地窖裡。于是,當他們壓迫和剝削的時候,就僅僅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而已。如果有人盲目到将保護自由的工作托付到這些人手上的話,他就沒有權利對自由随即遭到玷污表示驚訝。如果說,今時今日,自由被束縛和侮辱了,這絕不是因為它的敵人施行了什麼狡計,隻是因為它失去了天然的保護者。是的,自由成了寡婦。但我們還必須補充一句,這千真萬确——讓自由成為寡婦的正是我們。
加缪
關心自由的人是被壓迫者,而它天然的保護者也一向要到被壓迫者中去尋找。在封建制度下的歐洲,公社城鎮成了自由的溫床;一七八九年革命中自由那昙花一現的勝利也是城鎮居民的功勞;十九世紀以來,勞工運動始終捍衛着自由和正義的雙重榮光,當時人們做夢都未想到去說它們二者之間的沖突是不可調和的。無論是體力還是智力的勞動者,都共同參與到塑造并在這個世界上弘揚自由的事業之中,直到它成了我們一切思想的基石,像空氣一樣不可或缺卻鮮少被我們特别注意,直到它突然被奪走,我們才發現自己命不久矣。如果今天自由在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區都在逐漸退潮的話,這很可能是因為奴役的手段從未像今天這樣被如此冷漠而精心選取過,或從未如此行之有效過,但同時也是因為自由的天然捍衛者們出于疲勞,出于絕望,或是出于有關“政策”和“效率”的錯誤觀念而背棄了它。沒錯,二十世紀的大事件之一便是革命運動抛棄了自由的價值。從那一刻起,某種希望就從世界上消失了,于是每個自由人都陷入了孤獨之中。
自二十世紀初,一種流言開始廣為傳播,并逐漸變得越來越有力量,即自由隻是個布爾喬亞式的騙局。這個定義搞錯了一個詞語的位置,而我們今天仍然在為這個錯位付出代價。正确的說法應該是:布爾喬亞式的自由是個騙局——而非所有自由。事實上我們隻需要說布爾喬亞式的自由不是自由,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隻是自由的雛形。但有一些自由千真萬确地需要我們去争取,并且一旦抓住就永遠不能放手。誠然,對于那個白天被拴在機床旁邊無法脫身,夜裡則要與全家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裡的男人來說,沒有什麼自由可言。但這個事實所譴責的應該是一個階級、一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所施行的奴役,而非自由本身。如果沒有自由,我們中最窮困的那些人就活不下去,因為即使社會在一夜之間改頭換面,變得能讓所有人體面舒适,它将仍然是野蠻的,除非自由得勝。僅僅是因為布爾喬亞社會談論自由卻不實踐它,勞工們的世界就該同樣放棄實踐自由,而隻是因為自己并不空談它而自豪嗎?無論如何,混亂的确産生了,自由在革命運動中逐漸成了一個壞詞,因為布爾喬亞社會把它用作騙局。人們開始隻是合情合理地、健康地拒絕相信布爾喬亞社會對自由的挾持,而到後來他們開始不相信自由本身。在最好的情況下,自由被推遲到了遙不可及的未來,在那之前人們被禁止談論它。他們給出的理由是我們需要首先實作正義,然後才輪到自由,就好像一群奴隸還能指望獲得正義似的。還有些強硬的知識分子會向勞工宣稱,隻有面包而非自由才是他們的利益所在,就好像勞工們不知道他們的面包多多少少是因為自由而得到的。我們要承認,面對布爾喬亞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不正義,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誘惑是巨大的。畢竟,我們中可能沒有哪個人,是從來不曾在行動上或思想上向這種誘惑屈服過的。但是,曆史在前進,而鑒于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東西,我們必須要停下來三思了。由勞工們掀起的革命在一九一七年獲得勝利,它标志了真正自由的降臨,是這個世界上曾有過的最偉大的希冀。但這場革命在四周強敵環伺, 面臨内憂外患的情況下,建立起了一支警察力量以自保。于是這世界上最偉大的希冀便逐漸淪為世界上最高效的高壓統治。與此同時,布爾喬亞社會那種虛假的自由卻未被撼動分毫。
總的來說,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是以那種犬儒主義的辯證法為特征的,它将不正義與奴役對立起來,并用其中的一方去加強另一方。當我們将戈培爾和希姆萊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赢家佛朗哥請進文化殿堂的時候,有人抗議說,佛朗哥的監獄裡每一天發生的事情都在無情地嘲弄銘刻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上的人權條款。對此,我們微笑着答道,波蘭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國,而在公共自由這方面,兩者其實是半斤八兩。這當然是個愚蠢的論證!要是你不幸非得把你的大女兒嫁給一個前苦役犯隊伍的頭頭,這也完全不構成你接下來應該将她的妹妹嫁給社會小組裡最優雅的探員的理由,一個家庭裡有一個敗類就夠多了。但這個愚蠢的論證卻能生效,正如我們每天都能見到的那樣。在令人作嘔的“比爛”嘗試之下,隻有一件事情是始終不變的——受害者永遠都是同一群人。自由的價值不斷地遭到侵犯和冒用,于是我們注意到,在世界各處,正義也和自由一起遭到了亵渎。
要怎樣打破這個極惡的循環呢?顯然,隻能通過立刻在我們自己和他人身上重新喚醒自由的價值,并永遠不再允許它被犧牲或被與我們對正義的要求割裂開來,哪怕隻是暫時。當下我們所有人的口号都隻能是以下這句:在自由的層面上寸步不讓,同時在正義的層面上寸土必争。具體來說,我們仍能保有的少數幾項民主主義自由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幻覺,我們必須強硬地捍衛它們。它們所代表的,恰恰是過去的兩個世紀裡所有偉大的革命勝利所留下的遺産。是以,它們絕不像諸多聰明的煽動家告訴我們的那樣,是對真正自由的否定。并不存在一種理想的、會在未來的某天同時被給予全人類的自由,像一份在你生命行将結 束時發放的養老金那樣。隻有需要一點一點地艱難戰鬥才能赢得的自由,而我們仍然擁有的這些隻是前進路上的階梯,它們當然遠遠不充足,但通向徹底解放的路徑的确是由它們構成的。如果我們放任這些自由被壓制,我們無法取得進步。相反,我們是在步步後撤和倒退了。而在将來的某一天,我們注定要重新沿着之前的足迹再度奮力前進,屆時人們将再一次付出汗水與鮮血的代價。
不,在今天選擇自由,并不意味着停止從蘇聯政權中獲利,并向布爾喬亞政權那方投誠。因為那樣反而相當于選擇了被奴役兩次,而且最惡劣的是,兩次都是替其他人選擇的。選擇自由并不等于背棄正義,雖然有些人這樣告訴我們。相反,今天選擇自由,是關于那些在世界各處受苦和戰鬥的人的,而這便是自由的意義所在。在選擇自由的同時我們也選擇了正義,并且說實話,從今往後,我們無法隻選擇其中之一而放棄另一個。如果有人拿走了你的面包,那麼他同時也壓制了你的自由。然而,如果有人剝奪了你的自由,不用懷疑,你的面包一定也遭到了威脅,因為從此你的面包就不取決于你自己和你的奮鬥了,而是取決于你主人的心情。縱觀全世界,凡是自由消減的地方,貧窮就會增加,反之亦然。如果說這個殘酷的世紀曾教會我們什麼的話,那就是一切經濟革命都必須是自由的,正如一切政治上的解放也必須要涵蓋經濟上的解放。被壓迫者不但希望自己可以從饑餓中解脫,也希望可以從主人的宰制之下解脫。他們都很清楚,隻有在他們可以成功抵抗和擊退所有那些主人之後,他們才能在實質上免于饑餓。
在結語部分我還想補充一點,那就是,自由與正義的割裂就等同于勞工和文化的割裂,而後者是一切社會罪惡的縮影。歐洲勞工運動面臨的困惑,一部分就源于它失去了它那真正的、可以在經曆一切失敗之後為其提供撫慰的家園,即對自由的信仰。然而,與之相似的是,歐洲知識分子面臨的困惑來自布爾喬亞和僞革命者共同制造的雙重騙局,這騙局将他們與他們本真性的唯一來源,即一切人的工作和苦難割裂開來;将他們與他們唯一的同盟,即勞工群體割裂開來。在我看來,稱得上貴族的隻有兩種人:勞動的貴族和智識的貴族,而我現在知道了,試圖讓他們中的一方去統治另一方是多麼瘋狂和罪惡。我知道這兩者共同組成了同一個高貴的整體,而他們的真理,以及最重要的,他們的有效性取決于聯合。我知道如果兩者被分開,他們就會放任自己逐漸被暴政和野蠻所壓倒, 但如果聯合在一起,他們就可以統治世界。這就是為什麼,一切緻力于拆散他們的聯盟、将他們分開的舉動,都是在向人類和人類最高的希望開戰。是以,所有獨裁政權最關心的莫過于壓制勞工和文化兩者。事實上,兩者都必須被噤聲,因為暴君們非常清楚,不然的話其中一方總會為另一方振臂高呼。于是,在我看來,當下知識分子可能的背叛方式有兩種,而這兩種背叛都是因為他接受了同一個東西——勞工和文化的割裂。第一種背叛常見于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他們希望壓迫和奴役勞工,以維持自己的種種特權。他們常聲稱自己在捍衛自由,但他們所捍衛的首先是自由賦予他們且隻賦予他們的一系列特權。第二種背叛則常見于那些自認為是左翼的知識分子,他們出于對自由的不信任,情願在“服務未來的正義”這個虛假的借口下,将文化以及文化所預先假定的自由置于管控之下。在這兩種情況下,無論是從不正義中得利的人還是叛變自由的人,都認定和支援了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割裂,而這注定會讓勞工和文化兩者都變得蒼白無力。他們同時貶低了自由和正義。
誠然,當自由主要由特權構成的時候,它侮辱了勞工并将他們與文化隔絕。但自由并不主要由特權構成,責任才是它最重要的構成部分。當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試圖将自由的責任置于自由的特權之前時,自由就将勞工和文化聯結到了一起,并釋放出唯一一種能夠促進正義的力量。我們行動的法則、我們抵抗的秘密可以被簡單地陳述如下:一切羞辱了勞工的東西,同時也羞辱了文化,反之亦然。而那革命的鬥争,那長達數世紀的朝向解放的努力,首先可以作為一場持續的、對雙重羞辱的抗拒而得到辯護。
說實話,我們還尚未完全擺脫這種羞辱。但時代之輪滾滾向前,曆史在變化,而我敢肯定總有一天我們将不再是孤軍奮戰。對我來說,我們今天能聚到這裡,這本身就是一個好的信号。各個工會的成員出于對我們的自由的關切而相聚,并準備着捍衛自由。這着實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從四面八方來到這裡,來贊頌團結和希望。我們面前的路還很長,但如果擾亂一切的醜惡戰争不緻爆發的話,我們最終總會有時間來描繪我們所需要的那種正義和自由。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今後必須平靜而堅決地拒斥一切此前被灌輸的謊言。不,自由不是建立在集中營或是殖民地那些被壓迫民族的苦難,或是勞工的貧困之上的!不,和平鴿絕不會栖息在絞刑架上!不,自由的力量絕不會強迫受害者的子孫們與馬德裡或其他地方的劊子手為伍! 至少我們從今往後應該确信這一點,同時也要确信, 自由不該是某個國家或領袖贈送給我們的禮物,而是一件我們必須每天都打起精神,齊心協力去赢取的珍寶。
原作者|加缪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