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寰 李彬:飛彈防禦與美國延伸威懾政策
作者:程志寰,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所學生;李彬,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内容提要】 對盟友提供的延伸威懾安全保證,是美國維持與盟友關系的重要基礎。冷戰時期,美國的延伸威懾主要通過核保護傘方式運作。為了應對冷戰後新的安全環境,以滿足新舊盟友的安全需求,美國開始通過飛彈防禦合作來提供對盟友的安全承諾與安全保證。這使得美國的延伸威懾從以核保護傘為核心,轉變為核保護傘與飛彈防禦并重的模式。與盟友發展飛彈防禦合作關系,對美國的延伸威懾體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其正面效益是,飛彈防禦合作使更多盟友能參與集體防務并貢獻更多力量,還可增強盟友與夥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鞏固美國的軍事上司地位。但是,飛彈防禦系統仍然不具備絕對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且美國必須在以飛彈防禦合作促進延伸威懾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如今,美國已開始加大力度,團結盟友進行新一輪的全球戰略競争。在此背景下,飛彈防禦延伸威懾模式的可持續性也将面臨考驗。
【關鍵詞】 美國核政策;延伸威懾;核保護傘;飛彈防禦;安全保證
一 引言
美國的延伸威懾政策是國際核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維持與盟友關系的重要基礎。延伸威懾指的是一個國家基于保護或防止盟友遭到攻擊之目的,對特定或不特定具有潛在攻擊意圖的國家發出動武之威脅。 延伸威懾并不一定需要仰賴核武器的作用,隻要一個軍事力量較強的大國與小國結成同盟,就能用正常軍力威懾敵人,使敵人不敢進犯小國。但在冷戰時期,由于受到兩大洋的阻隔,美國很難為了確定西歐和東亞地區盟友的安全,長期在這些地區維持與蘇聯的正常軍力平衡。是以美國為盟友提供“核保護傘”,将其作為延伸威懾的主要内容,以此抗衡蘇聯陣營在歐亞大陸上的正常軍力優勢。強調大國保護小國的延伸威懾關系本身就是一種不對稱的安全合作模式,美國為盟友提供核保護傘的延伸威懾政策,則進一步突顯美國與盟友之間的不平等狀态。這使美國與盟友的安全合作關系呈現出“同心圓”或“等級制”的結構模式。在這樣的安全合作關系中,盟友高度依賴核大國提供的安全保證,使核大國能夠對盟友進行一定程度的軍事制約和施加較大的政治、經濟影響。 由于延伸威懾政策是美國維持同盟和實施全球戰略的重要工具,美國理所當然地希望盡可能保持自己的“核壟斷”地位,以使其享有的特殊上司地位長久維持下去。隻要美國的盟友沒有獨立的核力量,它們就會在安全上更加依賴美國的延伸威懾,而美國也就更容易控制這些盟友。 然而,以核保護傘為核心的延伸威懾也有一些缺點,主要是核保護傘本身過于嚴厲、僵硬,缺乏應對複雜局勢的靈活性。是以,美國試圖将飛彈防禦納入其延伸威懾體系,用于在複雜局面下加強和塑造其與盟友的安全合作關系。
美國在冷戰期間就開始發展戰略防禦能力,其主要目标是追求對蘇聯的戰略優勢地位。這一目标在冷戰後得到了延續,美國大力發展并在本土和境外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企圖借此削弱大國競争對手中國和俄羅斯的核報複能力。随着冷戰後地區安全局勢的複雜化,美國的延伸威懾戰略思想開始随之調整;同時,美國的地區飛彈防禦能力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開始在地區問題中發揮作用。這使飛彈防禦議題在美國延伸威懾政策中的重要性升高;確定地區形勢穩定的延伸威懾政策也逐漸成為美國發展和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的另一重要目标。美國的延伸威懾形式也開始從過去以核武器為主軸的模式,轉向更多地依靠飛彈防禦系統的發展和部署。
目前,美國在對一些盟友承諾提供核保護傘的前提下,更加強調與盟友開展飛彈防禦合作,逐漸形成“以核保護傘為核心,以飛彈防禦的發展與部署作為重要補充”的延伸威懾模式。是以,飛彈防禦已成為美國延伸威懾中的重要議題,為塑造美國與盟友的安全合作關系提供了重要支援。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與盟友的關系受到震蕩與考驗,飛彈防禦的費用分攤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分歧點。現在拜登政府又試圖重新恢複美國對盟友的信用,但是,美國與盟友之間關于飛彈防禦費用分攤的難題并未消除。今後,飛彈防禦合作将是美國與盟友延伸威懾關系中的一個核心話題。
二 冷戰後美國延伸威懾面臨的挑戰
冷戰後地區局勢日益複雜,美國為了強化其全球影響力,不斷拓展在各地區的新盟友和安全夥伴。這增大了美國延伸威懾政策的負擔,突顯出美國核保護傘延伸威懾模式的困境,迫使其延伸威懾政策必須針對新舊盟友和夥伴的安全需求做出适度的調整。
(一)新舊盟友的安全需求
冷戰後美國的延伸威懾政策主要面臨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數量的持續增加。這主要展現在北約向中歐、東歐地區擴張,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不斷擴大,目前美國仍然有繼續拉幫結派,招納新的夥伴,與它們建立安全合作關系的戰略考量。這使美國的延伸威懾政策需要應對的新成員不斷增加,美國必須想辦法滿足這些新盟友和夥伴對其安全承諾的需求。第二個問題是美國的舊盟友卷入更多新的地區沖突與對抗,它們更迫切需要美國提供新的安全保證。
美國延伸威懾安全夥伴在冷戰後的增加首先表現在北約的東擴上。北約成員國從冷戰結束之際的16國擴大到目前的30國。北約東擴的熱潮出現在20 世紀90年代末和21 世紀初期。1994年,北約提出“和平夥伴關系計劃”(Partnership for Peace),開始與中東歐地區國家建立軍事合作關系,使非成員國能參與到同北約的聯合演練中,并成為加入北約組織的候選國,這也是北約漸進式擴大的第一步。從1997年到2009年,北約進行了三次東擴,近年來北約東擴的程序已放緩。最新加入北約的國家包括2017年加入的黑山,以及2020年加入的北馬其頓。目前,除了波黑是北約東擴的候選國,有意願加入北約的尚有格魯吉亞、烏克蘭、阿塞拜疆三國,是以北約還有繼續擴張的可能性。
在北約開始東擴的程序中,作為舊北約成員國的西歐國家總體上更顧及與俄羅斯的合作,擔心北約東擴會影響東西方關系緩和以及雙方在軍控領域的合作程序。中東歐國家則更擔心俄羅斯,将俄羅斯視為主要的威脅來源;它們急于加入北約,在加入北約之後樂于與美國建立更牢固的軍事合作以制衡俄羅斯。在2008年的格魯吉亞戰争以及2014年的克裡米亞事件後,舊北約盟友也加深了對俄羅斯的疑慮,新的北約國家則更為倚重美國的保護。北約作為一個整體加重了對美國延伸威懾的需求。雖然北約盟友已獲得美國核保護傘延伸威懾十分有力的安全保證,但是新加入北約的國家境内沒有美國部署的戰術核武器,它們對于含義模糊的核保護傘也不滿意,希望與美國有更多的飛彈防禦合作,以增強與美國的軍事關系。
另一批在冷戰後成為美國延伸威懾安全夥伴的是中東海灣地區的國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減小,美國趁勢擴大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1991年海灣戰争後,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主導地位已然确立,開始大張旗鼓地在該地區建立軍事基地,部署大量軍力。九一一事件以及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後,美國繼續擴大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這段時期,美國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簡稱“海合會”)的六個成員國(沙特、阿聯酋、阿曼、巴林、卡達和科威特)逐漸形成緊密的軍事合作關系。美國不僅在海合會國家境内有多處軍事基地,而且在冷戰後對中東地區發動的多次戰争中,積累了與海合會國家共同作戰的豐富經驗。盡管美國與這些中東國家并未簽署正式的盟約,但已形成“準同盟”的安全合作關系。 随着伊朗核計劃與飛彈能力的發展,以色列和海合會國家對美國的安全保證也産生了更強烈的需求。
在亞太地區,美國的傳統盟友如日本、南韓和澳洲則開始關注新的威脅。美國認為,北韓不斷進行核試驗與發展飛彈能力,對美國延伸威懾體系造成了沖擊。一個具有核打擊能力的北韓可能通過對美國東北亞盟友(日本、南韓)的威脅,逼迫美國讓步,使美國不願在日本面臨高風險的狀态下進攻北韓半島,抑或是防止日本支援美國幫助防禦南韓。 美國和亞太地區盟友聲稱的第二個威脅,來源于中國的正常與核軍力的現代化。所謂的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成為美國與亞太地區盟友發展和部署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借口。
近年來,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更加重視整合亞太與印度洋地區的“印太戰略”。從2021年1月的《美國印太戰略架構》報告(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看,美國最希望和印度建立緊密的安全合作關系。該報告提出,美國在印太地區要建立以美國、澳洲、日本和印度為主軸的四邊安全架構;要與印度建立牢固的防務合作與協作關系;擴大對印度的軍售和軍事技術轉讓,将印度提升為主要的防務夥伴;與印度在網絡、外空安全及海域感覺方面建立夥伴關系;擴大美印情報共享和分析交流,建立更強有力的情報夥伴關系;等等。 可以看出,美國将印度發展為更緊密的盟友或戰略夥伴的意圖十分明顯,不僅急于拓展與印度的雙邊防務合作,更期望能把印度與亞太盟友日本、澳洲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跨印太地區的多邊軍事合作體系。由于印度也将中國正常與核軍力的現代化視為強大的“威脅”,是以也期望能深化與美國的軍事安全合作關系。
(二)核保護傘延伸威懾的困境
雖然核保護傘與正常延伸威懾關系都建立在提供保護的大國和受保護的小國有共同敵人的基礎上,但是核保護傘的要求比正常延伸威懾更嚴格。如果盟友與核大國有共同敵人,但同時又有其他不是核大國敵人的重要對手,就會使核保護傘關系難以建立。其原因在于,正常同盟的目的除了威懾之外,更重要的是備戰,備戰可以秘密進行;而核保護傘用來懾止敵人對盟友的進攻,需要公開承諾才能造成延伸威懾的效果;如果核大國不履行其公開承諾,就會損害核保護傘的可信度。是以,對于核大國來說,在盟友與一個不是自己敵人的對手針鋒相對,甚至采取失控的冒進行為時,對盟友提供正常延伸威懾,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例如大國可以選擇不直接參與盟友和其對手的沖突或戰争,而是通過秘密管道為盟友提供軍備和情報。但是,這種靈活性無法存在于核保護傘關系中。
學者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以20世紀60年代美國放棄對以色列提供核保護傘,以及19世紀末的法俄同盟為例說明了這一差異。法俄同盟可以通過秘密方式進行,這不影響兩國各自與其他歐洲強權國家建立同盟關系,也不影響兩國私下為戰争所做的軍事協防準備。但核保護傘安全承諾則必須要公開才能具備威懾效果。若美國明确、公開承諾為以色列提供核保護傘,勢必會對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這對美國來說代價太高,最終美國不得不放棄該做法,轉而以非公開承諾的方式與以色列結成實質性的同盟。
在奧巴馬政府初期,為了防止中東地區的盟友和夥伴以伊朗核計劃為理由發展核武器,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裡曾考慮過為這些盟友和夥伴提供核保護傘,但引起美國國内的争論。 中東的阿拉伯盟友若與以色列發生沖突或戰争,美國絕無可能履行核保護傘承諾,是以,阿拉伯國家不會對美國的核保護傘承諾産生較強的信任感。 進一步說,若美國在中東的核保護承諾不能兌現,很可能會導緻它提供給其他地區盟友的核保護傘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最終核保護傘就形同虛設。是以對美國來說,為中東地區盟友提供核保護傘是難以做到的。
上述情況表明,如果美國籠統地為一些盟友提供核保護傘,勢必會得罪這些盟友的敵人;如果這些盟友的敵人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會感到得不償失;美國的盟友也不會相信其安全承諾,核保護傘的信用和效果都會下降。理論上,美國可以通過條約或協定,限定其提供的核保護傘隻針對與盟友或夥伴的共同敵人。但是,核保護傘的公開宣示内容往往是模糊的,在實際操作中,公開限定特定敵人常常不容易實作,或者會削弱盟友或夥伴的安全期待。
另外,在延伸威懾關系中,因為受保護的盟友經常會擔心被抛棄,是以單憑核保護傘的“懲罰性威懾”(deterrence by punishment)無法緩解盟友對于被大國抛棄的疑慮。盟友更希望大國提供的是“拒止性威懾”(deterrence by denial),借此深化彼此受牽連的程度和風險,降低盟友被抛棄的疑慮。 這也是大國必須時常以各種形式的“安全保證”(security assurance)來強化延伸威懾關系的主要原因。延伸威懾的安全承諾大緻上可依照安全保證的程度分為三個級别。第一種級别,對盟友來說,安全保證效果最弱的是僅與大國簽署正式的盟約,或核大國僅以公開聲明的方式強調會使用核武器保護盟友與夥伴。公開對盟友和夥伴作出安全承諾,會形成觀衆成本,對核大國造成“制約”(hand-tying)效果;若其違反承諾,國家信譽會嚴重受損。 有學者認為隻要一個國家與核大國簽署盟約,就能建立核保護傘延伸威懾的可信度,有效懾止對手或挑戰者的進攻。 但從曆史經驗來看,安全保證措施的功能主要是用來安撫盟國的。如同前英國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提出的,“美國威懾蘇聯隻需要5%的報複能力可信度,但卻需要95%的可信度來安撫盟國”。 這說明即便與核大國的盟約關系能對挑戰者産生威懾作用,但仍然無法對盟友産生有說服力的安全保證。第二種級别是核大國與盟友或夥伴建立制度化的延伸威懾磋商機制。如此一來,盟友或夥伴就能夠通過該機制表達自己的安全需求,也能擷取核大國的軍事規劃等相關資訊。這使盟友或夥伴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核大國的延伸威懾政策,更加信賴與核大國的延伸威懾關系。 第三種級别是核大國在盟友或夥伴境内進行前沿軍事部署,包括直接将核武器部署在盟友境内,甚至授予它們核武器使用權,或建立讓盟友一同參與核戰略決策的“核共享”政策。前沿部署在延伸威懾中可發揮關鍵性的“觸發機制”(tripwire)作用。戰争爆發時,這些前沿部署也可能會遭到打擊,使核大國被迫參戰。如果一個大國願意在和平時期在盟友境内進行更多、更昂貴的前沿部署,就意味着當這些前沿部署受到敵人攻擊時,大國更願意投入到保護盟友的戰争中。 是以,這些做法能将核保護傘的安全承諾具體化為“可見的”行動,展現出大國使用核武器保護盟友的決心,也能使盟友對大國的安全承諾更有信心。
以上三種級别的安全保證中,隻有第三種“前沿部署”的方式最明确,也最能保證大國在沖突發生時不會抛棄小國。但在冷戰結束之後,美國陸續撤除了在全球的大部分戰術核武器部署,目前隻剩下約200件核重力炸彈還存放于北約五個國家(德國、比利時、意大利、荷蘭和土耳其)境内。出于核安保的考慮,美國不太可能再将大量戰術核武器部署到盟友境内。面對廣大盟友和夥伴的安全焦慮感,美國隻能以其他形式的前沿部署確定延伸威懾的可信度。
綜上所述,面對各地區新舊盟友和夥伴的威脅認知和安全需求,美國的核保護傘延伸威懾方式逐漸陷入幾種困境。第一,美國無法提供核保護傘給某些地區的新盟友和夥伴,也無法運用核保護傘來吸引或者安撫新盟友。第二,出現新的地區威脅,增加了盟友和夥伴卷入地區性低烈度沖突的可能,核保護傘無法在這類沖突中發揮作用。第三,核保護傘的作用是“懲罰性威懾”,但盟友更希望獲得“拒止性威懾”。第四,美國在大幅撤除境外核武器部署後,其延伸威懾政策面臨着缺乏確定機制的問題。對一些盟友來說,美國的核保護傘過于抽象和僵硬,在千變萬化的軍事對抗中,美國是否願意提供核保護傘以及核保護傘是否能夠發揮作用,存在不确定性。面對這些困境,美國開出了飛彈防禦這個“藥方”。
三 美國以飛彈防禦合作強化延伸威懾的戰略
為了回應各地區新舊盟友和夥伴的安全需求,消除核保護傘延伸威懾的缺陷,美國的延伸威懾政策逐漸從以核保護傘為主軸的模式,轉變為更加倚重飛彈防禦合作的形态。這一點突出展現在冷戰後美國延伸威懾戰略思想和理論的發展,以及延伸威懾政策的具體規劃和執行上。
(一)冷戰後美國以飛彈防禦強化延伸威懾的戰略思維和理論
冷戰期間,美國的飛彈防禦對其延伸威懾有一些間接的影響。這個時期美國飛彈防禦的主要目的是攔截蘇聯的戰略飛彈,這樣的飛彈防禦從理論上說可能改變美國核威懾的有效性,是以,美國盟友會從關心核保護傘可信度的角度關注美國的飛彈防禦。然而在這個時期,飛彈防禦還沒有實質性地獨立進入美國延伸威懾體系。冷戰結束後,飛彈防禦開始成為美國延伸威懾政策的重要工具,主要與其兩種戰略思維的轉變有關:一是對冷戰後安全環境和威脅來源的重新評估;二是對飛彈防禦功能的重新定位。
冷戰結束前夕,東西方關系緩和,美國與蘇聯達成了一系列限制和削減戰略武器的條約,美國評估發生大規模核戰争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與此同時,一些開發中國家開始發展飛彈能力,特别是更遠端的飛彈打擊能力,這使美國開始重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問題。冷戰後美國戰略學者開始關注新的國際格局下的安全環境,将其稱為“第二核時代”,并提出了有别于美蘇兩極對峙下的威懾理論。“第二核時代”的主要特征是,對美國來說,國際體系中不隻存在如俄羅斯和中國這樣具備成熟核反擊能力的核大國對手,還出現了更多擁有小規模核武庫的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北韓,以及企圖獲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國家(如伊朗、叙利亞、利比亞)和恐怖組織。 一些學者認為,這些國家的決策行為不一定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而可能基于非理性的考量, 這使美國及其盟友面臨的安全環境更加複雜,也将大幅提升核威懾的不确定性。是以,冷戰後美國的核威懾戰略必須逐漸轉向以“應對不确定性”為主軸。 為了應對核威懾的不确定性,確定面臨地區性威脅和挑戰的盟友能持續依賴美國的延伸威懾,美國必須放棄冷戰時期維持與對手之間的戰略穩定性的做法,尤其是對于一些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地區挑戰者,美國更不應該接受自己的脆弱性。 飛彈防禦成為應對這種複雜安全環境的重要工具。
從技術上和财政上看,發展針對核大國的大規模戰略武器攻擊的飛彈防禦系統是非常困難的。冷戰時期裡根政府提出的“戰略防禦倡議”(SDI)構想也是難以為繼的。但是針對核武器數量及飛彈能力有限的地區挑戰者,飛彈防禦仍可能降低美國的脆弱性,使這些國家無法對美國構成威脅。再加上“動能攔截器”(Kinetic Killing Vehicle,KKV)技術的發展,使陸基和海基“國家飛彈防禦”(National Missile Defense)和“戰區飛彈防禦”(Theater Missile Defense)被認為是可負擔且具一定有效性的。是以,冷戰後美國逐漸将從前追求對蘇聯戰略優勢的飛彈防禦系統,轉變為針對地區性挑戰者有限飛彈攻擊的飛彈防禦系統。
除了上述應對地區挑戰者的有限飛彈攻擊之外,亦有許多學者指出,飛彈防禦在延伸威懾中能發揮更多強化安全保證的作用,其部署也是美國與盟友和夥伴延伸威懾關系中的重要確定機制。美國空軍國家安全研究所的學者賈斯廷·安德森(Justin V. Anderson)等人指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部署可以抵消對手的飛彈能力,使對手用彈道飛彈的脅迫或攻擊失效,借此美國就能為盟友和夥伴實施更有效的“拒止性威懾”。 另一位學者布拉德·羅伯茨(Brad Roberts)認為,飛彈防禦在和平時期的延伸威懾戰略價值包括:展現美國和盟友對抗威逼和侵略的決心;将更高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強加給那些想通過擷取核武器來挑戰美國地區安全承諾的國家;有助于美國與盟友和安全夥伴建立更緊密協防合作關系;可以使無核武器的盟友也能貢獻己力,一同增強延伸威懾體系。
将飛彈防禦部署或合作作為延伸威懾的確定性措施,具有兩個方面的優勢。第一個優勢是美國可以借此與盟友建立更多樣、整合性更強的磋商機制。由于核武器具有高度敏感性,加上長期以來的防擴散政策,美國僅與北約建立以核保護傘或核共享為基礎的正式合作機制。而圍繞飛彈防禦合作建立的協商機制則更加靈活。這些機制可以是雙邊的,如美韓之間的“延伸威懾政策委員會”(EDPC)和“飛彈應對能力委員會”(CMCC);也可以是地區性的,如美國與海合會國家的“戰略合作論壇”(SCF);甚至可以是全球性的,如美國在2019年《飛彈防禦評估》報告(MDR)中提到的“靈活巨人論壇”(Nimble Titan),就是一個以飛彈防禦的合作、磋商、兵棋推演為主題、開放性的全球性論壇,美國的所有盟友和夥伴都可自由參加。“靈活巨人論壇”由美國戰略司令部負責,兩年舉辦一次,目前參與國家已達24個,分别來自歐盟、亞太、北美、海灣地區。2019年的《飛彈防禦評估》報告強調,要建立更有效的飛彈防禦網絡,需要美國與盟友、夥伴的飛彈防禦訓練、演練,以及盟友、夥伴在美國飛彈防禦試驗中更大的參與度。而“靈活巨人論壇”正是推動跨國合作的重要方式,包括加強對飛彈攻擊的威懾和防禦的作戰一體化試驗。 以上這些雙邊、區域或全球性飛彈防禦協商機制都能強化盟友對美國延伸威懾的信心。
第二個優勢是飛彈防禦的前沿部署在盟友心目中有展示作用和捆綁作用。飛彈防禦系統除了攔截器之外,還包括許多雷達傳感器,以及進行資料分析的指揮控制與通信系統等。這些裝置設施的部署都是一種昂貴的投資,能扮演“觸發機制”,增強盟友對美國延伸威懾的信心。 當盟友面臨較低烈度沖突的風險,不相信美國核保護傘作用的時候,美國部署在盟友和夥伴境内或地區中的飛彈防禦系統就可能展示美國的安全承諾,增強它們對美國延伸威懾的信心。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澳洲。雖然兩國之間是正式的安全同盟關系,但美國提供給澳洲的核保護傘一直處于模糊狀态,美國從來沒有以任何官方檔案或口頭方式公開宣布過使用核武器保護澳洲的意願或決心。但澳洲對美國的核保護傘深信不疑,而且在冷戰後曆次釋出的《國防白皮書》中,都會提到美國的核保護傘對澳洲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促使澳洲相信美國核保護傘存在的關鍵因素,就是美國在澳洲部署的具備重要戰略意義的相關設施。在澳洲西北角(North West Cape)設立的極低頻訊号發射台,是維持美國核潛艇通訊的重要設施;在松樹谷(Pine Gap)與努倫加(Nurrungar)的全球衛星監控系統可以對東半球的飛彈發射進行預警,以及監控其他國家的核試驗。澳洲認為這些設施表明自己已經處在美國延伸威懾體系之中,也是美國對澳洲核保護傘可信度的有力依據。
當美國政府推動在歐洲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的時候,西歐的北約國家顧慮重重,而新加入北約的中東歐國家則紛紛表示願意在本國部署飛彈防禦的部件。部署在這些國家的飛彈防禦部件對于抵禦攻擊這些國家的飛彈幫助很小,而且引起了俄羅斯的強烈不安,但即便如此,這些中東歐國家,也要引進美國的飛彈防禦部件。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本國領土内獲得“永久性的美國軍事設施”,使它們與美國和北約的防務有更直接、明确的關聯性。
(二)美國運用飛彈防禦強化延伸威懾的具體做法
在上述戰略思維和理論的指導下,冷戰後,美國開始将飛彈防禦與延伸威懾政策相結合,運用飛彈防禦來補強延伸威懾。綜觀美國的實際政策可以發現,冷戰後美國各屆政府都特别重視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發展,以此開展與各地區盟友和夥伴的安全合作關系,并強化對它們的安全保證。以2000年為分水嶺,大緻可将美國的飛彈防禦延伸威懾政策分為兩個時期。2000年以前是美國逐漸将飛彈防禦與延伸威懾結合的轉型期;進入21世紀以後,随着陸基、海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更趨成熟,美國一方面通過飛彈防禦合作與新盟友和夥伴建立安全關系;另一方面也借此建立與飛彈防禦合作相關的協商機制,制訂共同研制計劃,并通過在這些國家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來增強對它們的安全保證。
老布什政府是實作延伸威懾轉型的重要推手。1991年,老布什政府時期提出了“防禦有限飛彈攻擊的全球保護系統”(GPALS)計劃,其中就包括将飛彈防禦運用于延伸威懾,使其獨立發揮延伸威懾作用的政策規劃。該計劃将裡根時期的“戰略防禦倡議”進行調整和縮減,強調要提高發展戰區飛彈防禦的優先性,以應對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盟友和夥伴面臨的地區性威脅。 該計劃還特别宣傳了“愛國者”反導系統在海灣戰争中攔截“飛毛腿”飛彈的成功率。 至此,美國與盟友和夥伴在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發展和部署層面的合作,開始成為維持延伸威懾關系的重要方式,而且在保護、安撫、上司和整合盟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克林頓政府時期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已開始具備多層次、立體化、全方位的特征,可攔截從短程到遠端的各種射程飛彈,再加上海基與陸基、高空與低空防禦系統的配合,使其能覆寫更廣的防禦空間。 而且在此時期,美國開始實質性推動将戰區飛彈防禦與延伸威懾結合。在1993年的北約國家軍備主管官員會議上,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約翰·多伊奇(John Deutch)建議将戰區飛彈防禦列為北約國家加強防務合作的五大領域之一;1994年,在北約布魯塞爾首腦會議期間,美國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Les Aspin)要求北約接受美國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以此反制擴散問題。 當時北約國家并未面臨任何戰區飛彈的潛在威脅,但美國仍敦促北約接受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從中可以看出,美國開始認真地将飛彈防禦與其延伸威懾政策緊密挂鈎。
小布什政府更加明确地将飛彈防禦與確定盟友安全的延伸威懾政策整合在一起,認為部署在美國和盟友境内的飛彈防禦系統是全球多層次防禦體系的重要部分。2002年,小布什政府退出《反導條約》,同年12月,釋出“第23号國家安全總統令”(NSPD-23),提出了關于與盟友合作發展飛彈防禦的三點計劃:發展和部署有能力保護美國本土、駐外基地和盟友的飛彈防禦系統;以鼓勵盟友企業參與的方式建構與美國國家安全一緻的飛彈防禦計劃;促進同盟體系的飛彈防禦合作,包括雙邊性質或在北約架構下的合作。
奧巴馬政府深化了美國與各地區盟友和夥伴的飛彈防禦合作政策,擴大了美國在各地區的飛彈防禦部署。其運用飛彈防禦強化延伸威懾的做法展現出對小布什政策的延續性,而并非中斷。 美國2010年的《彈道飛彈防禦評估》報告(BMDR)提出,美國的飛彈防禦能力必須有足夠的彈性,以适應各種威脅變化;美國将在飛彈防禦領域上司更廣泛的國際合作”。 在實際做法方面,奧巴馬取消了小布什在東歐國家部署陸基中段反導系統(GMD)的“第三站點”(Third Site)計劃, 但大幅度推進了美國與盟友的飛彈防禦合作。在歐洲地區,奧巴馬政府推出了“歐洲分階段适應性飛彈防禦方案”(EPAA),計劃從2010年到2020年,分四個階段逐漸強化美國在歐洲地區的飛彈防禦部署。 在亞太地區,奧巴馬政府除了在日本部署新的X波段雷達站之外,還與日本進一步展開“标準-3”Block IIA攔截彈的研制合作;2016年,與南韓達成在南韓境内部署薩德系統(THAAD)的協定。在中東地區,奧巴馬政府大力推動與海合會國家的飛彈防禦合作,使其成為美國與中東地區盟友建立延伸威懾關系的主要途徑。2012年,希拉裡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舉辦的海合會安全論壇上提出要加大與海灣地區國家的飛彈防禦合作;在2013年的“戰略合作論壇”中,美國與海合會國家達成擴充飛彈防禦合作的共識,海合會國家同意将緻力于加強在彈道飛彈防禦方面的合作,最終部署一個覆寫整個海灣地區、可搭配性的飛彈防禦體系,保護海合會國家的領土和資産免受彈道飛彈的威脅。 除此之外,為了制衡中國而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後,奧巴馬政府也不斷強化與印度的飛彈防禦合作關系。2015年,美國和印度簽訂《美印國防技術與貿易倡議》(DTTI),為美印飛彈防禦合作創造更大的空間。2016年,印度成為美國的“主要軍事夥伴”;美印還簽署了《後勤交流備忘錄協定》;加上印度總理莫迪缺席不結盟運動峰會,這三大事件被視為印度脫離“不結盟政策”傳統,逐漸向美國靠攏的象征。
對于為盟友與夥伴提供延伸威懾的政策,特朗普的态度比較特殊:對于給予盟友和夥伴安全承諾以及強化安全保證缺乏前任那種強烈意願,因為他認為美國長期以來在國際多邊機制和延伸威懾政策中的投入,是一種過度“慷慨”的行為,也導緻美國長期受到盟友和競争對手的“利用”。 但是,特朗普願意在盟友和夥伴支付或分攤更多費用的前提下,強化與它們的飛彈防禦合作與延伸威懾關系。在2019年的《飛彈防禦評估》報告(MDR)中,特朗普政府仍然規劃了多項與盟友和夥伴的合作計劃。例如,在東亞地區,支援日本研制更多“宙斯盾”軍艦,原本還計劃2023年在日本部署兩台陸基“宙斯盾”系統,但日本取消了該計劃;幫助南韓更新更先進的“愛國者”反導系統。在歐洲地區,随着“歐洲分階段适應性飛彈防禦方案”的完成,下一階段美國計劃協助北約國家提升它們自身的飛彈防禦能力。在中東地區,美國持續以軍售方式将飛彈防禦系統賣給海合會國家,沙特阿拉伯正與美國進行購置“薩德”系統的協商。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還與北約、東亞盟友展開多輪軍費分擔談判。2017年,特朗普一上任便要求南韓承擔10億美元的“薩德”系統部署和建設費用,但遭到韓方的拒絕。美韓在2018年展開駐韓美軍軍費分擔談判,特朗普要求南韓負擔駐韓美軍的經費,再加上額外50%的費用,南韓雖再次拒絕,但也承諾會逐年上調負擔的經費。 2021年剛上任的拜登政府曾大力批評特朗普的做法,且不斷強調要重新鞏固與盟友和夥伴的關系,是以很可能會繼續通過飛彈防禦合作,強化對盟友和夥伴的延伸威懾政策。拜登政府也可能會要求盟友和夥伴為飛彈防禦合作提供更多費用,但态度不會像特朗普政府那麼任意和嚴厲。
四 飛彈防禦合作對美國延伸威懾的影響
随着美國更多地與盟友和夥伴開展飛彈防禦合作,支援其延伸威懾政策,該做法會對美國的延伸威懾政策同時産生正面和負面影響。美國延伸威懾政策的未來前景和走向,以及美國與盟友和夥伴在安全合作關系的發展趨勢,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能否妥善地應對飛彈防禦合作帶來的影響。
(一)飛彈防禦合作對美國延伸威懾的正面效果
學者凱文·法斯霍拉(Kevin Fashola)歸納出目前美國與盟友和夥伴開展飛彈防禦合作的五種模式:第一種是通過軍售将飛彈防禦系統賣給盟友和夥伴來增加地區性部署,這是美國與中東地區海合會國家的主要合作形式;第二種是“托管部署”,即以保護美軍海外基地為理由,直接将飛彈防禦系統部署在盟友和夥伴境内,美國在各地區都有這樣的做法;第三種是與盟友和夥伴合作研制和發展飛彈防禦技術,研究和試驗的共同成果自然會使盟友和夥伴擷取飛彈防禦能力,并增強相關部署,這是美國與以色列和日本的主要合作模式;第四種是相關資訊的共享;第五種是與盟友和夥伴開展飛彈防禦的聯合演訓。 以上五種以飛彈防禦為主軸的軍事合作關系,對美國的延伸威懾政策的正面效果包括:可增強盟友和夥伴的參與及分工程度,這不僅能減輕美國的負擔,還可以強化延伸威懾的可信度;能夠提高美國的軍事上司地位;提升盟友和夥伴之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向對手或敵人傳遞更強的延伸威懾信号。
首先,盟友和夥伴關于飛彈防禦的分工合作可以深化美國與它們的軍事合作程度。如法斯霍拉所述,以軍售方式将飛彈防禦系統賣給盟友,可強化盟友和夥伴自身的防禦能力,降低美國的協防負擔;而且盟友和夥伴買得越多,越能降低這些軍備的機關生産成本;還可以使美國飛彈防禦系統部署得更廣,提升雷達的偵測面積以及多層次防禦能力。這對美國而言完全是樁“一石三鳥”的好生意。與日本、以色列等科研能力較強的盟友和夥伴開展飛彈防禦系統的合作研制計劃,更可以大幅降低美國單獨研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通過飛彈防禦方面的共同研發計劃,美國可以與盟友進行專業分工,使各自能特别專精于某一分工領域。這不僅能減少開支,還能促進盟友和夥伴在各自專精的領域中實作技術突破。例如,日本是美國長期合作發展海基“宙斯盾”系統和“标準-3”系列攔截彈的夥伴;挪威與美國合作開發能攔截巡航飛彈、戰鬥機、直升機和無人機的“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NASAMS);以色列在美國的财政援助下,以研制針對中短程飛彈和火箭炮的高效能陸基飛彈防禦能力為主,目前以色列的“鐵穹”(Iron Dome)飛彈防禦系統号稱在實戰中攔截敵方火箭炮的成功率達到90%以上。 通過飛彈防禦研制方面的合作,美國不僅将盟友和夥伴的武器部署與美國整合到一起,還将盟友和夥伴的軍事工業整合到美國的體系中。這種分工合作關系在核武器領域隻有英國能夠享受,而在飛彈防禦領域則擴大到以色列、日本和挪威等國家,加深和拓展了美國與這些國家的軍事關系。除了研制項目上的分工以外,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也可以根據自身的地緣政治屬性進行飛彈防禦合作的角色分工。例如,在地區中政治地位較高的國家(如德國),可成為統整資料、資訊的戰鬥指揮中心的設立地點,其他處于關鍵地緣位置的小國則可以作為重要的雷達監控站或攔截系統的部署點。在這樣的分工體系中,美國仍然是維持延伸威懾關系的最重要的安全保證者;一些地區性強國如德國、日本雖然無法為其他盟友提供安全保證,但扮演着分攤美國負擔和協助美國的角色;像南韓這樣更鄰近于對手或敵人的國家,則更專精于“次級地區”的防務工作,以應對美國及其盟友所謂的地區性威脅;而某些實力更弱的國家或地區,雖然無法承擔太重要的防務工作,但能利用地緣位置發揮戰略價值,如保護關鍵航道,或成為某些重要的雷達站、軍事後勤設施的部署和維護地點,如波蘭、捷克和羅馬尼亞在東歐反導系統中扮演的角色。這樣的合作模式能适應不同的威脅來源,回應不同盟友和夥伴對美國延伸威懾的安全需求,降低美國在延伸威懾方面的防務負擔。
其次,飛彈防禦合作有利于強化美國對盟友和夥伴的控制力度,提升其軍事上司地位。美國是延伸威懾關系中的先進飛彈防禦系統的主要提供者,而且掌握着飛彈防禦系統的命脈——高端衛星監控能力,這讓其軍事上司地位更加鞏固,也使美國能要求盟友和夥伴配合其軍事行動,維持彼此軍事政策的一緻性。在1990—1991年的海灣戰争期間,美國首次向盟友提供飛彈防禦保護,并以此要求盟友在軍事政策上服從和配合美國。在實戰中,美國以“愛國者”反導系統攔截伊拉克攻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飛彈,安撫這兩個盟友,使它們即便在遭受伊拉克“飛毛腿”飛彈襲擊的狀況下,也不采取冒進的報複措施,以免損害美國上司的聯軍的聲譽。伊拉克在1990年8月初入侵科威特後,便開始刻意制造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沖突。薩達姆·侯賽因公開表示,以色列撤出阿拉伯領土,叙利亞撤出黎巴嫩,伊拉克才會撤出科威特。而位于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間的約旦則宣布禁止以色列的戰機飛越約旦的空域。一方面美國擔心若以色列貿然對伊拉克發動空襲,會進一步刺激阿以沖突,因而不斷要求以色列克制; 另一方面,美國也希望沙特阿拉伯在美國的指揮下參與聯合軍事行動,而不是采取單獨的軍事行動。在将“愛國者”系統和相關技術人員運抵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後,美國成功安撫了這兩個國家,使它們繼續遵照美國的指揮與規劃行事。
再次,飛彈防禦合作有利于提高盟友和夥伴的整合度。開展飛彈防禦合作,盟友之間就必須在資訊共享、雷達預警、多層次攔截等議題上加強配合,這也會增加盟友和夥伴在軍事安全議題上對彼此的依賴程度,因而能提升同盟的凝聚力。典型的案例是美國試圖以飛彈防禦合作整合東亞盟友和夥伴的做法。日本與南韓都是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重要盟友,也同樣視北韓為重要威脅,但由于複雜的曆史問題和領土糾紛,兩國長期以來卻始終無法建立密切的軍事合作關系。美國一直以來都扮演着調解日韓沖突的關鍵角色,希望兩國能與美國開展更全面的三邊安全合作關系。而飛彈防禦合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2016年1月,北韓進行了第四次核試驗。同年2月,美韓兩國就透露出“薩德入韓”的意向;6月,美日韓三國随即在夏威夷展開代号為“太平洋之龍”的飛彈防禦聯合軍演,演訓内容為三國“宙斯盾”艦針對飛彈威脅的發現、跟蹤及資訊共享能力。緊接着,2016年7月,美韓雙方達成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的共識。到了同年的11月,日本與南韓便正式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這不僅是兩國之間的第一個軍事合作協定,也為兩國後續更密切的軍事合作關系奠定了基礎。國内許多學者指出,美日韓三國以飛彈防禦合作為基礎,促進彼此建立更緊密的安全關系,是美國積極推動的結果。實作暢通無阻的情報共享,才能更有效地監控和預警地區飛彈威脅。是以,促成日韓軍事情報合作與共享也是美國建立東亞反導體系的關鍵步驟。 另外,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也會損害中韓關系,迫使南韓不得不融入美日軍事體系,在政治上更加向美日靠攏。
單純從技術上來說,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從其他管道擷取飛彈防禦系統,也能提高多層次反導效果。但是,美國對此卻極為敏感甚至反感。例如,2017年,土耳其花費25億美元向俄羅斯購置S-400系統,這個系統能夠提升土耳其的反導能力。但是,美國卻擔心此舉可能損害美國以飛彈防禦合作來整合其盟友和夥伴的目标。針對土耳其的行為,美國随即在2019年停止傳遞土耳其已付款購買的F-35戰機,還在2020年援引《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CAATSA)對土耳其進行制裁。2018年,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彼得·帕維爾(Petr Pavel)稱,擔心俄方利用在土耳其安裝S-400系統刺探北約情報;北約的飛彈防禦系統無法與S-400整合。 實際上,這些都是美國反對土耳其引進俄羅斯飛彈防禦系統的次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飛彈防禦方面的合作是美國盟友和夥伴團結互助以及服從美國上司地位的象征。如果土耳其的做法引起其他盟友和夥伴的仿效,将嚴重損害北約的團結以及美國的上司地位。此外,土耳其的做法也會破壞美國試圖通過飛彈防禦合作進一步擴大延伸威懾體系的全球戰略。如果連北約盟國都選擇采購S-400,其他并非美國正式盟友的戰略夥伴(如印度)就更可能考慮采購S-400。這也會使美國将先進飛彈防禦系統作為延伸威懾的安全保證、吸引更多安全合作夥伴的做法失去效果。
綜上所述,飛彈防禦合作能夠維持美國的延伸威懾安全保證,鞏固美國的軍事上司地位,又可以鼓勵盟友和夥伴更多地分攤負擔。這是美國基于“核壟斷”的核保護傘延伸威懾模式無法做到的。飛彈防禦合作也能增強盟友和夥伴的軍事合作及安全方面的互相依賴關系,提高它們的凝聚力。這種高度整合的延伸威懾關系以往在較正式化的多邊同盟體系如北約中才做得到。但北約在冷戰結束和東擴後,成員國之間也出現了較大的分歧。如今通過飛彈防禦合作,美國有望重整北約,并進一步整合中東和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關系。
(二)飛彈防禦合作對美國延伸威懾的負面影響
飛彈防禦合作對美國的延伸威懾政策也會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包括對盟友和夥伴來說,其可靠性較不明确;美國需要在延伸威懾政策上長期投入更高的成本。
首先,飛彈防禦系統對盟友和夥伴來說是否可靠的問題。飛彈防禦合作的延伸威懾是一種“拒止性威懾”,能夠提升美國對其盟友和夥伴的安全保證,比核保護傘的“懲罰性威懾”更能夠安撫盟友和夥伴,消除它們被抛棄的疑慮。但是,飛彈防禦合作解決的主要是延伸威懾關系中的政治問題,在盟友和夥伴面對的實際安全威脅問題上仍然存在不可靠性。第一,飛彈防禦的攔截成功率一直受到廣泛的質疑,而且對手也能夠通過各種技術上容易、成本低廉的反制措施提升飛彈的突防能力。 第二,“拒止性威懾”的作用是要讓對手相信,即使它發動了挑戰,也難以達成欲實作的目标。但是,飛彈防禦的“拒止性威懾”不一定能夠對所有對手都産生作用。例如軍事技術較先進的國家,能夠發展出多樣化的飛彈突防能力;對于擁有龐大核武庫的國家,飛彈防禦能造成的威懾效果也十分有限。針對上述這類對手,核保護傘的“懲罰性威懾”反而更能夠發揮作用,有效懾止它們的行動。
基于以上幾點可靠性問題,盡管飛彈防禦合作已逐漸成為美國延伸威懾政策中的一大重心,美國也與許多盟友和夥伴開展了深入的飛彈防禦合作,但是,這些盟友仍然非常看重美國的核保護傘延伸威懾。北約國家甚至将美國部署在歐洲地區的老舊、過時的戰術核武器視為美國提供給它們的最重要的安全保證方式。在2018年釋出的北約《布魯塞爾峰會宣言》中,北約重申2010年裡斯本峰會達成的更加重視發展自身飛彈防禦能力,以及在美國的幫助下完成“歐洲分階段适應性飛彈防禦方案”的共識,并強調飛彈防禦雖然能夠補充核武器的威懾效果,但其仍然無法取代核武器。是以,隻要核武器還存在于世,沒有被完全禁止或銷毀,北約的同盟基礎就必須以核武器為重心,其中,美國的戰略核力量仍然是北約盟友最大的安全保障。 2010年,奧巴馬政府提出讓海基核巡航飛彈退役的計劃,這引發了日本政府的不滿;特朗普執政後提出發展海基低當量核飛彈,以及核巡航飛彈重新服役的計劃,日本政府對此表示樂見其成。對許多盟友和夥伴來說,美國的戰術核武器部署是強化核保護傘延伸威懾的最重要的確定措施,仍然被認為是比飛彈防禦系統的部署更加可靠的方式。
其次,飛彈防禦合作導緻美國需要在延伸威懾政策上長期投入更高的成本。如前所述,美國可以通過與一些經濟、科技能力較強的盟友或夥伴進行分工,共同研制飛彈防禦系統,減輕美國單獨研制的成本;也可以軍售方式将飛彈防禦系統賣給盟友和夥伴,抵消部分經濟負擔。但是,相較于核保護傘,飛彈防禦的延伸威懾模式仍然會使美國付出更高的成本,基本理由有三條。第一,均攤到單個攔截器的成本遠遠高于均攤到單個核武器的成本。是以,發展同等規模的反導系統和核武器系統,前者費用會高出很多。第二,同一批次的核武器往往可以有不同的威懾對象,而地區飛彈防禦系統往往隻适用于一個地區。核保護傘延伸威懾可通過美國本身的戰略核武庫達成,隻要美國公開做出使用核武器確定盟友和夥伴安全的承諾就可以達成一定的效果,不需要投入其他成本。而目前的反導技術無法讓美國僅通過自身擁有,且部署在美國本土的飛彈防禦系統來為盟友和夥伴提供保護。很多情況下,需要在海外特定地區部署專門的反導系統才能實作地區飛彈防禦的功能。另外,在核保護傘延伸威懾中,就算要部署戰術核武器來安撫盟友,增強延伸威懾的安全保證,美國也可以規劃和調整成較為經濟的核部署形式,降低需要付出的成本,例如部署海基戰術核武器。這麼做就不需要在盟友或夥伴境内大興土木,建立核武器貯存基地,并派駐大量作戰和管理人員到當地待命了。第三,技術競争會提高飛彈防禦的費用。由于許多盟友和夥伴對飛彈防禦的可靠性有疑慮,美國就必須持續發展更先進、更有效的飛彈防禦技術,例如針對高超音速飛彈的防禦能力,才能使盟友和夥伴信服于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證。而且美國隻能更多地承擔這部分的開支,特别是在其單獨掌握的關鍵領域,如衛星監控系統的發展上,美國難以通過分工的方式讓盟友和夥伴分攤負擔。是以,冷戰後的飛彈防禦合作勢必會使美國在延伸威懾政策上付出的成本遠遠高于冷戰時期的核保護傘模式。
在飛彈防禦合作成為美國延伸威懾的重要形式後,對其延伸威懾政策産生了正面和負面兩種影響。未來飛彈防禦延伸威懾模式能否長期持續和發展的關鍵,就在于美國如何調和飛彈防禦合作對延伸威懾的正面和負面影響,以及處理這些影響可能衍生出的更多問題。美國目前正面臨兩個較為棘手的問題。首先,美國如何與盟友和夥伴分攤負擔?飛彈防禦本身價格昂貴,尤其是與進攻性飛彈相比費用很高。美國在這方面的經濟負擔很重,财政壓力很大,是以美國在各地區進行的飛彈防禦部署很難全面持續發展。雖然美國會強制盟友和夥伴分攤費用,但是,這會減少它們對飛彈防禦的興趣,不利于美國達成用飛彈防禦整合和團結盟友的目标。例如,南韓在北韓核武器與飛彈能力不斷發展的态勢下,為了緩解被美國抛棄的疑慮和恐懼,甚至願意承擔中韓關系惡化的代價,也要配合美國的東亞飛彈防禦政策,接受“薩德”系統的部署。 但是,特朗普“獅子大開口”,要求南韓全額支付部署“薩德”系統的費用,此舉引發南韓社會及輿論的不滿。其次,美國如何化解與盟友和夥伴在飛彈防禦的整合過程中産生的沖突?例如,印度和土耳其在采購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過程中遭遇太多阻礙,甚至認為俄羅斯的S-400系統的能力更強,更加可靠,因而選擇購置俄羅斯的S-400系統。但是,美國對它們這種“不合群”的行為非常不滿,還對它們發起制裁,引發了嚴重的沖突。成本問題和整合盟友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沖突,是目前美國以飛彈防禦加強延伸威懾所面對的難題。美國必須設法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維持飛彈防禦延伸威懾模式的長期發展。
五 結論
本文讨論了冷戰後美國延伸威懾模式的變化,即從主要依靠核保護傘轉變為更多地運用飛彈防禦來充實延伸威懾的内容。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核保護傘過于僵硬、敏感,美國無法運用核保護傘與一些新盟友和夥伴建立安全關系;另一方面,核保護傘對盟友的安全保證不夠具體,美國也不太可能再将境外核部署作為核保護傘的確定措施。是以,飛彈防禦合作逐漸成為美國延伸威懾的重要内容。對于像中東國家或印度這類無法通過核保護傘建立安全關系的國家,美國可通過拓展與它們在飛彈防禦領域的合作建立安全關系。在提供和強化安全保證的問題上,美國不僅能通過飛彈防禦合作,建立雙邊、多邊和地區性的多種協商機制,還能夠将飛彈防禦相關系統大量部署在各地區。這些做法都有利于提高盟友和夥伴對美國延伸威懾的信心。
美國延伸威懾模式的這一調整,對其延伸威懾政策造成了正面和負面影響。通過飛彈防禦合作,美國可以建立多種延伸威懾協商機制,并讓盟友和夥伴更多地參與其中,這不僅能讓它們分攤軍備研制和防務上的負擔,也能強化延伸威懾的可信度。此外,飛彈防禦合作還能增強美國對盟友的指揮控制,有利于促進盟友之間的團結與整合,進一步鞏固美國的軍事和政治上司地位。然而,飛彈防禦的可靠性仍然面臨諸多質疑,許多盟友将美國的核保護傘以及戰術核武器部署看得更重要。而且飛彈防禦合作的延伸威懾模式也使美國在境外部署和技術提升上必須付出更多的成本。是以,如何調和飛彈防禦合作的優點和缺點,将會是美國延伸威懾政策未來面臨的一大難題。
【來稿日期:2021-03-31】
【修回日期:2021-06-22】
【責任編輯:李水生】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衆号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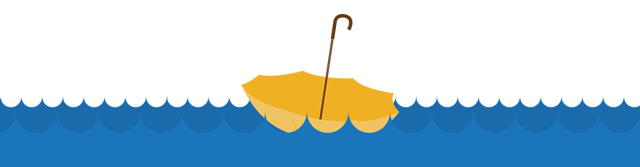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