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八一評論微信公衆号 作者:鐵坑
蜀漢時,何随著《譚言》十篇,專論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豬從何随家門口經過,豬索斷,失之。屠者強認何随家養的豬,何随便牽來送給他。何随家有片竹園,有人潛入盜筍,惟恐驚了偷盜者,他避身竹林。不料,竟傷了腳,最後拿着鞋一瘸一拐地回來。
“吾以是謂之會說也,以其太說得好,實難到也。”對于何随這類人,明代李贽稱其為“會說者”:但要說得好,不管行得行不得;既行不得,則謂之巧言亦可。從李贽給出的定義看,“會說”是一個貶義詞,徒求好聽、言行脫節。
現實中,會說的确吃香。言者伶牙俐齒、妙語連連,聞者如沐春風、正中下懷,此種表達很是吃得開。捧人捧得很到位,罵人罵得頗含蓄,自誇誇得像自謙……在很多人看來,這是技巧更是水準。天花亂墜之時,“你滿意,我得意”“你内心舒暢,我辦事順暢”。有人憑借此邀寵得勢,有人雖羨慕卻總學不來,當然也有人骨子裡就不願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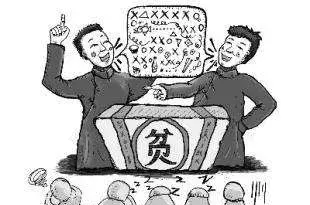
清代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中,記錄了一段對話。嘉慶皇帝問四川總督勒保:“爾等為督撫,僚屬中何等人最便宜?”勒保對曰:“能說話者。”嘉慶皇帝說:“然。工于應對,則能者益見其善;即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雖事後覺察,而目前已為所蒙矣。況政事不藉敷奏不能暢達,往往有極好之事,為拙于詞令者說壞。”這裡将“工于應對”與“拙于詞令”的兩種人放在一處對比,論理更顯透徹。
“居官以能說話得便宜”,陳其元有過切身體會。同治丁卯,他主政南彙縣時,曾處理過“掩埋暴露”事。曆時3個月,南彙縣共勸葬或代葬4萬餘棺,然尚有1萬餘具或因子孫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盡葬,須待來年再辦,陳其元據實上報。另有一縣,僅掩埋1700餘棺,卻以境内悉數葬盡具報。結果,陳其元以“尚有一萬餘棺未葬”被申饬,另一縣則因“辦理認真”被記以大功。在上級面前雖然吃了虧,但陳其元并不後悔,他依然堅信“公事不可作欺飾之語”。
巧言令色,鮮矣仁。檢閱曆史,巧舌如簧的佞人并不少見。桓玄篡位登基時禦床下陷,這是極為不祥的兇兆,殷仲文卻說:“陛下聖德深厚,大地也承載不了。”桓玄兵敗勢去後,這位讓主上轉怒為喜并大獲封賞的人,卻很快逃之夭夭。唐玄宗曾問安祿山:“腹中有何物,為何那麼大?”安回答:“沒有别的,隻有赤誠之心。”可後來起兵攻潼關、逼長安,使大唐王朝急轉直下的正是此人。
口口聲聲腹中一顆“赤誠之心”的安祿山,最終叛亂。
殷仲文和安祿山,他們的能說會道或是權力的“敲門磚”,或是禍心的“僞裝服”,背後深藏着私心和欲望。對這些“會說者”缺乏警醒,很有可能使自己成為脹破的氣球,甚至使苦心經營的事業走向危亡邊緣。這樣的教訓難道還少嗎?
“會說者”的心态與得意,錢鐘書描寫得惟妙惟肖。《魔鬼夜訪錢鐘書先生》中,魔鬼說:“我會對科學家談發明,對曆史家談考古,對政治家談國際情勢,展覽會上講藝術賞鑒,酒席上講烹調。不但這樣,有時我偏要對科學家講政治,對考古家論文藝,因為反正他們不懂甚麼,樂得讓他們拾點牙慧……這樣混了幾萬年,在人世間也稍微有點名氣。但丁贊我善于思辨,歌德說我見多識廣。”可實際上呢,鬼話連篇掩飾“殘疾”的魔鬼,是做靈魂生意的。
古人說:“一言之辯,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雄師。”毋庸諱言,能言說、善表達是一種必要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實學實行實說。無論立身處世還是察人觀物,都應如此。隻有具備了“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的自覺,擁有了“谄谀我者,吾賊也”的清醒,踏實做人、務實幹事,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幹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