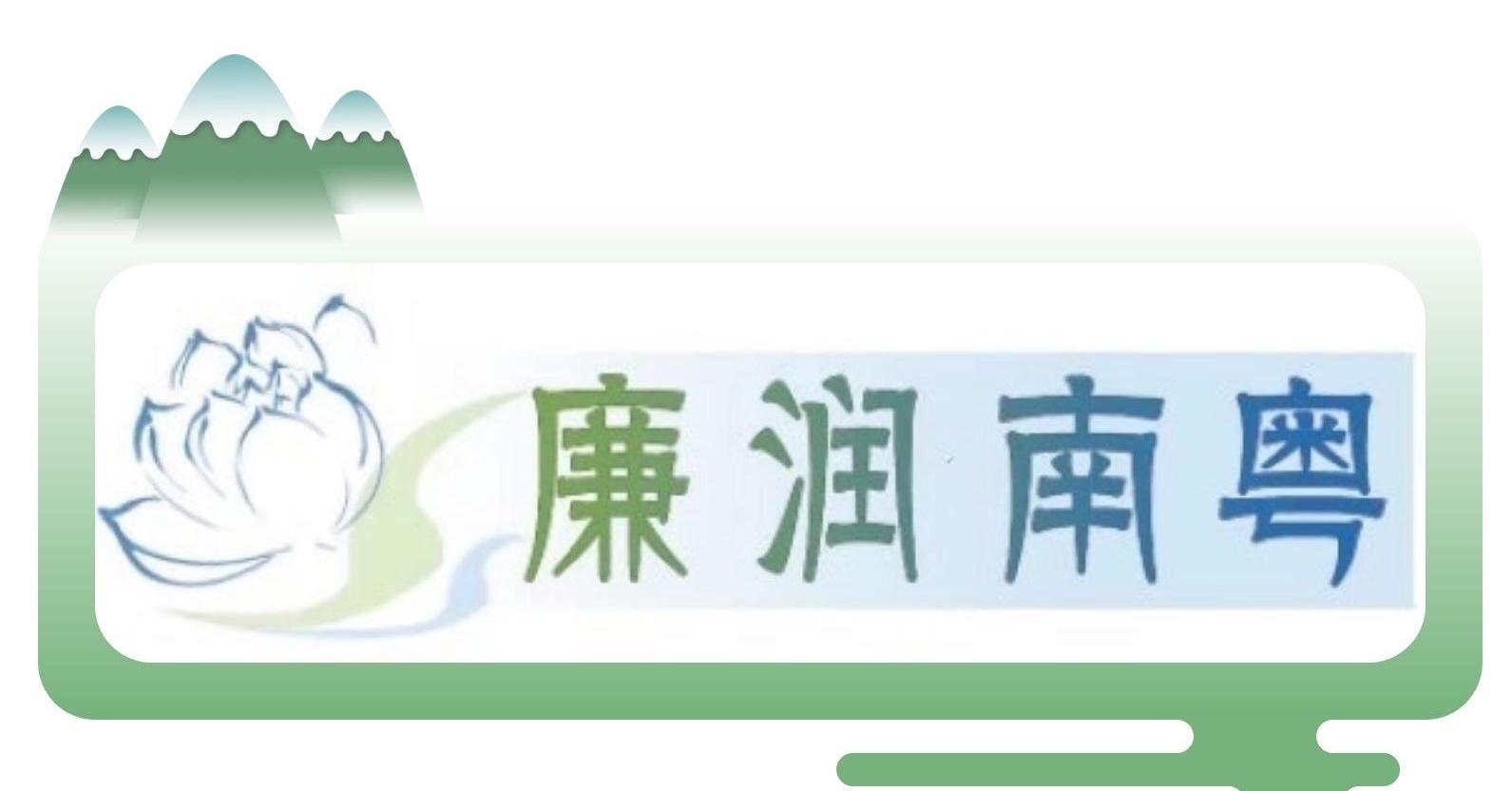
文/郭珊
《楚辭·漁父》曾借屈原與漁父的一段對話,提出這樣一個靈魂拷問:在一個“世人皆濁”的年代,是見機行事、随波逐流,還是保持正直清白,絕不同流合污?
如果說東漢的楊孚正直勤政,是因為他有幸遇到了明君治世,那麼在大約300年之後分裂動蕩的東晉末年,卻有這樣一個人,面對一口據說飲後必生貪念的“貪泉”,敢于犯險試酌,用一生的克勤克儉、清恪自守,證明貪欲生于人心,而不在于環境,為後世為官者作出了表率。
“古人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這就是被《晉書》推為“晉代第一良吏”的吳隐之所作著名的“貪泉詩”。
吳隐之飲“貪泉”的典故,曾被王維、李白、白居易、錢起、蘇轼等人的詩文廣泛引用,更因王勃《滕王閣序》中的名句“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而譽滿天下。這段曆史就發生在距離廣州市區西北約20公裡處的石井鎮石門村,“貪泉”原址立有石碑以示紀念。
其實,吳隐之身處的東晉官場,對人性的考驗遠甚于“貪泉”。戰亂頻繁,生靈塗炭,權貴當道,貪腐成風……誠如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所言,漢末魏晉六朝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也是“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當同時期的許多讀書人對現實深感失望,轉而談玄論虛的時候,吳隐之的故事愈發令人深思。
身居高位 清儉如舊
一介布衣,生于貧寒之家,既無祖蔭,又無資産,卻得名流舉薦,又獲權臣賞識,在公卿乃至皇室的連番提拔之下,一路平步青雲,直至官居大位……
觀其一生,吳隐之的仕途順暢到不可思議。特别是在晉代,門第觀念根深蒂固,選官制度成為世家子弟晉升的“快速通道”,以緻“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吳隐之的際遇堪稱是一出平民逆襲的傳奇。
吳隐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生年不詳。祖上曾是與司馬懿、陳群、朱铄并稱曹丕“四友”之一的吳質,因輔佐曹丕稱帝有功,得以封侯,子孫也都做過官。
到了吳隐之這一代,家道中落。《晉書•吳隐之傳》說他“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弱冠之年就品行出衆,就算窮到每日以豆粥果腹,也不取不義之财。
吳隐之在成為清官之前,首先是一個孝子。他早年喪父,侍奉母親很是用心。母親去世時,隐之和胞兄坦之悲痛欲絕。傳說兩人恸哭之聲感動了天地,引得雙鶴鳴叫,盤旋不去。
《晉書》對吳隐之出仕經過的記載,很有幾分戲劇色彩:玄學家韓伯母子與隐之為鄰。韓母聞其哭聲,難過到食不下咽,便對兒子說,如果你将來做了掌管人事任用權的大官,就該舉薦像吳隐之這樣的人。不料竟一語成真,韓伯果然累遷至吏部尚書,在他的力薦之下,吳隐之從一個地方基層文員——功曹開始,踏上了從政之路。
東晉自南渡以來,王室孱弱大權旁落,觊觎帝位的各股勢力蠢蠢欲動,叛亂四起。以前秦為首的北方諸國虎視眈眈,後期又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内憂外患使得朝中形勢複雜難測,時常“城頭變幻大王旗”。
然而,吳隐之在東晉晚期數十年的為官生涯中,卻仿佛超然于外,屢受褒賞,曆任奉朝請、尚書郎、禦史中丞、左衛将軍、中書侍郎等要職。
不僅如此,晉孝武帝司馬曜,大司馬桓溫,淝水之戰晉軍大都督謝石,以及北府軍将領劉裕等人都對他頗為器重。這些皆是當時處于權力鬥争巅峰的關鍵角色,谯國桓氏與陳郡謝氏兩大家族互為死敵,而劉裕曾率兵讨伐桓溫之子桓玄謀反篡位,自己卻又成了終結東晉江山的“南朝第一帝”。
吳隐之能夾在各派朋黨的利益攘奪之中免受沖擊,受到多方禮遇,原因還是在于他令名遠播。任晉陵太守時,他仍和顯達之前一樣布衣蔬食,負柴之類家務仍由妻子操持,把俸祿賞賜都分給親族,使得家無餘财,冬月無被,洗衣時沒有多餘的衣物替換,隻得披棉絮取暖,“勤苦同于貧庶”。
隆安年間(397-401),吳隐之出任廣州刺史,“清操逾厲”,常食不過蔬菜及幹魚,官方配備的帷帳、器具、衣服一律棄而不用、交到庫房。
随後,他還升任度支尚書、太常等職。從掌管一郡(市)、一州(省)到一國财政稅收,他始終厲行儉樸,每月饷銀仍舊隻留基本用度,其餘用來救濟他人。家人紡織度日,妻子兒女不沾寸祿,遇到困難時期,甚至吃不上飽飯,身上穿的衣衫破舊不堪。
吳隐之的立身處世,與曆史上那些來自底層、一旦大權在握便極盡搜刮的貪官形成了鮮明對比。例如《長安十二時辰》中庶民出身、依靠攀附鑽營上位的反派官員元載,曆史上就确有其人。
嶺南垂範 革除舊弊
吳隐之砥砺清節的作風,也曾惹來“做作”的非議。因其所處時代的社會風氣,從中央到地方都與“清廉”二字格格不入。
曆代史書以及《世說新語》《抱樸子》等文學作品中關于晉代王公貴族昏聩、荒淫、殘暴、奢靡的種種記載不勝枚舉,例如晉武帝為了選妃禁止天下婚嫁,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石崇與王恺炫奇比富等。西晉第二位皇帝即位時,已是“盤剝百姓,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晉書•惠帝紀》)
到了東晉,門閥世族氣焰熏天,大肆兼并土地,A錢受賄,以窮奢極欲為榮。吳隐之昔日的上司謝石就是一例。謝石出身名門,戰功彪炳,卻又“聚斂無餍,取譏當世”。太學博士範弘之曾批評他貪掠财物,大興土木,生活奢靡,不惜财力,實為“人臣之大害”。(《晉書•儒林列傳》)
有意思的是,謝石曾主動請吳隐之任其主簿。身為将軍的秘書,吳隐之嫁女的時候,竟然為了籌措嫁資,要臨時遣仆人上街賣狗,“此外蕭然無辦”。謝石對他多有照拂,知其清貧,還專門派人替他置辦婚宴。兩人一為巨貪,一為良吏,這段關系頗為耐人回味。
像謝石這樣的晉代官僚階層之是以敬重廉吏,是因為他們深知吏治廉明的重要。曹魏時期出現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監察法規《六條察吏》。在此基礎上,西晉又出台了《察長吏八條》和《五條律察郡》,分别明确了對進階官員(長吏)和郡縣政績民生的監察範疇。
在有成法可參照的情況下,東晉朝廷忌憚大規模的反腐整治會動搖統治根基,失去豪門望族的支援,故而一方面采取“鎮之以靜,不為察察之政”的暧昧态度,姑息放任,甚至沆瀣一氣;另一方面,又把期望寄托在吳隐之這樣的賢能身上,派他南下廣州,“革除舊弊”。
那時,嶺南路途遙遠,瘴疫流行,卻是自漢代以來的水陸貨運樞紐,山海珍異輻辏,是世人豔羨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庫”(屈大均《廣東新語》),加上天高皇帝遠,疏于監管,極易滋生腐敗。《南齊書•王琨傳》有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緻巨富,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而石門處于廣州西北水路要沖,為履新必經之地,“一飲貪泉、廉士必貪”的說法便由此而來。
為避免重蹈前任官員覆轍,吳隐之特意在上任途中拜訪“貪泉”,當衆飲水賦詩破除流言。就任後他不辱使命,大力懲治貪财納賄行為。有部下為了示好,給他送魚時去除魚刺,吳隐之非常厭惡,将之喝斥趕出帳外。
經過他的努力,嶺南風紀大為改觀。晉安帝司馬德宗下诏表彰他:“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革奢務啬,南域改觀。”(《晉書•吳隐之傳》)
廉慎傳家 影響深遠
離任之前,孫恩盧循上司的農民起義戰火波及廣州,吳隐之及家眷一度被盧循俘虜。危急關頭,幸得劉裕出面調停,才得以獲救。
歸舟之日,吳隐之行李單薄,“裝無餘資”。今天,廣州市石井鎮“貪泉”附近、流溪河下遊有一個小島。傳說吳隐之在船上清點随行物品,發現妻子帶了一斤沉香,因懷疑來路不明,遂丢到水裡。沉香一入河中,頓時化為沙洲,故而得名“沉香沙”,又名“沉香浦”。
返鄉後,吳家僅數畝小宅,茅屋六間,以竹籬為院牆,都很簡陋。劉裕賜給吳隐之車子、牲畜,為他起宅,都被他謝絕了。
義熙八年(412年),吳隐之正式退休,被授予光祿大夫,次年辭世。他多次獲得朝廷的優賜嘉獎,天下廉士以之為榮。
當初,吳隐之的先祖吳質同樣出身寒微,才學通博,卻因為仗着曹丕恩寵“怙威肆行”,卒後被谥為“醜侯”,還是靠着兒子堅持不懈上書二十餘載才獲得平反。吳隐之是否受此影響不得而知,或許對他來說,隻有“廉慎”二字,才是茫茫宦海唯一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去世以後,這兩個字成為吳氏後人的家規,他的子孫在為人“孝悌潔敬”方面代代相傳。
吳隐之的事迹對嶺南官場影響深遠。宋代淳熙初年,福建泉州人李維、李綸兄弟同赴廣東為官,曾在石門江邊舉杯起誓:“倘負軍民,有如此水!”說完将杯子投入江流,竟然不沉。兩人亦兌現承諾,廣施廉政,受到百姓擁戴。有人編了這樣一首民歌以示贊頌:“石門之水清且清,晉吏一歃千古榮。争如李公投杯盟,水流洶洶杯停停。”(參見《四庫全書•廣東通志卷三十九》)
事實上,在吳隐之之前,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中國曆史上也曾湧現出毛玠、崔琰、胡質、胡威、傅玄、陶侃等一幹以忠廉直亮著稱的名士。特别是陶侃在任廣州刺史期間,整肅秩序,執法廉明,還留下了一段“搬磚自勵”的佳話,可見并非人人皆會“越嶺喪清”。
另據宋方信孺《南海百詠》所載,五代十國時割據廣州地區的南漢統治者因不喜“貪泉”之名,派人運石填埋,“貪泉”從此不存。而到了清初,到廣東做官仍被視為一樁“油水豐厚”的美差,大小官員一旦接到赴粵調令,“靡不歡欣過望”,“以為十郡膻境,可以屬餍脂膏”。(屈大均《廣東新語》)
“貪泉”的存沒與嶺南古代官場的關系足以證明,吳隐之對“廉”的見解是十分精辟的——一個人是否廉潔,歸根到底在于内心信念是否堅定。他曾告誡身邊人“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保持心境澄明,故而處濁流亦能自清;反之,若因貪念動搖了心志,進而利用職權徇私漁利,卻歸咎于外部因素的誘惑和誤導,不過是推卸責任、自欺欺人罷了。吳隐之在1000多年前尚且明白這個道理,今人更應引以為戒。
評說吳隐之
文/潮白
吳隐之飲貪泉水而言志的故事,大抵世人皆知。他也許是最早對貪泉“功能”證否的官員,是以房玄齡等撰寫的《晉書》贊曰:“吳隐之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為最。”
位于廣州石門的貪泉,不僅名字不那麼好聽,而且“相傳飲此水者,即廉士亦貪”,還有能夠使好人變壞的“實用功能”。泉水能使人“易心為墨”,十足令人驚詫莫名。然廣州刺史吳隐之上任之際,專門去貪泉“酌而飲之”。結果呢?為官卻是“清操逾厲”,踐行了自己“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的承諾。用晉安帝的話說,叫做“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而當初派他前來,正是“欲革嶺南之弊”。之後,唐朝廣州都督馮立也是這樣。面對貪泉,他說:“飲一杯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杯耶,安能易吾性乎!”說罷“畢飲而去”。在職數年,馮立也是“甚有惠政”。
清代學者屈大均是廣東人,他對家鄉的泉水負“貪”之惡名十分不服。他指出,如果貪泉“飲之辄使人貪”,東莞還有廉泉,“未聞有飲之而廉者也”,怎麼就沒有喝了變得廉潔的呢?為什麼同樣是泉水,“廉者不能使人廉,貪者乃獨使人貪?其人累泉乎?泉累人乎?”
屈大均之問,何其振聾發聩!“泉之見罪,非有吳刺史不能釋”。的确,從吳隐之為貪泉平反開始,後之仍持“易心為墨”論調者,暴露的隻是其流氓性的一面。
【作者】 郭珊
【來源】 廉潤南粵南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