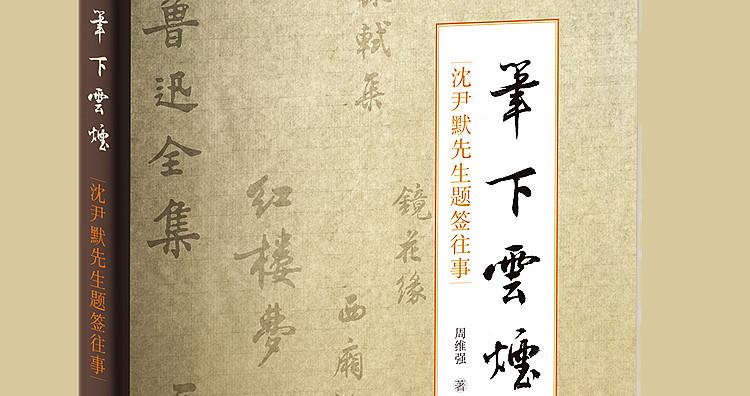
大約在兩年之前,我收到周維強先生的微信,他引了一段張宗祥先生1960年寫給在香港的侄子金申祿的信:
“尹默極好友。我字與彼,彼用功,我天資高,各有長處。彼既一幀售50元,我亦不可過高,至多高二成。畫可随便定,但亦不能過老友黃賓虹,照黃賓虹例,或減二成可也。”
接着他提出了兩個角度頗為特别的問題:“張宗祥先生提到的售價是港币還是人民币?書畫售賣行為是發生在香港還是内地?”這段材料資訊量很大,我一下子來了興緻,在私人通信的場合,張宗祥先生對沈尹默和黃賓虹的評價、對自我的定位耐人尋味。
60多年過去了,張宗祥、沈尹默、黃賓虹都已進入了被經典化的曆史序列,這番評論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依然值得細細審視。順着周維強先生這兩個問題想開去:張宗祥1960年尚有訂潤格的做法,那些在民國時期依靠藝術市場售賣作品為生的藝術家們,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生活情形如何?又去翻閱了王中秀先生主編的《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一書,雖然沒有找到能夠直接回答關于“币種”問題的答案,但由此對潤格相關的史料也開始留意起來。
後來才得知周維強先生在寫與沈尹默有關的“小文章”。那段時間常在朋友圈“看見”他在西溪濕地散步時拍下的風景照片,感到有一種沉思的情緒和氛圍,這是處在寫作中的人所熟悉的狀态。他似乎也很喜歡拍各種各樣的雲,不僅有編号,還标明拍攝時間,很有意思。到今年6月份時,收到他出版的新書《筆下雲煙:沈尹默先生題簽往事》(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1年版),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口中的“小文章”竟然是一本書!
《筆下雲煙:沈尹默先生題簽往事》,周維強著,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沈尹默在新中國成立後,做了大量的書法普及工作,為圖書題簽也是這些普及工作的内容之一。
他在《書法的今天和明天》一文中講過:
“書法本來不僅僅用在條屏、對聯、冊頁、扇面上的,就是廣告商标、路牌、肆招、智語、題簽、題畫之類,也需要有美麗的書法,引起一定的宣傳作用。我曆年來為書籍圖檔出版社以及日用商品店、出口物資公司等處題了不少字,前年天津中國制藥廠,要我替他們寫二十多種膏丹丸散名稱的包裝紙,據說以此來包藥,與銷路也有關系,這也是社會上需要書法的一個絕好的執行個體。”
對于當時社會上出現的為書法的命運擔憂的聲音,他一方面通過撰寫文章闡明書法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則身體力行,讓自己的書法為滿足大衆的生活和審美的需要而服務。
沈尹默對書法的時代定位除了考慮書體變遷的曆史規律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20世紀50年代,為掃除全國占比80%以上的文盲,由吳玉章牽頭的中國文字改革協會開始着手制定文字改革方案,推行台灣字。自改革伊始一直到現在,有關繁體字與簡體字之間的争論就一直沒有停息過。沈尹默作為彼時書壇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看法和态度很關鍵。
1963年底,沈尹默發表《書法藝術的時代精神》。該文認為,書法發展的規律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要結合實用,是以書法藝術家沒有理由反對台灣字,而要拍手歡迎它,這不僅符合時代的需要,也是書法藝術界取得“突破”的大好時機。在書法形體的處理上要追求“端莊、大方、生動、健康的美,而不能追求怪異。”這實際上就為這一時期的書法提出了一個如何為大衆服務的美學标準,也為個體書寫如何與新時代互動提供了一個樣本。也正因為他把題簽定位為書法普及的工作,為滿足各個行業的需求而書寫題簽對他而言就成為一項十分嚴肅的工作。這一時期題簽的數量很多,我們可以在周維強先生書中列舉的題簽材料當中看到這一點。在題簽時,他的書寫狀态在情緒準備上是飽滿的,積極的,思想上的準備也是非常充分的。是以這些題簽恐怕不能簡單地歸為應時之作,或者定位為隻是為服務宣傳和美化而展開的書寫,而應視為沈尹默晚年書寫觀念和書風探索的重要書法作品。
然而,題簽确實是一種在形制上較為特殊的書法形态。題簽由起分類、标記作用的标簽演化而來。随着書籍、書畫集結成冊,标簽逐漸演化為書籍、書畫裝潢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實用的功能之外又增藝術性的考量,在簽條上題寫的文字也逐漸講究起來。到明清時代,題簽的形态已極為豐富,其文化藝術功能亦在這塊小小方寸之地上展現到了極緻。題簽文字不僅可作為獨立的藝術形式來欣賞,亦可作為書畫流轉過程、文人交遊往來之見證。而在特殊的曆史時期,亦能見證社會文化審美慣習的變遷,傳達某些特殊的政治意涵。當然,也隻有某些特定的題簽會見證特定的曆史時刻。是以,題簽行為本身就不僅僅隻是簡單的書寫行為,題簽亦不可僅僅從書法的層面來了解。一方小小的題簽,不僅能夠見證書法家的藝術創造能力,同樣也能見證曆史。如果不回到曆史現場,何以能夠釋放那些特殊的曆史時刻?
周維強先生以題簽背後的“往事”切入,不能不說在選題上獨具心眼。全書25則随筆,以題簽為生發點勾連出沈尹默先生的人生經曆、人品、詩文、書風、交遊等,看似信筆寫出,但前後映帶緊密,顯現出作者剪裁史料的匠心,一個完整的沈尹默的剪影呈現出來。
就我的了解所及,本書應該是國内第一本專門彙集并讨論沈尹默題簽的著作。其中使用的材料不僅包含已經公開出版的題簽,還包括部分未被出版社“選中”、因而未能進入大衆視野的題簽。無論是對于書法愛好者還是專業的書法研究者,乃至關注沈尹默的一般讀者來說,這些題簽無疑都是具有研究和欣賞價值的新材料。
作者對史料非常敏感,常有獨得之見。比如沈尹默為出版社寫題簽所收稿酬之材料,鋪陳相當精彩,讀者自可循章閱讀。而其中一則材料之使用尤能看出作者解讀史料的特點,于一般人不注意之處多有申發,即注意到沈尹默信劄所用稿紙之細節,由此不僅可觀他與馬廉交往之密切,更可觀察他對題簽之鄭重态度。
書中亦有閑筆,于文獻之難以實證處,以心證通之。比如作者提到:
“沈尹默先生後來确實很少撰著古典文學論文了。那麼,他在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古典文學作品題寫書名的同時,會不會也借此在心底裡重溫着這些作品的意味呢?他在寫書名時會不會也在沉潛涵泳着這些古典的精華呢?”
如果稍稍了解沈尹默先生治學和人生經曆,讀到這裡恐怕都有會心之感。沈尹默早年在北大講授文史課程,亦以舊詩詞名家,作為詩人的沈尹默在題寫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轼諸人之詩集時,所思所感恐怕是不能平靜的。尤其是他還深受目力衰微之苦,不能多閱讀書報,晚年更甚。作者的發問為我們體會和了解沈尹默題簽時的書寫狀态留下了想象的空間。盡管沈尹默在書法上的名聲遠遠蓋過其詩名,但,作為書法家的沈尹默與作為文學家的沈尹默何嘗分裂過呢?當然不能割裂來看。書中有很多類似的閑筆,有含蓄蘊藉之緻,在我看來都是作者引而未發的部分,也是感到意猶未盡的部分。
沈尹默曾自述其平生笃信米芾“惜無索靖真迹,觀其下筆處”,尤其是“下筆”極為關鍵,乃是書家“金針度與”之處。學術随筆、學術掌故類寫作同樣也是如此,下筆發端處極為可觀,立意高下亦從此處分殊。本書固然有題簽書法欣賞,而更着重在題簽背後的曆史掌故。全書取材卻頗為“平淡”,無一般寫掌故之獵奇手筆,亦不販賣所謂“秘辛”,寫法上以随筆出之,雖有旁逸斜出之枝,然下判斷處落筆謹慎,小心求證。比如關于潤格問題,對高羅佩《巴江錄别詩書畫冊》、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等題簽的辨析,把尚有讨論空間的學術問題擺在了讀者面前,這恐怕是進一步研究沈尹默題簽書法很難繞過的問題。
有考證、有發問、亦有感懷,再加上作者精心選擇的史料,本書的寫作兼具學術與随筆寫作的特點。作者手裡拿着一塊瓦片,投擲出去,擊打出無數的水花。沈尹默的文化形象和個人形象在這些四濺的水花當中變得生動起來。
今年是沈尹默先生去世50周年,我手頭正好收有一本鐘明善先生六年前(2015)年編著的《小題“大做”:于右任題簽書法欣賞》,也是為紀念于右任先生去世50周年所作。“南沈北于”,兩座高峰,兩條書學道路,在被曆史化的道路上重新“相遇”,将兩本題簽對觀,竟似生出見證兩位老友重逢的幻覺。
本文作者系文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副研究員
作者:唐衛萍
編輯:薛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