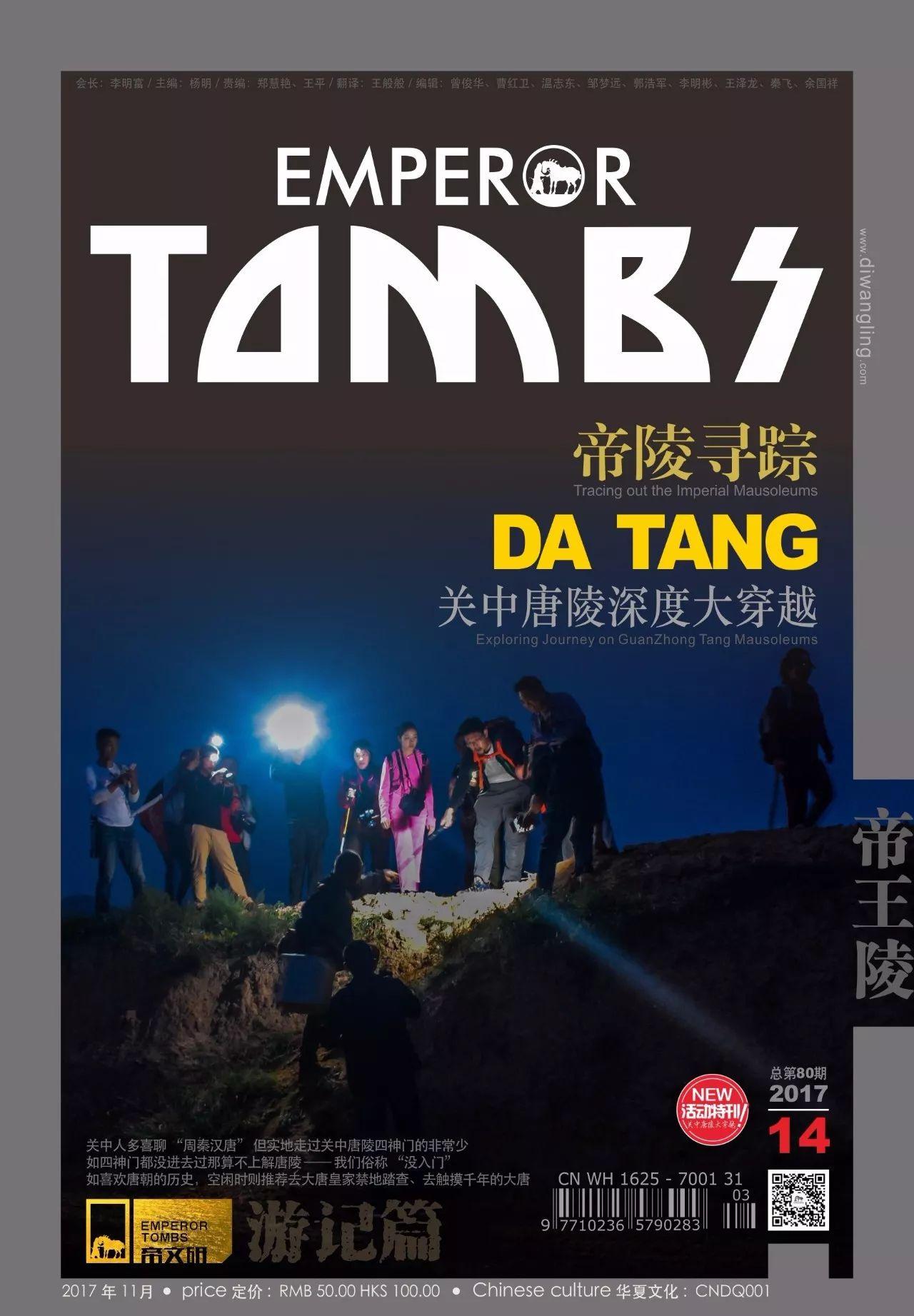
離開定陵,我們取道東邊的狹窄小路。
在村道上,對面突然駛來的大奔堵住了去路。
關中的民風彪悍,溝通無果後,師傅隻好從坡頂倒車讓道…
等待多時,我們才拐到大路,然前面又有限寬的遮擋物…
好在師傅經驗豐富,判斷準确,很牛地就駛了過去~
雨後的天氣清爽,轉到大路的時候我才留意剛剛的來路和狹窄下坡小道上竟是風景宜人。
可惜來不及捕捉清楚這一閃而過的美景,發現時來路已經很遠了。
路上,大家讨論起谥号,廟号一類的問題。邱小弟給我們普及了一下,唐以前的谥号短,是以帝王都按谥号叫,唐開始谥号變長了就改用了廟号,到清朝因為年号不變,是以按年号叫。
在楊家窖附近下了車,我們跟着隊伍穿過村莊,田野。
一個守候在柿子樹下的石人就這樣不經意間闖入了視野~
原來這裡是天乳山之陽,唐文宗李昂的章陵南門。
唐文宗李昂,是唐穆宗李恒次子、唐敬宗李湛之弟,唐武宗李炎之兄,在兄長死後,他被宦臣推上了帝位。
趕上牛李之争和宦官之亂的他運氣實在是不好,雖然他恭儉儒雅,以治易亂,代危為安,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操之過急,識人不清,用人有誤,最終将未來斷送。
《舊唐書》載:“開成五年春正月辛巳,上崩于大明宮之太和殿,壽享三十三。群臣谥曰元聖昭獻皇帝,廟号文宗。其年八月十七日,葬于章陵。”
或許曆史也有眷戀和恻隐,是以在他的葬地塑造出這樣一棵樹的巧合…
太和九年,在一方仗舍中也有一棵果樹,秋日裡會結出碩大的石榴。
文宗與自己的信臣已經商量好了一切,于是信臣依計上奏石榴樹上有甘露好引内官前往核查,借機消滅宦黨。
然而,事情卻與這位至尊所想天差地别。
最終,他被宦臣遽進宮院。
那本可成就他理想的甘露,反倒将他困入囹圄,令他抑郁而終。
時光流轉千年,如今,在他的冢茔,在這野村的田間,同樣有棵綴滿果實的樹,在這季節,紅柿已經壓彎了枝頭。
昨日天降甘露,将它洗禮一番,它便好像煥發了神采,彷如當年那場宮變正在如期進行。
遠遠望去,這樹像一把保護傘,努力撐着枝條,在這裡陪伴着文宗的冢茔度過歲月寒暑,遮擋雨雪風雷。
若當初宦臣沒有發現藏在附近的伏兵,沒有挾持到文宗,或許文宗的結局不至于如此凄涼吧…
土地松軟,我們努力找着幹硬之處挪近,但還是免不了一步一陷。
盡管如此,我還是忍不住想走近石人,坐在樹下,靠着它小憩。
大部隊已經開始前進,我有些不舍于這柿下守候的石人…
總覺得它有太多的遺憾要與我們訴說…
沿着鄉間小路而行,周圍皆是野田之景,遠處的天乳山便是文宗的葬處。
正不知為何行到了一處斷崖,幫主便給我們指了下下方一棵小樹苗的位置。
樹苗下隐隐藏有一塊石闆。
原來,那裡曾經是章陵的石獅子,如今被倒置埋進了土裡,隻有底座能從高處望見。
好在田裡現在并沒有種植什麼,不然恐怕就真的很難發現它了…
據說章陵的石刻在文 革中毀壞嚴重,如今所存也甚少,是以我們的章陵之行便從此處折返了…
但僅僅是剛剛的石人,便讓我記住了這位皇帝,這座帝陵,也會有還想來此的沖動。
回去的路上,幫主親自上樹為大家摘起了野柿子。
不同的品種,相同的甜膩,遙敬這位留有遺憾的帝王。
道路依舊泥濘不堪,但終歸還要走下去。
再回頭,已經尋不到石人的蹤影,唯見那天乳山仍如千年來一樣趴伏在田間。
為了記下來路,加之被村裡的小狗吸引,我和果果又拉了隊,卻不想大家從前面折傳回來。
不想村中還藏有一個石馬,隻是上面的雕刻已經模糊了。
短暫的章陵之行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便是樹下執着守候着的石人,是以回來去油畫體驗的時候把這幅畫畫了出來,希望這份景色能永遠存在在野村裡,供後世欣賞~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
長按二維碼關注更多
美即分享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遊集,亦或密迩而不接。
如喜走陵訪古 歡迎加入我們
入微信群(聯系微信号:huafu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