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宋高宗诏以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为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数路并举北伐。各路与金人战皆捷,尤以岳飞所部为甚,进至距故都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史称:“”。这就是著名的“直捣黄龙”的由来。然至闰六月,局势骤变,因秦桧正主议和,为孤立、逼迫岳飞班师,遂先命各路回军,然后命岳飞班师。《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岳飞班师后被收兵权,任为枢密副使,不久入狱。绍兴十一年十一月,“绍兴议和”成,宋、金以淮河中流为界,从此中原彻底属于金国。十二月,即以“莫须有”之名赐岳飞死于大理寺,遽成千古奇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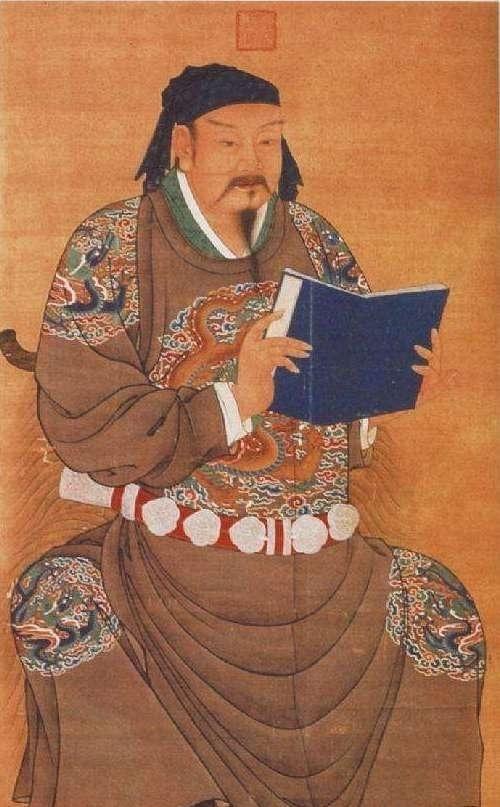
高宗杀岳飞固然有很多私底原因:比如迎钦宗的问题;比如岳飞不甘愿交兵权;比如岳飞置喙立储之事;比如岳飞公开称颂还未被立为储君的孝宗是中兴之望。这些都触了高宗的大忌,可以说岳飞是一个优秀的职业军人,却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但杀岳飞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岳飞已经成了高宗所做战略选择的主要障碍。高宗做的这个战略选择是:放弃恢复中原,经营现存的半壁江山。也就是备受后人诟病的“偏安”政策。但是,千载之下,我们站在客观的地缘政治角度看,他的这个战略选择未必没有道理。
当是时,宋可做的地缘战略选择无外乎有三个:(一)恢复中原,也就是恢复北宋的疆域;(二)直捣黄龙,也就是灭亡金国;(三)经营半壁,也就是维持现状。这里面持第(一)与第(二)种选择意愿的在高宗朝称为“主战派”;持第(三)种意愿的称为“主和派”。“主战派”的代表是:张浚、赵鼎、岳飞,两相一将;“主和派”的代表当然是秦桧,也许还有后台老板高宗本人。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主和派”的阵容会更为强大:“主战派”里面的第(一)种实际也是“主和派”,只不过他们主张的“和”,不是在绍兴十一年,而是在恢复中原之后。《宋史·高宗本纪》:“”。张浚是高宗早期最为倚重的相臣,此人军事能力不够,数次为帅基本都是败绩,但政治魄力以及抗金决心很大,是著名的“鹰派”,绍兴议和后被贬到了福建和湖南。但就是这位主战派首领的张浚,在他做宰相时一样对通使金国没有异议,并称:“后将辟地复土,终归于和”。就是说,这一派“主战派”的战略目标只是恢复北宋的疆域,之后就应该与金和好,各守其土。也就是说,他们是未来的“主和派”。岳飞如果真的恢复了中原,马上就会从这一派的政治盟友转为政治敌人。因此,高喊“直捣黄龙”的岳飞在政治上确实是个“孤臣”,其被政治清算应该是一个宿命。
当岳飞诸军在河南大捷时,朝廷实际就马上面临了一个悖论般的局面,似乎再往前打到哪里,都意味着一种危险:第一,如果按张浚一派的意愿,完全恢复北宋疆域,那么那个“天残”局依然存在,宋还要在地缘险境中继续生存;第二,如果按岳飞的意愿去“直捣黄龙”,那首先就面临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军事课题,能否做到恐怕谁都没底。“雍熙北伐”的噩梦,应该像基因一样存在大宋皇帝的身体里。绍兴九年宋、金议归河南地时,岳飞曾有“唾手燕云”的豪语(《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但谁又能保证岳飞不是曹彬。曹彬的军事成就曾比岳飞要辉煌得多,而北宋开国时的那批名将,也比绍兴年间这批“中兴大将”的军事素养要高得多。如此看,就怕“直捣黄龙”未果而重蹈雍熙覆辙,到时候怕是宋朝要直接灭亡了。
因此,岳飞的“直捣黄龙”是高宗绝不会选择的。那么,恢复到靖康以前的地缘形势又如何呢?很显然,金人依然居高临下,且岳飞等虽然大捷,金国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衰竭,否则不会二十年后完颜亮再次排山倒海般地南下,那么宋随时可能重演“靖康之难”。如果放弃中原,宋朝的前沿就是江、淮地区。建炎以来的经验证明,每一次宋军都主要在这一地区与金人拉锯,并最终打退了金人。因此,把前沿放在这一区域,反而会使宋朝更为安全。对这种地缘结构的分析,估计会是高宗最终做出第(三)种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种战略选择下,绍兴年间恢复了经济实力的南宋,就开始在半壁江山里全力恢复北宋的政治、文化成就,于是南瓷就迅速地迎来了复兴,并创造了中国瓷器史新的高度。
靖康之难,宋王朝损失惨重,不但损失了两位皇帝,还损失了所有的庙堂物质文明。《宋史·钦宗本纪》:“”。衣冠文明没了、图籍典册没了、礼器没了,这就让南渡的朝廷没法撑起“礼”的结构。更让人烦恼的是,连能够制作这些东西的人和工艺(技艺、工匠)也没了,想重新把它们做出来都变得困难重重。
北宋晚期,是中国古代青铜礼器最后的辉煌时代。徽宗之好古著名于史,其之爱古玉不必再说,古玉行当就由他而生(见拙作《玉里看中国》)。徽宗之爱古彝器,更是痴迷,所以宋代连宫廷玉器都有仿青铜器的重器。政和年间,徽宗下旨做出了一大批水平极高的青铜礼器。但随着它们被掳到北国,就成了中国中央王朝青铜礼器的绝唱。同时,宋朝的玉礼器也都被掳走。这就使南渡的朝廷无法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比如祀昊天上帝、祀神州地祇等。没有这些祭祀活动,朝廷的合法性和正规性就都是问题。因此,尽快地做出一批新的礼器就成了当务之急。
青铜器的铸造和玉器的琢制自古即以官方作坊为主,且需要动用的原料资源要求极高。当半壁江山不在,官方工匠又都失去的情况下,这两大类的礼器就很难快速恢复。好在造瓷器需要的资源远没有青铜与玉器要求高,且几百年来瓷器生产的大本营都在南方。因此,以瓷来制作礼器就成了最现实的选择。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建炎四年四月,在海上漂泊数月的宋高宗驻跸越州,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之后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江南失地逐渐收复。诸将在与金的拉锯战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胜利。金人逐渐向江、淮退却,最终于次年(绍兴元年)的二月退回了中原。至此,高宗即位四年来终于得到了喘息机会,朝廷也终于初步安定了下来。于是,以越州为行在的高宗改元绍兴,四月即命制作礼器。朝廷要恢复祭礼,宣布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继承大宋正朔的政权了。其中,大批用以替代青铜及玉礼器的瓷礼器,就由已经没落的越窑烧制。
从“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一语可知,这一次瓷礼器的烧制是典型的“制样须索”模式。客观地说,这个政治任务能够落在越窑身上,并不一定是因为越窑的制瓷水平依然很高,更有可能是因为着急使用,而越州作为行在可以直接监控烧制,并可以免于运输。当然,不可否认,越窑有悠久的秘色瓷烧制历史肯定也是重要因素。绍兴元年十月,越州升级为绍兴府,从此绍兴这个城市名称出现于历史。
绍兴四年,绍兴府的瓷窑再次承担了瓷礼器的烧制任务。《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这一次的史料记载里已经有了“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之语,说明朝廷对于瓷礼器烧造过程的干预大大加强了,已经超越了“制样须索”的限度而实施了直接督造。这似乎暗示了三年前的那一次烧制成果并未让朝廷满意。
上林湖越窑遗址博物馆藏越窑天青釉碗
那么绍兴元年和四年这两次烧制瓷礼器,是由越窑系的那个窑口来完成的呢?1998年至1999年,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寺龙村北的寺龙口窑址考古发掘证明了,这里以及附近的低岭头是那两次瓷礼器的烧制地。或者说,这里是越窑的绝唱之地。
据《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简报》的相关结论:“”。
这也就证明了:南宋朝廷虽然把瓷礼器的烧制任务交给了越窑,但是北宋晚期河南诸窑奠定的“天青色”青瓷釉色新标准并没有改变,越窑曾经的“千峰翠色”已经正式被宫廷淘汰了。如今在宁波慈溪上林湖遗址博物馆及杭州浙江博物馆内,都藏有越窑所处天青釉瓷,馆藏标注多为北宋,但从以上史料逻辑及考古证据来说,似乎将这些天青釉瓷定为北宋、南宋之交或直接定为南宋早期更为合理。
浙江博物馆藏越窑青瓷牡丹纹龟钮盖罐:博物馆标识时代为“北宋”,但从其天青釉色来看应为南宋初期之物。
由于越窑必须生产自己并不擅长的,施用乳浊釉的天青釉瓷。自然越窑就无法体现出曾经的贡瓷生产水准,毕竟一些汝窑工艺并不是越窑擅长的,甚至是陌生的。比如:汝窑使用馒头窑烧制,而越窑瓷系从商、周时期开始就一直使用的是龙窑。再比如:汝窑是满釉支烧,而越窑早从五代起就是垫圈烧制。在寺龙口窑址出土的非天青釉瓷器都是垫圈烧制,而天青釉瓷器则有一部分是支烧,一部分是垫圈烧制。这就说明,越窑在完成烧制天青釉瓷的政治任务时,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想必这两次越窑生产的瓷礼器朝廷都不能满意,所以历史给予越窑的这次翻身机会也就此失去了。越窑之后湮没无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两次瓷礼器在越窑的烧制,却正式拉开了南瓷复兴的大幕。很快,因为对这一批越窑生产的天青釉瓷不满意,促使朝廷加快了恢复北宋官窑的速度。新的官方用瓷订单的竞争,也催生了整个南方瓷系的大复兴和大发展。同时,南宋对外贸易的井喷式发展,也让新的瓷器生产大本营崛起,“瓷都”这个概念开始出现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