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有一天突然问起来,“中国有美学家吗?”我有些激动,脱口而出,“当然有啊,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回答完,总觉着哪里不对劲,大概是因为我回答的是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家。
美学,一个高冷的词。记得大四的时候,纠结考研考什么专业?一个朋友问我喜欢什么,我也是同样脱口而出,“音乐、文学、艺术、电影……大概都喜欢。”朋友笑了笑说,不用纠结了,就学美学吧。
学美学的三年时光是美妙的,课堂上,讨论过“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这样无尽、形而上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案;也从看一朵花、看一幅画、发呆一分钟开始认识美。课堂之外,经常有人问,“美学是干什么的?学出来以后做什么工作?”我被问得哑口无言。在世俗意义上,美学大概就是典型的“无用之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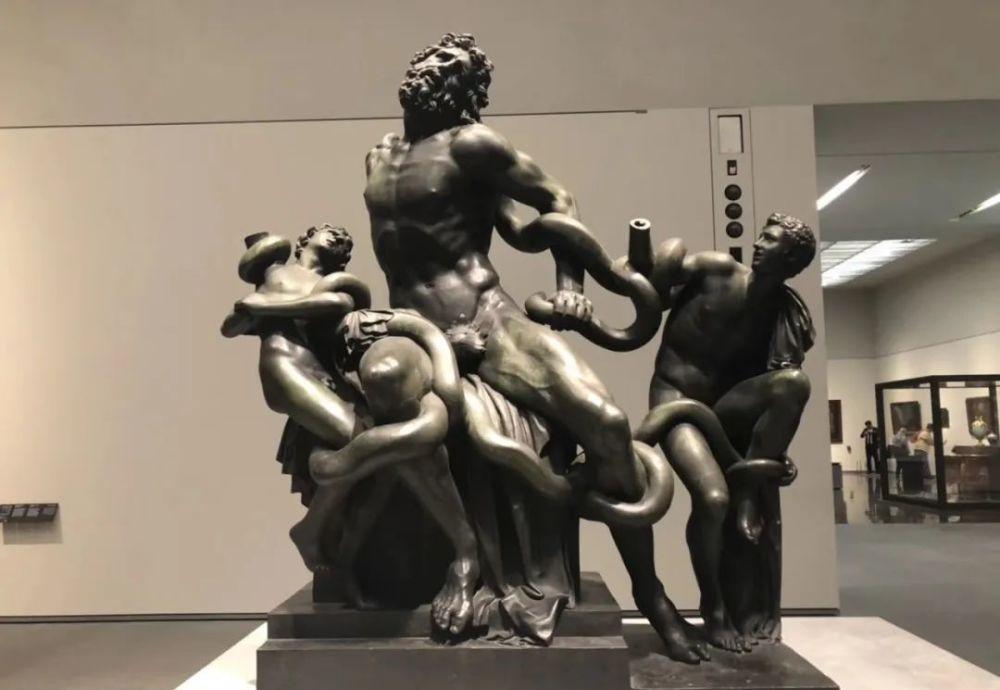
毕业之后,发现到处都是“美学”:美发有造型美学、美容有形象管理美学、设计有品牌美学、养生有生活美学、装修有家装美学……只是这些“美学”大多只是世俗美感的,用金钱可以购买得到的美。是被事先定义好的美,一时流行的、短暂的美。
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伪美学时代,高呼着美学,却鲜少用心去体会美的真实与微处。高喊着美学,却还是不停追求着“美学的功利性”,而那份从内心发出,清澈的、微妙的、真实的美,早已是奢侈……
真正的美学是什么?这个亲切的问题一抛出来,脑海里浮现起课堂上大家一起讨论的情形:“美是和谐”、“美是理念””、“美是上帝”、“美是完善”“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西方的先哲们回答这个问题总是抽丝剥茧、丝丝入扣,美在这里是认知与思辨的,总泛着思想的花火。
知识与智慧不太一样,知识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证明是对的,知识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能掌握的。智慧却并不如此,它是比知识更为恒久,也比知识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它是多维的,可以是一时之悟,也可以是植根于文化深处和心灵深处的良知。
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美学“一词,但处处可以见到“美”。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语境表达中,“美”往往是以“智慧”而开启的。
年少时老师讲《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故事,孔子问四位弟子各自的理想。子路先急匆匆的表明自己的理想是治理一个兵衰民饿的弱国,让弱国之民学会勇敢,自然国富民强;冉有谦虚一点点,说自己可治理一个相对安稳的国家,让百姓富足;公西华显得更为谦虚,他只愿做个小官,遵守礼仪。
孔子听完都摇了摇头,问旁边鼓瑟的曾皙,曾皙不慌不忙,琴声渐渐稀疏,说到自己的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己的理想不过是初春时节,穿着春天的衣服,和几个朋友,带着几个孩子,到沂河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走回家。
孔子听完会心一笑,自己和曾皙的理想一样。这样的理想不大,甚至极小、极日常,但里面有四季、有天地、有人心,全然是纯净而清澈的,这样的美感是浑然天成的,这也是一种非凡的智慧,是真正的美。
同样的,在近代美学大师宗白华的眼里,美和诗的寻求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位吃透东西方文化的大家给出了极平淡亦极悠远的理想解答:
诗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真正的美从来不是苦苦寻得的,而是在生活纯净的细微末节处。和孔子与曾皙理想中的“咏而归”一样,纯洁、善意、平和。
从前吴冠中先生说,“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各种“美学”花样百出,美学教育比比皆是。无可否认,我们这个时代审美多元了。人们的物质条件更好了,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一切。
我们似乎掌握了审美的主导权:刷某宝和某音时,大数据算出我们的喜好,推送我们喜爱的事物;每天都有很多风格博主,教你打扮出别人眼中好看的自己;想拥有好身材,有减肥训练营,吃一根营养已经配置好的蛋白棒就解决一切;打开电子书城,有一个“猜你喜欢”,如果不喜欢,可以点击“换一换”……我们看到的真的是我们所喜欢的吗?泛娱乐化、泛个性的世界,真的是“美”吗?
记得有一个朋友,是大家认知的“大龄剩女”,她一心想要摆脱这种困境,也想找到最好的自己。于是报名了一个美学形象管理班,想要先从外貌上自信起来。谁知一去,所谓专业的医美“美学家”分析了她的五官问题,一股脑的她整容了,从脸型到鼻子、从双眼皮到发际线都按流行的“美”调整了,背负了一身的债务。看到现在的她,有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但缺少了原有的自然,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还有一些所谓的美学教育,在室内教小朋友写作文,变了无数个写作套路,条条框框像公式一样。小朋友写出来的文章全然是自己所知的高分套路,而非所感到的真实与美。
高喊美学的时代,或许是一个伪美学的时代。那些大数据挑选出的“喜爱”,一定程度也在缩短我们的眼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喜爱;市面上花样百出的“美学”,能快速占据我们的心,也能快速被我们遗忘;美学专业还是最高冷、最难找工作的学科;高谈美学的人们,还是在拧巴地过活,忽而高高在上,忽而满目创伤,说人们不懂美。
美不是一时的快感,更不是浮于感官的快乐。美是能清洗灵魂的,而不是让欲望膨胀的;美是自然而然的自信,而不是活在他人的眼中;美是需要沉淀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夸张。
美是能让人“免俗”的,而不是又让人掉进“俗套”里;美不是单纯的占有,或是某个具象的事物,而是形成一种“场”,像空气一样,自然流动着,向内和向外对自我、对世界真实的敞开。
“如何进入一个真正的美学时代?”当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胆怯的、是失落的,但总有希望盈盈然在心间。
八十八年前,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说,“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可是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
朱光潜先生心怀着有限的失望与无限的希望,只想轻轻的告诉人们“慢慢走,欣赏啊!”
八十八年后的今天,更有太多的急匆匆,太多想要占有的快乐,太多不真心且不自知的“喜欢”,但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嫌弃所处环境的无聊,自嘲又丧又怂,心里明明白白地与原有的理想越拉越远。
我们更需要“慢慢走,欣赏美”的态度来过活啊,来进入一个真正的美学时代。带上发现美的眼睛在这个世上流浪,倾听一朵花的开放、注视一双眼睛的透明、心领神会一个笑容的可爱、流连天空云朵的缓慢。美,不该只是遥远的理想和高贵的说辞,而是对自我的坦诚,以及对万物的敬畏。
我想,人人都可以是美学家,生活才是最大的、最有意思的艺术。只要我们在才此刻感受了真正的美,此刻就是一个美学时代。
写这篇文章时,生怕说得太多,变成了讲道理;也生怕说得太少,变成了泛泛而谈。离开学校才发现,美学不是读几本美学书哲学书就读得好的,那些读过的书只是种子,至于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不是浇水修剪而已,还有四季的变化、广阔的天地和路过的人们。
美学,也许真是难的,总难以用言语准确传达它的意味,稍有不慎,甚至会破坏它的本色。
美学,也许是简单的。它就是最为原初的“因为喜欢”,不是高高在上的“真、善、美”,而是一种实在的“真、善、美”,在山、在水、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因为喜欢”也是一切有趣故事的开始,但这份喜欢定是真诚的、是有所延伸的、是会触达到内心深处的,美因为喜欢而生发。
如果真正进入了一个美学时代,这个时代会好吗?这个时代会更好的。
看更多走心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