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信上读到纪念许国璋先生的文章,不觉想起三十几年前的往事。
当时,母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书,我家住在北外西院19楼4单元。许国璋先生原住西院北楼,那楼住了不少老教授,像周珏良、危东亚、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等。八十年代中期,学校新建了几栋宿舍楼,给几位居住面积不达标的老先生,每人补了个一居室,许先生也得到一套,位于19楼1单元1层。于是,我有幸跟先生成了一栋楼里的邻居,与他常在楼下或院里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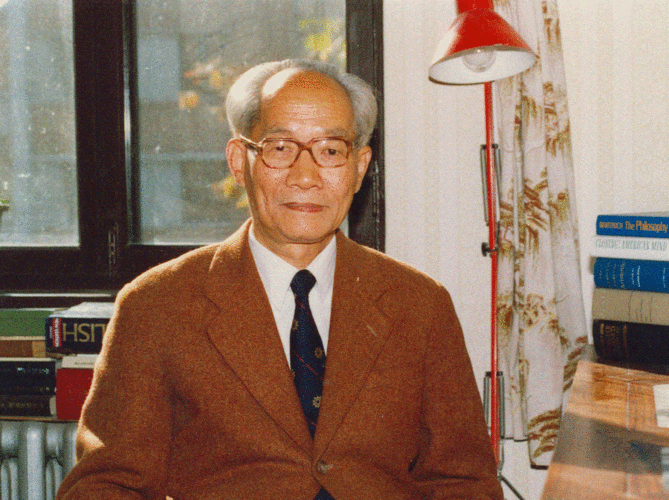
图:许国璋先生在家中。(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的许先生应该是七十岁左右,喜欢穿件绛色粗呢西装,足蹬牛筋底白皮鞋。记得一位熟识的英语系女生说,有一年,先生从香港讲学归来,跟系里学生们讲话,其中说道:女生应该把高跟鞋扔了,运动鞋配裙子才美。她还说,每年开学,许先生都自掏腰包,用稿费买汉英词典,每个新生,一人一本。当时,先生主编的“许国璋英语”,火遍全国,年销售几十万册,他从所得稿酬拿出不少用来资助英语教育。
图:“许国璋英语”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许先生是北外校园的一景。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是先生休息的时间。常可看见,他坐在面对学校大门的楼前花坛水泥围墙边,手里拿着刚从小卖部买的纸杯冰激凌,津津有味地吃着,看着过往行人和车辆,怡然自得。时有路过的教师或学生,认识先生的,就会驻足跟他聊上几句。
当年,出了北外西院大门左拐,人行道边有一溜卖菜的摊贩。一次,见许先生走到一处鱼摊前,一言不发,那鱼贩立即从盛满水的黑色塑料大袋里,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草鱼,用草绳穿好,递到先生手上。先生提起鱼,掉头就走。我惊诧鱼贩不称重、先生不付钱,便好奇地小声打探,鱼贩笑答:“他一个月一结。”又有人问:“这是谁呀?”鱼贩得意地说:“他可是北外最有名的教授。”
有时,可以看见许先生和许师母一起出行。总是许先生走得快,许师母走得慢,落在后面几步。师母走路不太灵便,她那双脚仿佛是解放脚,即小时被缠过足后又放开的。许师母,瘦高个儿,细白皮肤,鹅蛋小脸,大眼睛,仍能看出当年风姿的绰约,听说年轻时她在上海做过舞女。
图:许先生、许师母和学生。(图片来自《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
一居室是许先生的一块飞地。他每天从北楼过来做事。有时,饭点儿,许师母过来叫他回去吃饭。有时,做事做晚了,他也住在那里。
许先生在飞地的小院里,种了些花草菜蔬。小院近旁的道路略高于楼前地面,站在路上可以望见院中情景。常见许先生站在路边,微笑着欣赏自家院里的葱葱郁郁,并不时和路过的人讨论几句。一次,见他站上路边矮墙,倾身查看小院里面的植物。那院里生长的荷兰豆,曾让季羡林先生赞不绝口:
“他(笔者注:此指许国璋先生)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我家里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当时还算是珍奇的荷兰豆,嚼在我嘴里是什么滋味,这里面蕴涵着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于万一。”(季羡林《悼许国璋先生》,《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季先生的描述绝非夸张,八十年代,荷兰豆对于很多城市的居民,确是特别稀罕的美味。我们第一次吃到,还是在昆明的叔叔、婶婶,乘飞机来京时带的。碧绿碧绿的颜色,清脆甜嫩的味道,在当时蔬菜匮乏的北京,真令人啧啧称奇。上海的姑奶奶也尝过这来自昆明的馈赠,一次叔叔又要去上海,老人家特别叮嘱:“再带些像翡翠似的菜吧。”
许先生还种了些爬墙虎。飞地在19楼东端,爬墙虎顺着高楼东墙,向上攀缘,长得飞快,不知什么时候,就从一层爬到了顶楼六层,枝繁叶茂,差不多铺满了整个墙面。夏日,一墙青翠;秋来,满目殷红。
1993年某天,听说许先生夜里从飞地的行军床上摔了下来,中风了,就此一病不起。又听说是因先生此前赴欧讲学,过度劳累所致。第二年秋天,许先生过世,享年七十九岁。
图:《许国璋论语言》书影。
记得八十年代末,当时社会上还残留着一些极左文风,文章开头不乏“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等套话。导师张志公先生曾对我说,一次应邀参加许国璋先生博士生论文答辩,看到文章中有“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语句,便在提问时请那学生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简要说出个一二。许国璋先生闻之惊愕:
“还有这个?我怎么没注意到。”
拿过论文,翻到出处,抬头对学生说道——“你把这句删了。”
图:《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书影。
手上的《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是1997年在北外西院大门外学校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的,从书中文章了解到,许先生虽去过很多国家,可从没机会到访欧洲大陆,一直念兹在兹,心驰神往。那次,本来说好由一学生陪同,最终不知何故变成只身前往。他万里走单骑,讲学游历了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意大利、瑞士、俄罗斯等国。毕竟是年近八十的人了,怎么禁得起如此辛劳的旅程?
图:1993年5月,许国璋先生在苏黎世湖上。(图片来自《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
再次翻阅《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眼前出现先生在“大如剧场的电教馆”演讲的身影,铿锵的话语震响耳边:
“我教学生,从来不以教会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为目标,而是要教怎样做人,是英语教育,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育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我们的理想要高一点,要做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只想练些应酬英语,到合资企业去跑腿,去做翻译,目标太平凡也太庸俗了。你就是做了合资企业经理,举止是不是要有修养些?谈吐是不是要更典雅些?写作时笔下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文化内容?否则你每月挣成百上千,我也很鄙视你。我一般不随便跟人说话。你要跟我说话,我首先要看你有多少文化内涵。否则我这样一个教授,来陪你练英语?
现在外国人来,不论老太毛孩,一律号称专家。专什么家?有的不过会说外语,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了不得。他们是专家,那么美国大街上走的都是专家了!他们见了我还是毕恭毕做的,不敢在我面前放肆,妄议‘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语言水平比他高,分析问题比他深刻,他受的教育、读的书不能跟我比啊!”
(傅杰《这就是许国璋教授》,《许国璋先生纪念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
这真是空谷足音,广陵绝响。
许先生和许师母没有小孩儿。
许先生走后,在校园里很少见到许师母了,那满墙的藤蔓也渐枯黄衰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