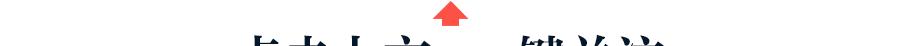
記者/劉思潔
2020年11月份,張倩帶着孩子從随州老家回到闊别八個月的武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還在懷孕的她被确診為輕症患者,後來順利産下一個健康的寶寶。
疫情之前,她和丈夫、公公、婆婆以及奶奶住在一起。疫情來臨,本身是醫生的公公最先倒下,最後全家有四人受感染,公公、婆婆和丈夫一樣,是重症患者。好在一家人最後都挺過了疫情,張倩把寶寶的小名取做“恩恩”,希望能夠記住在疫情之中人們對于她家以及武漢的恩情。
雖然疫情已經過去,但是疫情的影響并沒有在這個家中消散。半年多過去了,家中仍然堅持着分餐制。公公婆婆對于新冠後遺症的消息格外敏感,直到今日,他們還有着肺部、膝蓋關節等器官的後遺症。和外化的身體上的影響不同,更隐秘的變化發生在家庭的氛圍和人們的心理上。
以下是張倩的口述:
<h1>病毒的陰影一直籠罩在家裡</h1>
我在2020年11月帶着孩子回到武漢的家,到家時,才覺察到家中的氛圍有些冷清。我本以為因為寶寶的到來,一家三代之間的聯結會更加緊密。但是對新冠病毒的恐慌讓這種親密消失了,回來至今,家人們還沒有坐在一張桌子上好好吃過一頓飯。
家中施行分餐制,每天婆婆做好飯,分成固定的份數。吃飯時,有人坐在餐桌,有人坐在客廳,有人回自己的房間。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或許是因為我們都覺得,疫情期間我們家人接連倒下,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在一桌吃飯。我老公的奶奶今年八十多歲了,她一直跟我們生活在一起,她是我們當中唯一沒有感染新冠肺炎的,她一直沒和我們同桌吃飯。
我慢慢接受了這個新習慣。最早丈夫去随州我父母家看我,他就不在我們一個桌子上吃飯。當時我母親會勸他,但是他說注意點好,他怕自己還沒有完全好,會傳染給大家。
這種變化是心照不宣的,公公婆婆在家時還會戴着口罩,他們也分屋住了。大家不會去讨論這樣做是否應該,也沒有人提出異議。雖然我會覺得大家不親密了,但是也接受了這樣的變化。
公公婆婆對待“恩恩”也特别注意,不敢過多地擁抱,偶爾會戴着口罩坐在沙發上,看着寶寶自己玩一會兒。育兒的任務落在了我一個人身上,公公婆婆連孩子的奶瓶、衣物等個人物品都不敢碰。婆婆不敢帶“恩恩”,一是怕自己沒有完全好,感染了孩子,二是婆婆現在有後遺症,身體狀況也不太好。
後遺症,我公公、婆婆,還有我老公都有。最初的時候,家裡買了制氧機,公公婆婆每天都要吸氧,他們的自主呼吸能力很差,氧飽和度一度下降到70%多。公公的肺部至今纖維化還沒有好,而婆婆每天總是喊着自己的膝蓋疼、腿疼。婆婆之前膝蓋也有一些積水,但是沒有現在這麼嚴重。每天一般都是婆婆去買菜,去菜市場步行十分鐘的路程,對她來說都有些困難了,她需要停下來歇好多次。老公現在的體力也不如之前了,有時幹點重活也會大喘氣。
家中沒有我想象中其樂融融的樣子,病毒的陰影一直還籠罩在家中。當時全家生病的時候,就想着大家都一定要挺過來,然後能整整齊齊地坐在桌子前吃個團圓飯,但現在這似乎成奢望了。我們出門,還是會做好全面的防護,回到家全身上下都會用酒精消毒。而寶寶,如果有人想要抱她,我都會拒絕。我們是真的怕了。
<h1>“恩恩”要記住人們的恩情</h1>
現在家人、我自己都不願意去回憶當時我們得病住院的日子。家庭成員之間幾乎都不會交流疫情的事情。畢竟對于我們來說,那是一段痛苦的回憶。疫情來得太兇猛了,我們家最先倒下的是我公公。公公是醫生,有一個自己的診所,或許就是整天接觸的病人太多了,他感染了。
四月武漢解封後東湖運動的孩子。
我也感染了,我是2020年1月25日出現的症狀,當時距離我的預産期還有兩周。最開始,我想要做一個核酸檢測都非常困難,跑了好幾家醫院都做不了。當時老公開着車帶着我和婆婆去武漢的各大醫院跑,想要找到一家能夠接收我們的醫院。
我的情況很特殊,既是新冠患者,又是孕婦,許多醫院的手術室沒有條件來給我做剖腹産手術。武漢封城後,街上幾乎看不到人,隻有醫院裡的發熱門診人最多。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十點多,老公帶着我們去找床位,我們到了武昌醫院和天佑醫院,當時兩家醫院的發熱門診的座椅上、走廊上都是人,有人站着打吊針。人們戴着口罩排着隊,其實就是想等着醫生能給他們開點藥。到了人民醫院時,我看到急診室裡拉出了沒有救過來的人,當時我好害怕。
我們在網上聽說哪裡有床位了,就往哪兒跑。但是去了往往是撲空,甚至在醫院等過一整個晚上。那時天氣冷,我們又都生着病,太絕望了。最後我們在網絡上求救,每天有好多人幫我們想辦法,幫聯系醫院,聯系醫生。我也不知道是志願者還是社群那邊起了作用,我最終被中南醫院收治了,我那時啥都不多想了,腦子裡一片空白,隻想把寶寶健康生下來。
“恩恩”最終在2020年1月29日降生了,我都沒有機會好好看看她,隻聽到了她的一聲哭聲,然後護士們把她抱在我頭頂處清洗,我看到了她,紅紅的。然後她被抱走了,我當時就給她取名“恩恩”,希望她長大了能記住疫情中人們給予的這份恩情。
我的老公1月30日住進了醫院,公公婆婆在2月5日住進了醫院,當時是中央說要“應收盡收”的時候。
後來我的父母從随州趕來,把恩恩接去随州照顧。當時接恩恩的過程,我爸媽全程高度緊張,之前給寶寶準備的所有東西都扔掉了。他們用嬰兒包被包裹着恩恩,在她臉上蓋着一個方巾,從電梯出去直接上車,全身消毒,沒有任何停留就駛向了随州老家。
我是輕症,很快就出院了。我回到家中,姐姐從随州趕來照顧我坐月子。雖然是她照顧我,我們住在一起,但是我們一兩個月沒見面,她每天就把飯放在我的房間門口。其實我當時整個人的狀态都不是很好,心理壓力很大,主要是丈夫那邊一直高燒不退,我很擔心他的情況,怕他出什麼事情,坐月子的時候我總是哭。後來他慢慢好轉了,我的狀态也就好了起來。
<h1>為了寶寶,一切都值得</h1>
在三月底四月初,家人們陸續出院。2020年4月8日淩晨武漢解封的那天,我和姐姐提前就去高速路口等着,車上裝着我給孩子準備的各種物品,内心激動。我們回家啦,終于見到了我的恩恩,最開始我不敢碰她,到家是深夜,我蹑手蹑腳地去看她,發現她怎麼長得和視訊裡不一樣呢,好像比視訊裡更大一些。
慢慢陪伴孩子成長是一個很幸福的過程,孩子一天天跟你親近,你被她依賴着,看到她的變化,比如五官長開了呀,第一次擡頭,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喊媽媽,現在她在慢慢學着和人打招呼,每一個小小的進步都會讓你驚喜。她有時會來摸摸你的臉,把臉蹭到你臉上,你會感歎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小東西。無論生活再怎麼糟糕,都無所謂了,看到寶寶,你就會知道你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疫情過去了,新的生活也要開始了。雖然我們偶爾還是會感受到一些歧視,比如老公在深圳的公司和老公協商解約了。好在在武漢找工作順利,也沒出什麼問題。之前我公公的外孫女每天中午都來我家吃飯,但是疫情之後,她和她的母親再也沒有來過我家了。她們都說着要我們注意防護,還是有擔心、害怕。現在我公公每天中午把飯送到他外孫女工作的商場,讓她在那裡吃。
公公婆婆似乎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妥,但是我還是覺得這樣有些不太好,畢竟是親人。在外人面前,我們不會主動提起自己曾經是新冠患者這件事,但是要是需要我們說明自己身份的時候,我們也不會隐瞞。
現在每個月都有社群組織我們去做檢查,公公婆婆還在堅持吃中藥調理身體,總體來說他們的身體狀況比剛出院時好很多了。也感覺,經曆了這場疫情,大家都把很多事情看淡了,覺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們對恩恩也沒有什麼過多的期待,隻希望她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疫情之中,我們一家人團結在一起,我跟老公經曆了這樣的大風大浪,我們的關系更緊密了。現在周末時,老公也會照顧孩子,我們會帶着恩恩到樓下曬曬太陽,周末會去家附近的遊泳館遊泳。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之後應該會搬出去住,經營起自己的小家庭。公公和老公都恢複上班了,我也抽閑暇時間在網上賣賣東西,一個月有時能掙一兩千塊錢。
很多事情我不願意去想了,過去了就過去了,生活還在繼續。
(為保護受訪者隐私,張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