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日前,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署長戴維·比斯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全世界最富有的兩個人,馬斯克(特斯拉創始人)和貝索斯(亞馬遜創始人)企業的市值都超過萬億美元,隻要拿出自己2%的财富來支援聯合國食品救助計劃,全球因疫情出現的4200萬人的饑餓問題就有可能得到解決”。這個表态很快引起了國際關注,也讓人感到疑惑。疫情沖擊、氣候變化加上經濟長下行周期三種力量疊加導緻目前全球出現新的人道主義災難,理論上聯合國應該首先向各會員國公共部門求助,為什麼反而向私人機構求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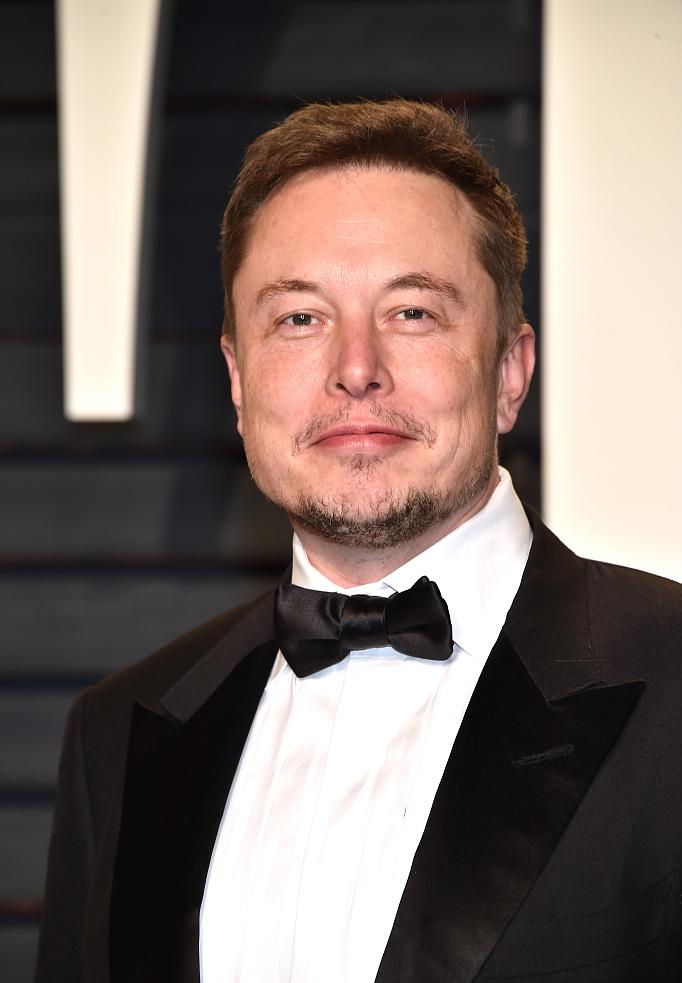
馬斯克資料圖
實際上,這樣的做法有先例可循。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多年累積欠聯合國費用曾一度達到十幾億美元(聯合國當時一年的經費約30億美元),再加上增加了維和活動、人道主義救助等項目,聯合國營運常常入不敷出。世界各國一直要求美國支付多年的欠賬緩解聯合國費用不足,但是,不管國際上怎麼呼籲,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就是對欠費不聞不問。最後,美國傳媒巨頭坦德·特納承諾如果美國政府不還錢,他這個納稅人替美國政府還,後來他個人宣布捐贈10億美元,支援聯合國及其事業。這也開創了聯合國和商業界合作的先例。這一次,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署長戴維·比斯利實際上還是想故調重彈,希望通過非正常手法解決4200萬人的饑餓問題。但這種一事一解決的方法不是制度上的可持續之法。
聯合國機制在過去30年一直營運不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在蘇聯解體以後,覺得自己可以通過單邊主義做法擺平全世界的絕大多數事情。對它而言,聯合國有時候反倒變成絆手絆腳的平台,是以,當符合自己利益的時候就拿過來用,用不着的時候就撇在一邊。美國的實用主義做派在國際組織建設上帶了一個很壞的頭,讓包括美國盟友在内的許多國家時常感到頭疼。
美國的黨派政治也時常對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公共品制度建設形成幹擾,影響國際合作。上世紀90年代美國共和黨内競選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有一個叫帕特裡克·布坎南的候選人,他提出的4個重要的競選綱領之一就是,如果他赢得總統大選,上任的第一天就會下令讓聯合國搬出美國。他表示,如果聯合國做不了這件事,就派海軍陸戰隊員幫他們卷鋪蓋滾蛋。而他竟然一連赢了四個州,最後共和黨人聯起手來才迫使他退出競選。到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更是接連退出聯合國幾個專門機構,屢屢拖欠會費,試圖把聯合國變成一個讨價還價強取好處的場所。
衆所周知,二戰後國際治理體系的複興和重建有四個引擎,政治體制方面的合作是聯合國,貿易領域的合作是國際貿易組織,開發和重建領域的合作是世界銀行,交易所依賴的匯率體系和流動性支付領域的合作是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後來,還補建了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随着技術進步和全球貿易的增加,全球合作和協調的任務也成倍增加,但是,這些組織的營運經費,在美國的壞示範影響下,入不敷出的程度更加嚴重了。
如何救助4200萬饑餓人群隻是聯合國系統面臨問題的一個截面,借助私人部門力量,想各種辦法盡快為這些人提供救援很有必要,但更應該思考的是,類似問題的解決如何建立在制度保障的基礎之上。
戰後複興和重建的四個引擎制度,在過去近80年間向廣域範圍和深層次延伸的速度太慢了。人類發展到了21世紀,數字技術支援下的聯網共享平台出現,具有了全新的制度建設含義。技術平台本身既是個公共品,同時也是市場競争性産品單元的互動場所,“府-産-學-研-資-商-媒”七個人類經濟最為活躍的領域實體,可以在新的平台上打破原有的技術制度四堵牆,在世界範圍内進行一體化合作。全球數字網絡網格的“綿密性-高通量-低延遲時間-隐秘性保護”也可以讓新的合作更有效率,讓救助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合作的意義上,更好地解決人類超國家範圍合作的很多問題。多邊機制的合作應該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導引下,在更高層次上解決國界之間的科教文化、環境保護、碳中和使用、發展鴻溝、食品安全、人道救助、太空開發甚至新的數字發展鴻溝方面的問題。(作者是中信基金會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