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梅是一名女性宇宙學家,而杜磊是一名養蜂人。由于時空的扭轉,他們在平行宇宙中沒完沒了地相遇,而他們的愛情故事因為時間的微妙擾動,走向了50種或溫馨、或遺憾的結局。這是新浪潮戲劇導演王翀的作品《平行宇宙愛情演繹法》,10月21日晚,在佛山大劇院上演。
對于廣佛地區的觀衆而言,能在“家門口”看到這部作品殊為不易。受疫情影響,它先是從今年1月推遲到6月,又從6月延期至8月,後來又重新定檔10月。劇中負責“扭轉時空”的活體倉鼠,甚至在等待中耗盡了它的一生,以緻劇組隻能在開演前補招動物演員。然而觀衆們的熱情并未消減——繼國慶假期廣州連演40場的《存在與時間2.0》之後,佛山終于迎來了首部由王翀執導的新浪潮戲劇。
2012年,剛滿30歲的王翀發表了《新浪潮戲劇宣言》,他的一批極具探索氣質的作品,在劇圈内外刮起一陣旋風。近十年之後,39歲的他對南都記者形容,自己到了一個微妙的“坎”上,有了一種危機感。就在2021這一年,他賣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房産“停電亭”,開始用微信,養貓,嘗試“換一種活法,尋找新的人生着力點”。不變的是,依然在作品中反觀時代,叩問“當下”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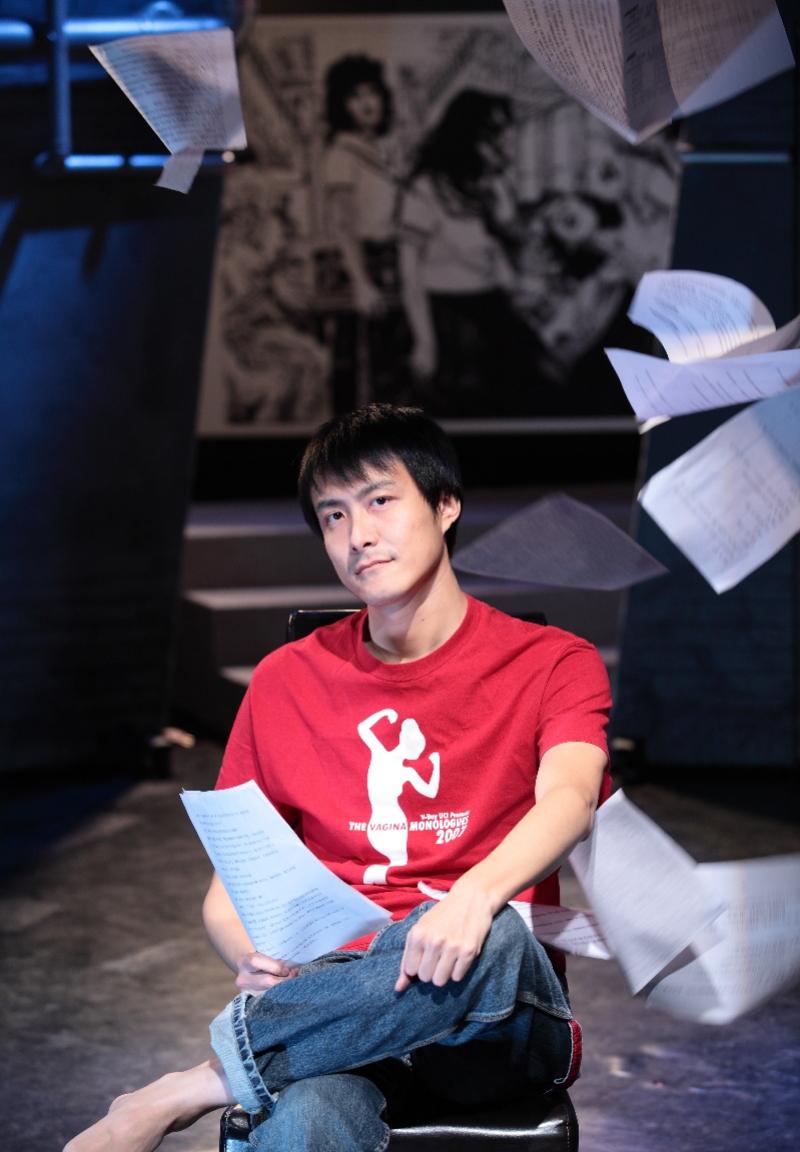
王翀。受訪者供圖
“看得懂”的新浪潮戲劇
《平行宇宙愛情演繹法》(以下簡稱《平行宇宙》)與電影《羅拉快跑》的結構有些相似,但它将蒙太奇手法移用到現場演出中,并極力推高“重新開機”的次數,無論對演員還是觀衆,都構成了另一量級的挑戰。
這種“極緻”,正是王翀想要的。在《平行宇宙》的舞台上,他設定了13台錄影機,其中1台位居舞台中央,另外12台如同表盤上的12個時刻一般環繞在它周圍,男女主演需要在這些鏡頭組成的“平行宇宙”中精确走位,而舞台後方的大螢幕則會在13台錄影機呈現的即時畫面之間快切,現場“生成”一部有50種故事走向的影片。演出結束時,卻并不存檔。2015年,該劇在國内首演時,27歲的女主角王小歡曾因精湛的演技,被媒體選為“年度新銳戲劇人”。
10月21日晚,《平行宇宙愛情演繹法》佛山演出劇照。
當一對男女的愛情故事重複50遍,幾乎推演出了一段感情中的所有可能,王翀相信,觀衆很容易在《平行宇宙》中找到共鳴,被“某個情境的某個分支”牽起回憶。與此同時,它也給有心人留下了一串思考題:眼前上演的,究竟是一部戲劇,還是一部電影?兩種藝術形式怎樣互相關聯?邊界又何在?
或許可以這樣說:王翀發起的新浪潮戲劇,正是以“提問”為特征的;作品夾帶的問題,每每挑戰着最根深蒂固的戲劇觀念。在發表于2012年的《新浪潮戲劇宣言》中,他明确表達了破舊立新之意:“我們的劇場在浪潮之上,撲向舊的劇場。澄明的海水沖刷着舊劇場裡的塵土和污垢,把淡紅色的屍體帶走,留下魚和美麗的貝殼……我們乘風破浪,探索沒人去過的海域,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每一縷新鮮的陽光裡。”全文不足500字,卻影響深遠,至今讀來仍有激蕩人心的海浪聲。
站在2021年的時間節點上,王翀回顧說,當年他和朋友們對于“新浪潮戲劇”尚未形成完整的認識,乃至成為一種風格流派,“就是喊這一嗓子本身很重要”。沿着這條道路走了近十年後,《宣言》中未及摹狀的圖景已然清晰。用他的話說:“新浪潮戲劇總結起來,就是在不同方向上嘗試突破戲劇藝術的邊界,探索它的極端形态和戲劇存在的本質;借用‘戲劇憑什麼必須是什麼’、‘戲劇有可能成為什麼’的反問,沖擊傳統的戲劇觀念,為中國戲劇開創新的道路。”
比如《平行宇宙》在戲劇舞台上引入攝影機、“邊拍邊演”,就是新浪潮戲劇的典型方法之一,它誕生在王翀執迷于“劇場影像探索”的時期;在《雷雨2.0》《一鏡一生易蔔生》等作品中,同樣可見類似的嘗試,但是影像的風格與探索的方向有别。除了将戲劇與影像結合,他還試驗過“抛棄劇場”,讓演出發生在教室、走廊、公共廁所等非正常空間,甚至幹脆線上上、在網絡連線過程中。最近幾年,他推出的“極小戲劇”三部曲也引起了大量關注和研究,從每場限11名觀衆的《茶館2.0》,到取消現場演員、讓4名觀衆成為角色的《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2.0》,再到剛剛于廣州完成首演的《存在與時間2.0》,每場8位演員,卻隻接待1名觀衆,将戲劇規模和觀演關系的實驗推向了極緻。
許多觀衆對他的戲劇作品充滿了好奇,又怕自己“看不懂”,而王翀以為,無論此前看劇多少,任何人在走進劇場時都不必有此擔心:“我覺得隻要心靈是開放的,就能夠接受這樣的形式,就能夠進入我們的邏輯裡,擁抱戲劇中的每一個精彩瞬間。”
“薪火相傳”與“2.0”精神
10月19日晚,王翀在佛山大劇院舉行的公開活動之後接受了南都記者的專訪。出生于1982年的他說,自己開始有了“中年危機”。但從他的面貌到表達方式來看,分明還是個年輕人。
他的戲也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年輕感”,好似仍然處于青春叛逆期,不屈從票房的評價标準,拒絕一切循規蹈矩。王翀對南都記者談道:“做任何創新的時候,現有的東西是什麼很重要。”而新浪潮戲劇的“假想敵”,正是被幾代人奉為經典的那種戲劇傳統—— “所見即所得”,一切為劇本服務,假裝有一堵看不見的牆橫亘在演員與觀衆之間。
為什麼王翀不肯“老老實實”地繼承戲劇前輩們的遺産,非要另起爐竈?他自己的回答是,這或許跟他接觸戲劇的方式有關。王翀看的第一部話劇來自孟京輝,彼時他還在讀高三,而孟氏執導的《戀愛的犀牛》剛剛問世、在社會上引起觀演狂潮;2000年跨進大學校門之後,王翀又曾為林兆華擔任助理,這位當之無愧的大導演出身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卻又熱衷前衛戲劇的探索,早在1982年就導演了“無場次”、虛拟情境、時空交錯的話劇作品。
王翀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完成了大學學業,但并未參與過盛名在外的北大劇社。他說:“劇社招新的時候我去了,但聽說有一個面試,我羞于表演,是以扭頭就走了。現在想想,錯過了不一定是壞事,可能戲劇是以在我這兒成了一種更有距離感的事物,更加神聖。”
中學時代,王翀癡迷電影,大學則混迹于天涯BBS的舞台藝術版。通過網際網路,他結識了專門來北京“駐地研究林兆華”的夏威夷大學博士生林偉瑜,也是以有機會進入了林兆華的圈子,大三大四就在他的工作室幫忙整理資料,也現場觀看了他的很多作品。“可以說,是孟京輝讓我對戲劇産生興趣,是林兆華讓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成為事業。”王翀告訴南都記者,“恰恰是因為整理資料的時候,需要對着文本細看,才會發現,‘原來這個戲這麼厲害’。”與此同時,他也系統觀看了北京人藝的演出錄像,“那種傳統戲,有些看進去之後也挺有意思的,但是當時我就感覺有點‘套路’;作為話劇導演,如果你的工作隻是按照劇本把一個戲排出來,好像也太簡單了,或者說沒有真正的挑戰,在我眼裡不值得我去追求。”
1999年,孟京輝執導的話劇《戀愛的犀牛》。首演卡司為郭濤、吳越。
懷着這樣的想法,大學畢業之後,王翀去了夏威夷大學讀戲劇碩士,2007年又前往加州大學攻讀博士,次年成立了“薪傳實驗劇團”。有趣的是,身為傳統戲劇的“反叛者”,他卻用了“薪火相傳”的詞義給自己的實踐冠名。王翀介紹,“薪傳”希望傳承的是“實驗戲劇的精神”。
擁有光輝傳統的劇團多半都有“保留劇目”,比如北京人藝,就有《茶館》《雷雨》等一批代代相傳的名作,也被藝術家們視為“家底”。而王翀認為,經典并非無可超越,後人不應該隻追求對經典作品“原汁原味”的重制,讓戲劇舞台變成“博物館”。
在發表《新浪潮戲劇宣言》的2012年,他就推出了《雷雨2.0》——劇中所有台詞均出自曹禺的《雷雨》,但人物關系已經跟原作不太相關,該劇被媒體評為中國内地小劇場戲劇30年“十大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2017年,他又在北京一所中學組織了《茶館2.0》的演出,每場邀請11名觀衆走進真實的教室,像旁聽一樣感受44名演員(多數為素人中學生)呈現的劇情,台詞依然是老舍《茶館》的台詞,故事背景卻變成了21世紀的校園。
“我覺得《茶館2.0》是一個特别能代表我的作品,”王翀對南都記者解釋,“它最能展現我所說的在精神核心上尊重大師、尊重原作者,而在導演手法上絞盡腦汁地去颠覆前人,尤其是我視為窠臼的‘博物館式’戲劇。”
2017年,在劇圈引起熱議的《茶館2.0》。
在王翀的宇宙中,似乎一切經典皆可“2.0”,如今帶此字尾的劇名也成了識别王翀作品的一種提示,而這不隻是文字遊戲。王翀說,“2.0”的含義即是“當下”,戲劇應該是行進中的藝術,與時代同行,永遠使用當代人的工具,關乎當代人的存在。
獨立戲劇人走向“四十不惑”
王翀最新創作的戲劇叫《存在與時間2.0》——繼解構劇場名作、影史經典和世界名畫之後,這一次他選擇“注解”德國哲學家、思想家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著作。為其編劇的馬楚怡,恰是4年前參演《茶館2.0》的一名素人中學生,如今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并開始在戲劇圈嶄露頭角。
馬楚怡告訴南都記者,《存在與時間2.0》起源于王翀說,想做一部“一個觀衆的戲”。一群戲劇朋友在一起頭腦風暴,決定把這部“腦洞之作”打造成“一個演員和一個觀衆之間的對話”,而她作為編劇就要開始考慮,怎樣的故事内容恰好能适配這種演出形式。今年10月1日至10日,該劇在廣州連演40場,也因為“每場僅限1名觀衆”而備受矚目。
2021年10月首演于廣州的《存在與時間2.0》。
“你要說我真的是對海德格爾特别感興趣嗎?确實感興趣,但那是次要的。”王翀說。從他的角度,這部戲的重點還是在于觀演關系的實驗。但在創排過程中,最初設想的“演員與觀衆1對1”變成了“8對1”,王翀也對自己的過去、當下和未來進行了檢視,在結尾處設定了一段直擊心靈的“拷問”。他向南都記者坦言,那段群戲也反映出了他的心境:“我39歲了,我也迷茫,也在一個微妙的‘坎兒’上,其實很多東西就是我想問自己、我想對自己說的。”
轉過年來,王翀就要迎來“四十不惑”,在某種危機感的驅使之下,他開始了一系列改變:“開始用微信了,然後’停電亭’也賣了,現在是跟家人一起住,而且我開始養貓了……這些都是發生在今年的事情。”
“停電亭”原是王翀在北京鬧市的小根據地,裝修時特意沒有鋪設電線,客人身上的電子裝置也不得進門,必須留在門外的保險櫃,夜晚全屋需要用蠟燭照明。這種“行為藝術”般的規則,對很多朋友來說是一種新奇的體驗,王翀本人則是從2017年堅持到了2021年。其間,他幾乎不用手機,微網誌完全停更,隻用一個iPad回郵件,擷取必要的新聞就靠他人轉述。他曾說,這樣做的目的在于挽救渙散的注意力,特别是對他想做的關于“當下”的戲劇而言,精神的集中至關重要。或許是疫情動搖了這種穩态,大約在《存在與時間2.0》啟動之後,王翀才開始用微信與外界溝通。
獨立戲劇人的經濟狀況常常令劇迷們憂心,事實上他們的創作資金或來自投資人,或源于藝術機構的委約項目。與商業上極其成功的舞台作品相比,可以感覺到的是,他們的劇作通常不會有繁複的舞美。王翀承認:“有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追求一種樸素的美,或者說基于極簡基礎之上的美;至于說(借助商業的力量)發展壯大,其實也做出過嘗試,但是可能就不是那種人吧,确實還是一個‘作品思路’,或者說‘藝術宣言的思路’,甚至是‘梵高思路’。”然而繁複的舞美細節,一定勝過簡約和想象力嗎?在王翀看來,或許未必。
“我們在創作的時候,經常想象有‘戲劇之神’在天上俯瞰,‘她’是一個類似公理的存在,可以去評判什麼樣的戲劇藝術是值得的、有意義的、真正有新意的。”王翀認為面對‘她’來進行戲劇創作,這樣的描述,能夠準确傳遞出自己的創作态度。
“我做了‘一個觀衆的戲’,在未來還希望做‘沒有觀衆的戲’,其實是對‘戲劇的儀式性’進行一次極端的嘗試……”談到感興趣的探索方向,王翀變得有些滔滔不絕,不過他又笑道,“這些都是狂野的想法。也許明年就實作了,也許10年之後才會實作。”
出品:南都即時
采寫:南都記者 侯婧婧
劇照由佛山大劇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