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31 1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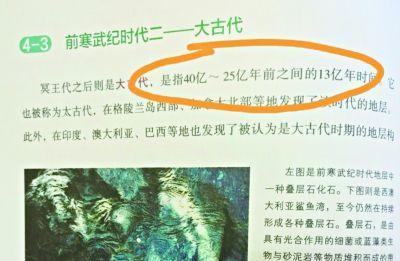
對于“大古代”表述的明顯錯誤。
書中将“知識”寫成了“隻是”。
此頁圖書關于“糖果蝸牛”的表述有誤。
伴随持續性的教學内容調整,義務教育階段閱讀占據着愈發重要的比例。自秋季新學期開學以來,書店櫃台前湧動着為孩子選書的家長,以及自己挑書的中國小生。圖文并茂、新奇好看的科普圖書,一向是捕獲少兒“芳心”的“熱門選手”。在趣味中汲取知識養分的同時,人們也期待,這份營養能更加“純淨無瑕”。
調查
知識錯誤不少 低級錯誤真礙眼
不久前,北京農學院碩士研究所學生雷廣元無意間翻看朋友的《我們愛科學》雜志,2019年6月(下)那一期中,幾頁關于蝸牛的知識引起了他的興趣。
受所學專業影響,雷廣元有個相對小衆的愛好,特别喜歡蝸牛、貝殼,在這方面也研究頗深。而這随手一翻他就發現,介紹珍稀品種糖果蝸牛的内容出現了錯誤。
在這一頁共有上中下三張圖檔。中部一張色彩斑斓的圖檔配文是,“仔細看,這隻是普通的蝸牛殼被塗成了彩色,并不是真正的糖果蝸牛殼,因為糖果蝸牛殼的形狀是錐形的。”
事實上,雷廣元發現配文中“普通蝸牛殼被塗了色”的表述有誤,它們其實就是真正的糖果蝸牛,隻不過來自Polymita屬,産地隻有古巴,故又被稱作“古巴糖果蝸牛”。為了進一步證明,他還發來朋友在當地拍的生态照以及收藏的标本圖檔作為說明。
“平時這些方面的書,我大多是看國外的,因為國内的書錯誤比較多。”說着,雷廣元又翻開一本《世界名貝鑒賞圖譜》,其中一頁的葡萄巢螺和間布巢螺,以及另外一頁的黃雙旋蝸牛,栖息地都被描述為“栖于海底草叢中”。而兩種螺的栖息地應該是在樹幹或者石頭上,蝸牛的栖息地應該是在樹葉枝幹上,相當于這三處資訊都錯了。
除了這種顯得有些專業的内容差錯,網絡上人們曬出的科普書“低級錯誤”更比比皆是。例如一張《貓科動物》的内頁照片中,“動物知識小錦囊”的“知識”寫成了“隻是”。該網友怒問,“130頁到150頁所有‘知識’都寫成了‘隻是’,這麼貴的書,全彩,就犯這麼低級的錯誤?”《地球⋅生命——138億年的進化》一書中,更有“大古代,是指40億——5億年前之間13億年時間”的表述。還有網友曬出孩子正看的一套科普書,其中一本福鳄的配圖解說,和另一本中巨沙螽的配圖解說一模一樣,一看就是複制粘貼的。
質疑
編輯校對挖坑 家長“掃雷”成難點
王府井書店三層,一道道弧形線條勾勒出明亮活潑的閱讀空間。這一層圖書主要面向少年兒童,按年齡段和大緻内容劃分為幼兒啟蒙、少兒百科等多個區域。無論哪個區域,科普書都被放在較為醒目的位置,吸引到不少孩子興緻勃勃翻閱着心儀主題。
“小朋友,幫我看看,這個書你喜歡嗎?”一位從秦皇島來京出差的老先生,回程前特意到書店,想給自己的小孫女帶上幾本書。他拿着一本昆蟲翻翻書詢問旁邊和自己孫女年紀相仿、正津津有味看着“揭秘汽車”的小男孩。
“喜歡!”孩子饒有興緻撥弄了幾下書頁中的立體昆蟲,回答得很幹脆。“這書可挺貴。”一旁的孩子媽媽插話,果然,封底價格赫然逼近百元大關。“現在小孩書做得都可精美了,各種立體插圖、機關,價格也就上去了。”感慨圖書“迷人外表”的同時,這位媽媽表示,選書會看重孩子是否感興趣,确實不太能夠留意到裡面的問題。“錯别字之類的我還能發現,像他喜歡的車啊、恐龍那些,知識點寫錯的話,我也看不出來啊!”
對科普書内容錯誤的識别,是家長們共同的“難點”,也最受争議。有細心網友在微網誌中曬出《拉魯斯趣味科學館》之《神奇的自然》一書,稱“一出現鳥名就瞎翻譯,前後錯誤還不對應。”科普作者三蝶紀轉發表示,“家長們注意掃雷。随便看了下,單是海鹦就出現了‘大喙海鴨’和‘紅嘴鷗’兩種翻譯,編輯校對都不及格。”
還有家長拍下科普書的内容,向“恐龍博士”邢立達詢問,書裡介紹巴洛龍又叫迷惑龍,但是《恐龍王國大百科》裡說雷龍才是迷惑龍,請問迷惑龍到底是雷龍還是巴洛龍?邢立達回複,巴洛龍是重龍“Barosaurus”的錯誤翻譯,雷龍是“Brontosaurus”,可能都是B開頭,作者就錯把重龍當作了雷龍。
“這書我家也有”、“中招了”、“小朋友天天帶去幼稚園看”……多條類似微網誌下,都有大量評論。家長們認為,“小孩記東西可清楚了!科普書更應做好編校把關工作。”
建議
杜絕剪刀糨糊 科學家應做“元科普”
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副秘書長、中國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志敏長期對科普讀物保持着高度關注。在她看來,科普圖書出現錯誤有多種原因。如創作者引用了錯誤的資料,講了錯誤的觀點;彙編的圖書,可能因編寫者缺乏相關素養,不同資訊之間的比對性沒有掌握好;以及排版過程中發生纰漏等。
而圖書出版前,還要由出版社做最終的品質審查,其中就包括對科學性的審查。若圖書仍存在錯誤,歸根結底,與品質審查時“沒看出來”脫不開幹系。
中國科普作家協會設有一項“優秀科普作品獎”,是國内科普創作領域的最高專業獎。該獎項對圖書類的評選,征集管道之一是由省一級科普作家協會、全國的出版社來推薦作品。報送到協會後,由不同學科背景的專家進行分組評審,經初審、終審、終評會等環節來确定獲獎作品。其中科學性是最重要的,還有排版品質,内容是否有趣好看等多種考量。
評審過程中,專家确實見到過交上來的作品中出現錯誤。一想到它們是各大出版社奔着得獎“優中選優”報送的,評審卻一下子就發現了錯,心裡也免不了默默歎氣——會疑惑之前的“把關”是怎麼做的,同時也覺得有些無奈,因為這是整個出版行業的監管問題。另外,市場上不乏評審時發現了問題,但賣得還不錯的科普書。例如編校方面出現錯誤、關于科學的謠言混入書中,以及暫時沒有定論的事情,将其寫得很确定,也不符合科學精神。
“科學家、科研人員親自來做科普,肯定是最理想的。”對科普作品的科學性,要求再高也不為過,而“由專業人員創作”,則被業内普遍視作保證科普作品品質的好辦法。我國天文學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老先生,出版了數百萬字的科普作品,早年間他就曾表示,在整個科學傳播中,科學家乃是無可替代的“發球員”。近年來更提倡科學家要做“元科普”,提供權威、準确的“一手材料”。
事實上,茅以升、賈祖璋、高士其等老一輩科學家,都曾寫過科普文章。但後來因為科研人員壓力大,可能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科普。而非專業人士來做科普,情況就十分複雜了。畢竟科普作品可以給進階知識分子看,也可以給兩三歲的幼兒看。不同程度存在急功近利、粗制濫造、“剪刀加糨糊”複制粘貼的情況。
目前,亞馬遜、當當等平台圖書售賣排名前十的科普書,還是以引進圖書為主,據張志敏觀察,已經有個好的趨勢在悄然出現——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一線科研人員對科普創作又活躍起來。“例如中國古動物館館長王原,還有鄭永春、張勁碩、李淼等很多科學家,他們去寫科普書,科學性上出問題的可能性會更小。”
此外,伴随新媒體蓬勃發展,科研人士在網上寫文章、做公号,進而參與到線下活動之中,有更多管道來普及科學知識。“當然現在也不能說科學家成了做科普的主流,隻能說有更多的人在關注、參與。那麼科普作品的科學性,應該是向好的方向去發展。”本報記者 魏婧 文并圖
責編:李昔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