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相親文學的扛鼎之作、谷崎潤一郎的《細雪》,是這麼開頭的:樓下,雪子正陪着悅子練琴。樓上,幸子在梳妝打扮,看到妙子經過,把她喊住,讓她幫忙敷粉。妙子剛起手,兩人的話題就迅速切換到了八卦雪子新近的相親對象上,随之而來的,是一系列一發入魂、直擊心靈的追問:做什麼工作的?機關好不好?工資多少啦?哪裡畢業的?什麼家庭背景?有多少财産?為什麼到現在還不結婚?——還有最重要的,照片有伐?
大齡女青年雪子的嫁人問題,就這麼赤裸裸地被擺上了台面,更重要的是,以這三言兩語間的問答與評點,谷崎潤一郎輕巧地點出了莳岡氏在嫁(mài)女兒時的顧慮與算計。在某種意義上,厚厚三卷的《細雪》,正是借由對這些問題的反複權衡取舍,展現出了一個衰落中的關西望族在動蕩的社會中如何不斷重新調試、定位自身,以及這些定位背後的沖突、無奈與妥協。
不過,開篇這一幕并未就此結束。谷崎筆鋒一轉,帶出了一個貌似可有可無的小細節。幸子畫完妝,突然想起來件事兒,便囑咐妙子道:
“哎對了,我又‘缺B’了,麻煩你下樓去吩咐一聲,讓誰把注射器消消毒。”
腳氣可以說是阪神地區的一種地方病,也許由于這個緣故,這一家人從當家的兩口子到剛上國小一年級的悅子,每年夏秋兩季都鬧腳氣,注射維生素B就成了習慣。近來連醫生那兒也不去了,家裡常備有高效維生素注射劑,連沒有什麼毛病的時候也互相打針。隻要什麼地方有點兒不舒服,就歸之于缺少維生素B。也不知是誰先說開的,碰到這種情況,就稱之為“缺B”。
“缺B”這個症狀,幾乎貫穿全書,一家人把注射維生素當習慣,有事兒沒事兒就掏出針筒互相打,動作還相當熟練,先“用砂輪劃斷瓶頸,把藥水吸進注射器”,拉過手臂,“用蘸着酒精的脫脂棉”擦一擦,一下把針頭紮進去,完了還要“貼上膠布,在進針處又拍又揉,使肌肉松弛下來”這才算完成了全套。至于打針的原因,治療腳氣病當然是最常見的原因,但“沒有什麼毛病的時候”也沒停過,用叙事者的話說,“姐妹們互相打針幾乎成了她們的日課”。妙子病了,要注射維他命以助康複。悅子晚上失眠睡不着,幸子上手就給她來了一針。天熱,三姐妹胃口不好,于是互相打針。雪子想要消除自己眼皮上的那塊褐色斑,于是每隔一天要打一針維生素。三姐妹準備去聽音樂會,出門前商量着穿什麼衣服,差點誤了時間,而就在這當口,還要擠出時間來打一針。對于她們來說,維生素仿佛成了所有健康問題的萬靈藥。——問題是,為什麼?這些關于維生素的細節,對于谷崎潤一郎的叙事而言起到什麼作用?它的重要性從何而來?在當時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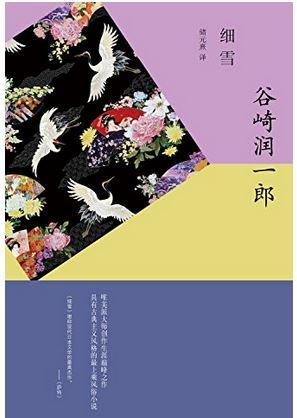
谷崎潤一郎《細雪》
在《秘窗》中,安東尼·錢伯斯将谷崎潤一郎叙事中的維生素與疾病關聯了起來,而後者則可以被視為家族衰落的一個标志。錢伯斯寫道,“疾病指向了凋零與衰亡,并為讀者提示着小說諸角色的身體的脆弱性,同時,疾病也表征着那種貫穿全書的焦慮感”。這種關于衰亡的焦慮感絕不僅限于莳岡家族之内。錢伯斯特意提醒我們,《細雪》全書故事的時間始于1936年11月,終于1941年4月,而此時“離珍珠港事件還剩不到八個月,而離東京第一次被轟炸隻剩不到一年”。在這個意義上,借由衰亡這一概念,錢伯斯在小說中的維生素/疾病,和小說所處的曆史與政治語境之間,建立起了某種模糊的關聯。
然而,維生素與日本殖民戰争之間的曆史聯系,要比錢伯斯的論述直接得多,它不僅在日本軍國主義話語及其身體政治中占據着重要位置,對維生素的消費,也貫穿着整個殖民時期的内部改造與對外征伐。事實上,随着現代營養科學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滲透,維生素早已不僅是一種特定的營養品,在大衆媒體中,它已然成為健康本身的象征符号。而健康的國民,則是帝國的殖民宣傳所念茲在茲的核心問題。舉例而言,1941年,綠旗聯盟——這一組織原先是一個佛學研究小組,後來則慢慢成為殖民政府宣傳國家意識形态時的重要合作者——出版了《家庭食事讀本》,此書以普通的家庭婦女為對象,意在指導她們如何去建立一個理想的家庭。《讀本》中專門辟出一章讨論主食,并極力強調維生素B的重要性:它指出,自1899年起,由于缺乏維生素B而造成的腳氣病所帶來的死亡率正逐年上升。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此書建議家庭主婦們将精米與雜糧相混合。尤其是對那些以外國大米,也即從泰國和越南進口的大米為主食的家庭來說,主婦應當将這些米與麥子或豆類相混合,因為,與“内地米”(即産于日本本土的大米)相比,進口大米被認為缺乏維生素B。
更關鍵的問題在于,這些建議并非是從提升個體健康水準的角度作出的,事實上,它們深刻地契入了日本當時的帝國主義擴張程序。《讀本》繼續寫道,作為一個擁有進階軍事防禦力量的國家,日本立志達成食品供給方面的自給自足,“但今日,我們正緻力于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進而不得不從外國進口大米與谷子。是以,普通日本人應該認識到食用外國米的價值所在,補充它的不足之處,并且抛開抱怨之情。
為了應對殖民戰争所導緻的糧食短缺,日本政府試圖通過宣傳手段來修正普通日本家庭的日常食譜,這種新的食譜被認定為“國民食”,并在整個帝國範圍内得以推廣,其目的無非是糧食短缺的前提下,以普通國民的餐食為代價,為前線的軍隊榨取更多糧食供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維生素作為膳食營養的替代品,被納入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宏大叙事中,成為日本殖民擴張的有機組成部分。用海倫·李的話說,它“不僅滋養了人體,更滋養了對帝國的忠誠與奉獻”。
谷崎潤一郎
國家對個人身體健康的關注貫穿了整個戰争時期。薩賓·弗呂史蒂克曾指出,兒童的“身體建設”在明治時期就被認為是“帝國建設”的手段與前提,并是以被納入了國家的直接保護與指導之下。在此原則上建立的體制被弗呂史蒂克稱為“現代的健康政制”(modern health regime)。而到了1930年代末期以及1940年代,這一體系的控制愈發嚴格。1938年,厚生省在東京成立,從此,對國民健康與衛生的管控被納入政府的制度化工作。以日軍軍裝為模闆制作的著名的戰時“國民服”正是由厚生省出台推廣的。可以說,随着戰争的日漸深入,對普通國民身體健康與衛生的管控,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并且影響、改造着人們的日常行為邏輯。《細雪》第1卷第24章,幸子的丈夫貞之助注意到了莳岡家姐妹們對于衛生問題的過度關注,“比如吃飯時筷子一遍又一遍地用開水消毒,掉在桌布上的東西不肯吃,這都是幸子和雪子的作風”,而這種作風已經傳染到了女兒悅子身上:
貞之助一向采取放任主義,特别在女兒的教育問題上,他一切聽憑孩子母親的教育方針。最近由于“支那事變”的發展,有朝一日可能要讓婦女參加戰事的後勤工作,考慮到這一點,他擔心今後如果不把女子培養得剛健一些,恐怕什麼事也幹不了。有一次,他無意之間看到悅子在和阿花玩“過家家”,悅子拿來一個打針的舊針頭,紮進稻草做芯子的洋娃娃的胳膊。他想這種遊戲多麼不健康,覺得這也是那種衛生教育的餘毒,今後必須設法加以糾正。
由“支那事變”而來的關于“衛生教育”的焦慮與實踐,正是“健康政制”有效運作的産物。有趣的是,培養剛健的、能夠從事戰争後勤工作的婦女,恰恰要求她們能夠掌握皮下注射的技能,正是這種知識與技能的習得,将女性的身體轉化為帝國事業的一部分,而投入到包括“支那事變”在内的殖民戰争機器的運轉中去。事實上,在整個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婦女的身體始終是國家關于國民責任與義務的宣傳運動以及政策頒布的焦點之一。所謂理想婦女的形象,已從明治時期的“良妻賢母”,慢慢被修正為衛生的、健康的婦女。
而一個健康婦女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她能夠生出一個健康的孩子。由于殖民戰争所導緻的人力資源的極度匮乏,使得女性的子宮成為國家的珍貴資源,堕胎行為是以被嚴格地控制起來。《細雪》第三部裡,妙子未婚先孕,幸子本想說服她去堕胎,但很快放棄了這個念頭:“再說在兩三年以前,任何醫生都很容易接受這種手術。可是近來的社會形勢對于這種事情越來越嚴格,是以今天即使妙子答應做人工流産,也不是輕易就能做到的。既然這樣的話,另外能做得到的辦法就隻有暫時讓她躲藏在一個見不到熟人的地方,讓她在那裡分娩。”在這裡所提到的“社會形勢”,恰是前文所提及的殖民時期對女性身體的嚴格管控,在這裡,健康政制已然被内化為莳岡一家在作出決策時的思維傾向,并成為推動叙事前進的看不見的手。
對女性生育的幹涉絕不僅限于堕胎,在《新女性》這樣的婦女雜志上,女性的生殖健康與個人衛生成為各路政治與商業宣傳的鹄的,從防止早産與流産的維生素E補劑,到促進胎兒發育的各類藥物,幾乎涵蓋了女性生育的全過程。重要的是,這種宣傳廣告的用語與修辭極其政治化與軍事化。其中一則鼓勵婦女生育的廣告大聲疾呼:“敵機已經布滿了廣闊的天空!/我們在南部戰鬥的戰士們歎着氣如此說道。/我們如何回答他們的聲音?/我們必須盡快将挂着日本國旗的飛機送上天空。/我們必須培養出更多的能夠駕駛飛機的孩子。/你是否還有尚未捐出的鋼鐵?/是否還過着阻礙軍力發展的生活方式?/提高生育率!前進吧軍隊!/是時候動員起百萬大軍了!”在這則宣傳的同一頁所刊載的嬰兒營養品廣告則宣稱,“健康的國家與強大的軍隊始于賢良的母親”。兩則廣告間的互相呼應,将女性身體牢牢釘在了戰争機器中,假如前方制作飛機所用的鋼鐵,與後方制造戰士所用的子宮能夠等量齊觀,那麼,滋養女性身體的維生素藥劑,便可以如駕駛飛機所需的燃油一樣,能夠被收歸改造為殖民事業的資源與武器。
路易斯·楊曾指出,日本全國上下的戰争狂熱恰與當時急劇擴張的大衆媒體市場互為表裡。一方面,《新女性》這樣的雜志證明了對健康、完美的女性身體的宣傳與追求,與當時的殖民話語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另一方面,大衆媒體上的類似宣傳,亦将日本本土國民的日常生活轉化成了意識形态戰争的戰場。在《細雪》中,雪子眼皮處的褐色斑始終困擾着她,成為她相親之路上的一塊心病。為了去除這塊褐色斑,雪子不得不定期去注射女性荷爾蒙以及維生素C針劑。有趣的是,這個辦法正是妙子與幸子在一份“婦女雜志”上發現的。我們當然無法确知妙子與幸子所看的是哪一份“婦女雜志”,但至少我們已然知曉當時的婦女雜志對修複“不健康”的女性抱有多大的熱情,以及這種熱情的部分來源。尤其是尚未結婚的女性,她們猶如“一件等着出售的商品”,應當具有完美的身體,而這不僅源于婚戀市場的壓力,更是健康政制的要求。
假如我們将《細雪》放在殖民時期帝國對女性身體健康及家庭責任的宣揚與管理的語境中,會發現莳岡家的日常行為方式與思維與當時的意識形态宣教幾乎嚴絲合縫:互相注射維生素的家庭習慣、對悅子的衛生教育、幸子與妙子對堕胎的顧慮、雪子對自身健康的焦慮(主動照X光片排除肺病隐患、遵從婦女雜志的建議去除褐色斑、習慣性地注射維生素等),諸如此類。随着雪子的相親曆程的展開,她也似乎一步步地将自身改造成了合格、健康的預備役妻子及母親。
1943年,《細雪》在《中央公論》上剛剛連載了兩期,便因為其中所描寫的“陰柔、綿軟、極端個人主義的婦女生活”與當時高亢、陽剛的軍國主義宣傳基調不符而被禁。然而,軍國主義自身卻未有片刻将婦女生活置于自身視野之外。《細雪》這部以“缺B”開頭的作品中這些關于健康、疾病與女性身體的細節,恰在有意無意間洩露出了殖民話語及其健康政制的蛛絲馬迹。在小說末尾,雪子終于敲定了婚姻問題,然而就在婚禮之前幾天,她突然毫無來由地開始拉肚子,且不論吃什麼藥都無法見效,直到坐上趕赴婚禮的列車也還是如此,小說最後一句,谷崎如此寫道:“那天雪子拉肚子始終沒有好,坐上火車還在拉。”
在健康政制的語境中,故事的這個結尾顯得微妙而有趣。它是在召喚進一步的治療,還是在質疑一個永遠健康完美的女性身體本身的可能性?疾病是否構成對于某種現代規訓的抵抗,或至少是偏移?個人身體與帝國殖民事業之間的和諧,是否在根本上是無法實作的?這些問題,絕不意味着将《細雪》視為一部政治小說。或者應該說,正是因為《細雪》不是一部政治小說,上述的瑣碎細節才更顯其意味深長。更重要的是,即便抛開所有這些論述,雪子的相親曆程本身,也已經留下足夠振聾發聩的追問:
做什麼工作的?機關好不好?工資多少啦?哪裡畢業的?什麼家庭背景?有多少财産?為什麼到現在還不結婚?——還有最重要的,照片有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