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英) 瑪麗·比爾德
譯者丨王迪
摘編丨董牧孜
羅馬人發明了笑話?
這個世界上并不存在“第一個笑話”這一說(甚至在西方世界的小範圍内也是如此)。任何有關“笑話”肇始于何處的說法都會在面對定義的問題時土崩瓦解。笑話和其他口頭上的逗樂究竟有何不同?一句诙諧的格言、一個寓言或是一句雙關能算作笑話嗎?如果笑和人類本身一樣古老的話,那我們能否想象在人際溝通的曆史上,笑曾經并不是由語言引發的?
不過,當革拉西穆斯出現在台上,聲稱自己要售賣笑話和笑話書來換得一頓美味的晚餐時,我們便已經處在一個特色鮮明、一目了然的玩笑世界裡了。這裡的笑話成了某種商品。盡管這一幕本身就是一個笑話,但革拉西穆斯的插科打诨仍然有價值。它們在一個交換的體系中發揮着作用。這些事物的存在獨立于這位弄臣;而在薩圖裡奧的故事裡,它們甚至還可以一代代地傳下來。同時,它們也擁有自己的曆史;在泰倫斯的《閹奴》中,特拉索說了一個關于羅得島小子的笑話,從中我們其實可以認識到,一個笑話的曆史既是它主旨的一部分,也構成了它的笑點。
不過,盡管帶有濃重的羅馬喜劇色彩,我們還是從中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識的痕迹。在現代世界裡,笑話往往也是交換體系中的一部分。我們是會交換笑話的。我們會像比賽似的講着笑話。對于我們而言,它們也可以是擁有譜系和價值的商品。有些人甚至靠賣段子給廣播台和電視台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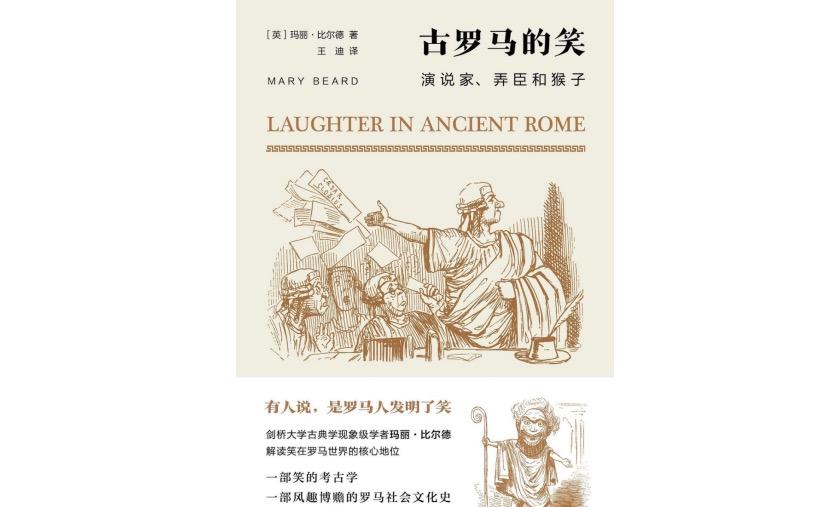
《古羅馬的笑:演說家、弄臣和猴子》,(英) 瑪麗·比爾德 著,王迪 譯,新民說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
而在古典和希臘化時代的希臘,這種商品化的迹象遠遠沒那麼多。當然,那個時候的語言和文學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博人一笑;從政治家到哲學家,各式著名人物說出了許多犀利而又有趣的語錄;而且笑話在很多場合中都是備受期待的(吃白食的人靠逗樂飽餐一頓的點子可不是羅馬人首創)。不僅如此,我們間或還會發現一些迹象,表明那時的希臘也有更具一般性、不具姓名的笑話,會讓人聯想到《愛笑人》。
在我們看來,與之最為相近的就是阿裡斯托芬的喜劇《馬蜂》( Wasps )了 。在這出戲末尾的一片喧鬧之中,老菲羅克勒翁(Philocleon)試圖以一種紳士和老練的方式平息事态,故而講述了一個“錫巴裡斯人的故事”,不過結果卻未能如願。這個故事是這樣的:“有個錫巴裡斯人從馬車上掉了下來,腦袋摔得當真不輕。因為其實他駕車的技術并不好。他一個朋友站在一旁,說道:‘沒有金剛鑽,不要攬瓷器活。’”
錫巴裡斯人的故事是古代說教智慧故事中的一個有趣分支,内容說的都是意大利南部城市錫巴裡斯的居民有多愚蠢——這座城市當時出了名的富足,以至于為自己招來了禍端,最終在公元前 6 世紀晚期遭到毀滅。我們對這些故事的了解主要源于羅馬時期作家的引述,而且它們往往被歸為寓言一類——阿裡斯托芬在這部戲前面的叙述中就是這麼做的(“伊索筆下的趣事或是一個錫巴裡斯人的故事”)。故事中那個姓名不詳、愚蠢的錫巴裡斯人讓我們不禁會聯想起《愛笑人》中的阿布德拉人、庫邁人和西頓人。
成書于四世紀的《愛笑人》,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一本笑話集。
不過,在古典和希臘化時代的希臘,笑話并不像它們在羅馬或者羅馬世界中那樣被當作可供收集的商品。這種差別在阿忒奈烏斯《哲人燕談錄》中一個講述馬其頓國王腓力的故事中明确展現出來。這部作品用希臘語寫就,成書于2 世紀與 3 世紀之交,是一部長達數卷的傑出巨著,總彙、選編了當時文學與文化的各方面資訊,其作者阿忒奈烏斯來自羅馬的埃及行省。這本書假裝描寫了羅馬一位富有的恩主舉辦的晚宴,晚宴上有許多學識淵博的人談笑風生。他們引經據典,在閑聊間分享各自的學術智慧,令人歎為觀止(不過說實話,有時也很冗長無聊)。
笑話與開玩笑也是阿忒奈烏斯書中的一大主題,而且我前面也已經說到了他記錄下來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素材,包括不能笑的帕耳墨尼斯庫斯的離奇故事。在這場晚宴上有一個叫作烏爾比阿努斯(Ulpian)的羅馬人,他講述了一個腓力國王買笑話的故事,很有啟發性。
烏爾比阿努斯說,在公元前 4 世紀的雅典,有一群機智風趣的人會在城外的一個聖殿裡聚會。這群人總共有六十個人,是以被稱為“六十智者”,他們在逗樂上有着獨特的才能(sophia)。當腓力聽說有這麼一群人之後,就給了他們一大筆錢,想要以此交換他們的笑話(geloia),“他給他們送了一些銀子,這樣這些人就可以把笑話寫下來送給他”。這個故事經常被拿來證明公元前 4 世紀的希臘就有笑話集存在了(正如一位評論家所寫的那樣,這群弄臣就是“那些把‘口頭功夫’變成紙上笑話的人”)。或許乍看起來的确如此。
在撰寫本章的過程中,我才意識到這個故事和它蘊含的寓意其實更有可能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盡管阿忒奈烏斯隻是簡要地概述了這個故事,但他後面緊跟着又講述了幾個故事,說的是“圍城者”德米特裡(Demetrius Poliorcetes)和蘇拉等臭名昭著的獨裁君主對笑的熱衷。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當時的雅典社會,“六十智者”的故事并沒有被看作宣揚文學收藏這種進取精神的正面案例;相反,人們把它視作一個反面的例子,因為這裡面的商品化是颠覆、獨裁式的:腓力是一位擁有财富和權勢的君主,他錯誤地認為自己可以把“六十智者”的風趣以這種友善、便攜、紙面的形式買下來(我們并不知道他們究竟有沒有把笑話寫下來送給腓力)。
羅馬世界則不同。說得再直接一點,玩笑的商品化(形成可以交換、傳襲、收集或買賣的笑話)在這裡并不是獨裁者颠覆式意願的展現;它更像是羅馬的一種文化範式。而展現了這一點的,不隻是革拉西穆斯和羅馬喜劇中出現的其他食客們的逗樂打趣,也不隻是《愛笑人》中收錄的俗語。拉丁語和希臘語單詞之間的顯著差異也讓我們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拉丁語中,可以用于表示笑話的單詞極其豐富(甚至多得幾乎沒有必要);而希臘語則似乎太過重視同笑的動詞與名詞有關的單詞,其geloion 和 skōmma(或許還要算上chreia)的含義在被用來表達各種類型的笑話時遭到了過度延展。
如果僅根據這些顯而易見的迹象,就認定“希臘”和“羅馬”的玩笑文化之間有着鮮明且固定的差異的話,那就把問題過于簡單化了。不過,它們的确說明笑話與開玩笑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坐标,如果我們對此視而不見,則太缺乏責任感和想象力:這其中,我們尤其應該意識到, 在羅馬世界裡,笑話不僅僅是一種互動的形式,同時它本身可以作為一種文化客體或是商品(或者說作為一個名詞,而不是動詞)。
不願冒險的學者可能會按照重點的不同來看待這個問題,這樣一來證據的模式和存在與否可能會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而最大膽的學者則傾向于提出更加激進的主張,他們認為我們現在所謂的“笑話”就起源于羅馬文化,并将其看作羅馬人在西方曆史中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産比他們建造的橋梁和道路都要重要得多。
但是,無論選擇哪個方向,仍然有一個問題讓我們摸不着頭腦:究竟該如何解釋笑話在羅馬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該如何書寫笑的曆史的問題,包括它随時間(和地點) 發生的變化。
有人認為,笑話作為一種商品,與羅馬世界裡保護者和受保護者、富人和窮人之間尖銳的交易關系密切相關;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是不是正是在這種情境下,玩笑才被定義成一種可以交換的物品(同時也作為一種文學互動的模式)?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們或許還會認為,它也是羅馬帝國統治下文化商品化的一大标志。不管是在地中海地區的其他地方還是在羅馬本土。羅馬帝國裡的任何東西都是有标價的。帝國的征服者們購買、複制、交換藝術品,并對它們進行分類和估值。他們對風趣、笑話和玩笑也做了同樣的事。是以難怪,“腓力國王模式”成為羅馬“笑學”中的一大重要組成部分。
好皇帝和壞皇帝
羅馬的專制統治深深地影響着笑(laughter)和玩笑(joke)的文化——這種模式早在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之前便已經出現了。可能兇殘的獨裁者蘇拉現在已經不是名聲最響的那個了,但在公元前 1 世紀 80 年代前,他曾短暫地掌握過權力,其治下的羅馬城堪稱血雨腥風;不過在古典時代,像許多希臘化時期的僭主和統治者一樣,他狂熱地愛笑也是出了名的。是以他和一些弄臣之間的淵源也絕非偶然。在西塞羅和昆體良看來,這些弄臣的诙諧風格是演說家所要避免的。
“他特别喜歡笑劇演員和小醜,是一個很愛笑的人,”公元前 1 世紀晚期的曆史學家、大馬士革的尼古勞斯(Nicolaus of Damascus)這樣寫道,“甚至把許多公有土地都賞給了那些人。他自己用母語(拉丁語)寫了很多聲色犬馬的喜劇,它們能夠清楚地說明他有多享受這些事 物。”普魯塔克也記錄下了這種說法,還表示這位獨裁者“很喜歡笑話” (philoskōmmōn),而且晚宴上的他和其他時候嚴肅的形象判若兩人。就連死之前(按照普魯塔克筆下那個駭人聽聞的故事來看,他的死是因為身體出現潰爛,生了蠕蟲),他都還沉迷于喜劇演員、笑劇演員和模仿者們的表演。
獨裁者和笑之間的某些聯系是可想而知的。在羅馬社會,有一條基本的規律(中世紀“诙諧國王”[rex facetus]的傳統便是從這兒直接流傳下來的):寬厚的明君所開的玩笑也是仁慈的,他們從來不會用笑去羞辱别人,而且還能夠大度地接受取笑他們的俏皮話 ;而另一方面,糟糕的統治者和獨裁者甚至對沒有一絲惡意的打趣也要施以暴力壓制,同時還會把笑和笑話當作對付敵人的武器。許多關于宮廷的笑的轶事都能夠證明這一規律。我們也不知道這些故事是不是真的,而且我們也能看到,有些笑話在這裡說是這個著名的笑匠說的,但在那裡又被說成是出自另一個人之口,這顯然表明我們所了解到的隻是文化定勢,或者是被流傳下來的故事,而不是事實。但它們也指出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既算是一則政治啟示,也是 一個迷思):笑能夠幫助我們鑒别好的統治者和壞的統治者。
狄奧在論及韋帕芗時便利落地總結了這一觀點的一個方面:這位皇帝的風度(civilitas,這裡指将百姓看作同胞而非臣民的優秀品質)展現在“他像普通的百姓(dēmotikōs)一樣開玩笑,能夠欣然接受對自己的打趣,而且每當有人匿名貼出了那種寫給皇帝看的智語,以此侮辱他時, 他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并不會是以而惱火”。
當然,風度一向隻是一種虛飾(皇帝和公民之間是不可能實作真正的平等的,皇帝和平民之間更是如此,像後者這種非精英階層的公民在這些笑話中往往會起到重要作用)。不過,在皇權的複雜鬥争中,這的确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僞裝,而這些鬥争的基本規則早在奧古斯都皇帝治下就形成了。是以,有許多轶事都是圍繞奧古斯都展開的,這些故事中既有得到容忍的笑話,也有讓人們欣然接受的笑話。
建立羅馬帝國的奧古斯都皇帝很有幽默感。
馬克羅比烏斯收集了許多關于奧古斯都妙語如珠、逗樂打趣的故事,從中可以看出這位皇帝是怎麼和手下開玩笑的(比如,當有人猶豫着要不要向他呈遞訴狀,不停重複伸手又收回的動作時,他見了便說道 :“你以為你是要把錢遞給一頭大象嗎?”)。不過,在這些故事中,我們看到他也會容忍那些拿他打趣的俏皮話。在馬克羅比烏斯的《農神節》一 書中,有一個人物這樣說道:“說起奧古斯都,和他說出的那些笑話相比,他容忍下來的笑話更讓我感到吃驚。”
接着,他便引述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一個很出名的笑話,我們發現它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畢竟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到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都在讨論它,而且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羅馬共和國時期。“一個外鄉人編的諷刺笑話(iocus asper) 變得廣為人知。說的是羅馬城裡來了一個人,長得很像奧古斯都皇帝,是以他總是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奧古斯都便下令把那人帶到他面前來。他一看到那人,就問他說:‘年輕人,告訴我,你的母親來過羅馬嗎?’‘沒來過。’那人回答道。但他并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便又接着說道 :‘不過我父親倒是常來。’”要知道,羅馬父系權力的基石就在于父親的身份。 也就是說,奧古斯都竟然連事關此事的玩笑都能夠忍受。
不過,并不是所有的說笑者都有着卑微的出身。有些時候,我們會發現羅馬社會中的上層人士拿來打趣的話也得到了這樣的寬容。在公元 2 世紀初的一樁引人入勝的奇事中,笑話在元老院裡成了一種工具,被用來分寸合宜地諷刺别人。這個故事出自小普林尼的一封信件,它讓我們對一貫莊嚴肅穆的元老院有了全新的認知。盡管寫下這個故事的小普林尼自己并沒有被逗樂。
在那封信中,小普林尼讨論了在元老院選舉中使用不記名投票有哪些明擺着的後果,而且他認為這些後果将是災難性的 :“我跟你說過,”他給收信人寫道,“你應該擔心不記名投票會導緻它們被濫用。好吧,這已經發生了。”他解釋說,在上次選舉中,有人在選票紙上草草地寫了幾個笑話(iocularia),甚至還有污言穢語 ; 其中一張上寫着的是支援者的名字,而不是候選人的名字。可以想見,這些行為都是故意的,隻是為了粗俗地評判獨裁統治下的這種無意義的流程。那些忠誠的元老氣鼓鼓地要求圖拉真(Trajan)皇帝懲罰肇事者,但此人一直聰明地保持低調,是以從來都沒有被發現過。從小普林尼信中的内容來看,圖拉真對這種現象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并沒有采取行動。小普林尼還提到,當其中一些比較古闆的旁觀者感到失望時,其他人則會祝賀皇帝表現出了極佳的風度。
通過他們笑和開玩笑的風格,“壞”皇帝同樣暴露無遺。從卡利古拉到圖密善(Domitian)再到埃拉伽巴路斯,古時的人說起這些高居皇位的“惡魔”時,總是會一遍遍地借由笑以及對其規則、傳統的僭越,來定義和衡量不同形式的殘酷和暴行。這和風度正好相反。在有些故事中,皇帝們忍受不了拿自己逗樂的笑話。比如,羅馬的競技場裡有一群水兵,平日裡的工作是看管那些用來給競技場遮陰的巨型遮篷。據說,如果康茂德覺得觀衆中有誰在笑他的話,就會指令這些水兵取了那人的性命(難怪狄奧那麼擔心自己會大笑出來)。而另一些故事則說的是 皇帝們會以錯誤的方式,在錯誤的場合,或者對着不合宜的事物大笑起來,又或者他們會說一些殘酷(或者單純隻是十分糟糕)的笑話供自己取樂。
說到克勞狄,他的俏皮話都不太好笑,或者說有點“冷”(frigidus): 他曾用一個叫帕倫布斯(Palumbus)的角鬥士的名字說了個雙關的笑話,因為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斑尾林鴿”(當人們喊着要帕倫布斯上場時,克勞狄承諾“如果他被逮住了”就讓他上場),而蘇維托尼烏斯對這個笑話并不感冒。卡利古拉的笑話倒不是冷,而是充滿了咄咄逼人的威脅意味。“在他舉辦的一次極為奢侈的宴會上,”蘇維托尼烏斯寫道,“他突然狂笑起來(in cachinnos)。他兩旁的執政官禮貌地詢問他這是在笑什麼。‘沒什麼,不過是想到我隻要一點頭,你們兩個就會立馬人頭落地而已。’”而在《羅馬君王傳》中,康茂德的傳記作者則清楚地寫道,“他的笑話也都是要人命的”(in iocis quoque perniciosus),接着講述了一個可怕的故事:有個男人的一頭黑發中夾雜了些許白發,這個皇帝就在他頭上放了一隻椋鳥;這隻鳥開始啄那些白頭發,以為那些頭發是蟲子,這使得那個男人的頭皮開始發膿潰爛,想必最終還要了他的性命。
《羅馬君王傳》,[古羅馬]埃利烏斯·斯巴提亞努斯 著,謝品巍 譯,啟真館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
這個故事也呼應了《埃拉伽巴路斯傳》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 : 獨裁者的笑話的确是會要人命的。不過,這并不是全部。在這部半真半假的傳記裡,康茂德的惡作劇也效仿了戲耍白發或秃頭之人的一整套帝國傳統。皇帝們在愚弄别人時,一個最常見的主題便是那人腦袋的狀态:尤利烏斯·恺撒就因為秃頭多次被嘲笑過,據說他把剩下的頭發全部往前梳,好蓋住秃掉的部位(這種做法很早就有了,而且也早就成了人們進一步嘲笑的對象);圖密善(即“秃頂尼祿”)也把别人打趣他秃頭的做法看作侮辱。
不過,我們前面說到了康茂德的故事,他的做法顯然借鑒了馬克羅比烏斯的記錄中奧古斯都對女兒朱莉娅開的玩笑。傳說朱莉娅很擔心自己頭上的白發,是以她會讓女仆把那些白發拔出來。一天,奧古斯都來看她,在那之前她已經讓仆人把白發都拔了。“奧古斯都裝作沒有看見朱莉娅衣服上落着的白發......問她等到幾年之後,她是更願意秃着,還是滿頭白發。朱莉娅回答道:‘父親,就我個人而言, 我更願意長着一頭白發。’他便指責女兒說了謊:‘那麼,為什麼要讓這些女人把你這麼快就變成秃子呢?’”
這裡有一個很鮮明的對比。明君奧古斯都用開玩笑的口吻,數落自己的女兒為什麼要把白頭發給拔出來。而暴君康茂德卻把一隻鳥放在無辜之人的頭頂上,讓它去啄那人的頭發——甚至還讓那人是以喪了命。
《羅馬君王傳》中記載的這些過于誇張的傳說所具有的曆史意義,往往比表面看起來的更大。因為其中不單單有憑空編造的内容,還有對羅馬社會中一些傳統問題的荒誕化誇張。我認為,羅馬社會中的獨裁統治有一個讓人膽寒的後果,那就是專制君主能夠讓他的玩笑(可怕而又意外地)變成現實。
不過,說起皇帝們的笑,他們最鮮明的優勢并不在于控制自己的笑或者開玩笑的能力,而是展現在他們嘗試控制其他人笑或者開玩笑。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卡利古拉在自己的妹妹德魯西拉(Drusilla)去世之後,便下達了一項專橫的禁令,讓所有人都不準笑。據蘇維托尼烏斯 描述,卡利古拉下令,在哀悼德魯西拉期間,任何人都不得大笑、洗浴 或者和家人一起進餐(這是三項重要的“正常”社會活動,并且蘇維托尼烏斯把“笑”放在了第一位),否則便會以死論處。這個規定雖然不能說執行不了,但顯然也沒什麼結果,而且(不管事實如何)正因如此才被收錄到了傳記之中。不過,還有其他一些與之相似的或成功或失敗、或真實或虛構的專橫行為,它們的目的都是左右自然的力量:就像薛西 斯(Xerxes)下令建橋橫跨赫勒斯滂海峽一樣,卡利古拉也想要征服臣民們的笑這種自然力量(隻不過範圍限于他的國家之内)。
如果說“笑”是最不可控的一種身體反應的話,那麼它恰恰(或者說正因如此)就是皇帝們想要掌控的對象,隻不過有些皇帝比其他人要稍微溫和、收斂一些。換言之,在帝國統治的文學體系中,皇帝對笑的管控可能是一個清晰的政治符号,象征着專制制度的“非自然性”,即使它們的形式再溫和也依然如此。
(本文摘編自《古羅馬的笑:演說家、弄臣和猴子》一書,由出版社授權轉載。)
原作者丨(英) 瑪麗·比爾德 譯者丨王迪
摘編及編輯丨董牧孜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