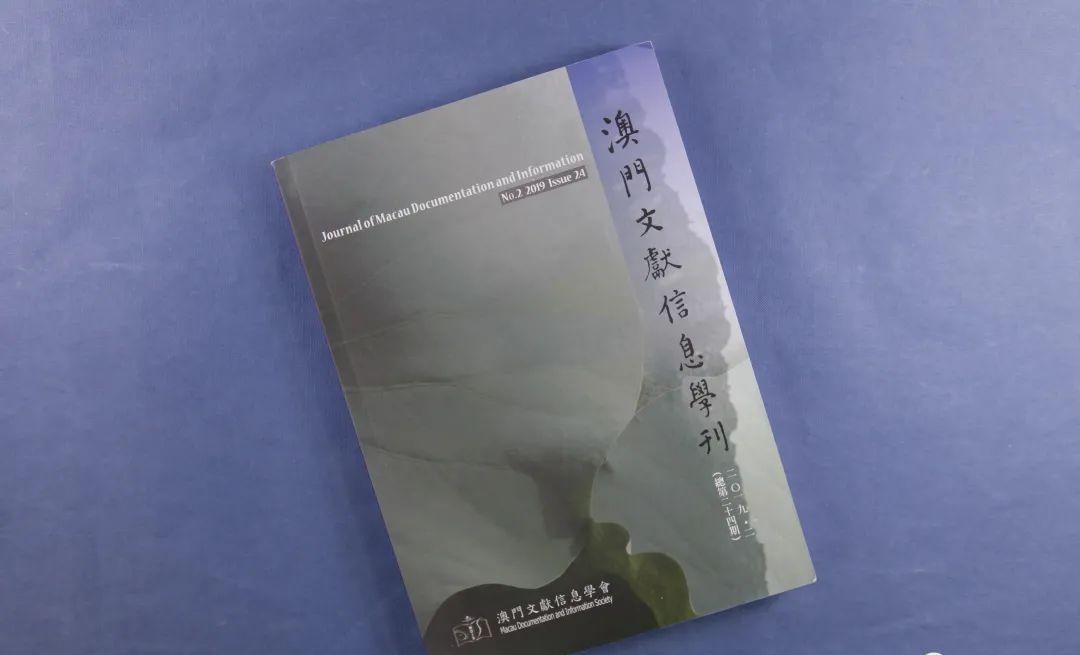
《澳門文獻資訊學刊》,總第二十四、二十五期,鄧俊捷主編
澳門文獻資訊學會2019年12月、2020年6月出版
兩期學刊同時收到,均為鄧俊捷先生所贈,并且兩期都有我喜歡讀的文章。比如第二十四期中有王傳龍所撰《古籍登記中的“闆裂聯系法”》。文中談到目前國内各大圖書館在登記線裝古籍的版本時,對于版本項的著錄主要依據封面頁、牌記、序跋、堂号、印章等項,如果這些項缺失,才會花時間核對其他版本,而核對方法主要是比對存有上述出版項的版本。王傳龍指出了這種著錄方式的弊端,舉出了乾隆三十七年葉氏海錄軒朱墨套印本《文選》至少有十幾個翻刻本的問題,汲古閣刊刻的《十七史》,其翻刻本也同樣有“汲古閣”及“毛氏正本”字樣。
傳統的版本鑒定,除了上述依據外,主要是通過字型、名家藏印以及紙張綜合考量,該文中分别指出了每一種鑒定方法的不足,而後提出他所發明的“闆裂聯系法”,稱這種鑒定方式是受甲骨文蔔辭鑒定的影響,當年郭沫若、董作賓等人就是通過甲骨文中的地名、幹支、貞人等項,對甲骨進行分類,同一類的甲骨大緻為同一時期的産物,或者出土于同一地點。
王傳龍認為,中國線裝古籍絕大部分為雕版印刷品,闆片在使用過程中逐漸出現裂痕,按照刷印時間的先後排序,越早刷印的闆裂越少,而闆裂乃是雕版自身所具有的實體特征,“凡具有相同闆裂之版本,則必然出于同一源頭”,即便是初刻初印本,雖然沒有闆裂,但會有欄線上的細小缺口,個别字形上的筆畫缺失等,同樣可以使用闆裂聯系法。
其實,在版本的鑒别過程中,這種方法早已被業界所熟用,以往用這種辦法一是用來鑒定某部線裝書是活字本還是雕版本,因為前者不會有闆裂問題,二者則是用闆裂來鑒定某部書屬于某版,隻是這種鑒定方式大多停留在經驗總結方面,而将其進行疏理,行諸成文,王傳龍先生的這篇文章乃是我看到的第一篇。
第二十四期中還有胡善兵所撰《民國詞人喬大壯書信六通柬釋》。該文先介紹了喬大壯的生平,以往我主要是關注他在篆刻上的成就,因其印譜頗受市場追捧,讀完此文,我方留意到喬大壯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與魯迅、高步瀛同時,1935年,他因徐悲鴻之邀前往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做兼職教授,1940年又受伍叔傥之聘,轉任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講授詞學專題,後來因台灣大學校長陸志鴻的禮聘,1947年前往該校任中文系教授,轉年系主任許壽裳不幸遇刺,喬大壯接任此職,為台大中文系第二任主任。
胡善兵是位有心人,第二十五期又刊發了他的《民國詞人喬大壯自沉原因發微》,文中提及1948年5月,喬大壯以探親為由從台北傳回南京,停留數日後又往上海,住在其女喬無疆家。在此期間喬大壯查閱郵件,希望收到台大新學期聘書,但因諸多原因,該校未寄出大部分老師的聘書,幾天後喬大壯孤身前往蘇州,住在蘇州太古旅館,于此寫好遺書,寄給喬無疆,而後自沉于蘇州平門外梅村橋下。
胡善兵說,民國建立後,在20世紀前半葉以自殺辭世的文人學者并多不見,這期間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及喬大壯自沉梅村橋下都給人“異代同悲”之感。文中引用了向達《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喬大壯之生死探析》中的所言,此文将當時知識份子的心态分為兩類,對于前者文中寫道:
當新舊兩時代交替之際,在其間最為感覺彷徨苦悶的,大約要數所謂知識份子。有一派對于舊的,既不勝其留戀;對于新的,又不勝其疑懼,彷徨無所适從。于是意志脆弱的,便醇酒婦人終世,而意志堅強的便幹脆自了其生。如王靜安先生即是屬于後一流的人。
關于後者,此文則稱:
還有一派,對于舊的也是不滿。可是他沒有力量改善舊的,也沒有勇氣接受的新的,始終在沖突中過日子。不幸在這彷徨的路上,受了一點不大不小的刺激,更無法調和這種沖突,而自己又良知未泯,在這時候,便也隻有将這無可奈何的生命,幹脆了結。
向達接着說:“喬大壯之死,可以歸入這一類。”喬大壯為什麼要自沉呢?胡善兵總結前人之說,認為自沉的原因主要有“猝賦悼亡說”“台大未寄聘書說”“對二子分處國共兩黨參加内戰而感内疚說”等,但他認為研究者忽略了一個問題:1948年初,喬大壯自台灣歸大陸後,曾在南京一位學生家借住數日,而這位學生似對喬大壯未盡到周緻的事師禮節,這或也是喬大壯萌生斯世無可留戀的原因。而後文中引用了曾克耑的所言,指出這位學生就是蔣維崧。之後胡善兵對這種說法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蔣維崧其實對喬大壯執弟子禮甚謹,那為什麼還會有這樣的猜測呢?顯然其中另有緣故。胡善兵的這些疏理,讓我得以明了當時知識份子的一些處境。
葉憲允《古代藏書史上的“書藏”》一文,則談出了曆代藏書家在藏書之外,又以“書藏”名之的奇特現象,文中提及蘇轼第一次使用這種稱呼方式,他在第二次擔任杭州太守時,為錢龢起了“錢氏書藏”的堂号,接下來又談到了阮元創立的靈隐書藏和焦山書藏,另外還有惠州的豐湖書藏,這幾處我都前往探訪過,唯獨沒有去過安亭書藏,正是此文的提醒,讓我有了一個新的尋訪目标。
《吳翌鳳字學九辨稿鈔本》,(清)吳翌鳳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0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乃責編時潤民先生所贈,該書大16開,上下兩冊,合計558頁之多,售價僅148元,在書價騰升的今日,這個價格足夠親民,但如此專業之書,想來印量不大,如何能将成本降到這麼低,确實需要方方面面的考量。
本書雖然是黑白印刷,但因在修版時沒有去底,故保留了許多版本資訊,這對版本鑒定最有益處,唯一的小缺憾是掃描時沒有給每個筒子頁襯墊白紙,緻使出來的效果,可以透過紙背看到另外一頁的反字。
關于吳翌鳳,我以往關注者是他的藏書成就。二十年前第一次到蘇州尋訪藏書樓時,在江澄波先生的帶領下目睹吳翌鳳舊居遺址,當時所見那裡已經變成了現代化的小區,隻是入口處立一仿古牌坊,同時小巷的側牆上露出一拴馬樁,江老說,此乃吳宅舊物。那個拴馬樁的柱頭雕一小獅子,小獅的三面已經被水泥包圍,故其正面顯現出小獅子的掙紮狀,讓人印象深刻。
本書前有王幼敏所撰《吳翌鳳與〈字學九辨〉》,文章首先對吳翌鳳的生平做了介紹,提及吳翌鳳自小家境貧寒,卻嗜書成癖,14歲之前就儲滿了一櫥書,然遇上吳中饑荒,隻好賣書換米。後來他又開始藏書,18歲時竊賊将其所藏全部偷走。再後來,吳翌鳳到陶家做家庭教師,稍有餘錢,又開始廣泛的收書和抄書,藏書量達到12000餘卷。乾隆五十二年,吳翌鳳出外遊幕,将家中藏書托給友人保管,然所托非良,在他出遊的第四年,這些藏書陸續被賣出,待其傳回時,萬卷藏書已蕩然無存,此時的吳翌鳳發揚藏書家堅韌不拔之毅力,以耄耋之年開始第四次收書,經過努力,又有了可觀的藏書,這種經曆令人敬佩。
我以往并不知道吳翌鳳在藏書和詩文創作外,還研究字學,雖然他曾在《遜志堂雜鈔》中提到曾撰《字學八辨》一書,然因無刊本傳世,故後人以為該書已經失傳。前些年王幼敏先生作碩士論文,偶然在華東師大圖書館看到了該稿本,他将這個發現寫入了《吳翌鳳研究——乾嘉姑蘇學界考略》一書中,由而讓人們了解到該稿的存在。
然該館将《字學九辨》著錄為鈔本。王幼敏發覺此書筆迹跟他見到的其他吳氏手稿本相似,是以懷疑這是稿本,然其未下肯定之語。前些年,曹大鐵舊藏出現在拍賣場中,其中有一部吳翌鳳所抄的《绛雲樓書目》,因我欲得該書,故仔細翻閱了該書的各個細節,其字迹與吳翌鳳的這部《字學九辨》完全相同,故以我的愚見,華東師大圖書館藏的這部《字學九辨》确實是吳翌鳳的手稿。今該稿得以影印出版,又給鑒定吳翌鳳手迹多一依據。
《鄒城古詩文選注》,張延齡選注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該社副社長詹斌先生所贈,小32開精裝,裸脊裝的設計,加外豎插式腰封,内頁便于翻閱平展,書内附有影印的張延齡先生手書《孟子》選錄。
本書無序言,書前有《标注序例》,作者談到在上世紀80年代,他受當時縣史志辦主任之約,編選一本詩文選注,選取鄒城人創作以及外地人寫鄒城的作品,該書起名為《邾婁故地,孔孟桑梓——曆代名家詩文選注》,作者亦稱這個題目有笨笨的感覺。
30年過去了,作者認為當時出版的那部書有許多不惬人意之處,故而又選編了本書,同時對所選詩文進行注釋。作者談到,他對于典故一個也不放過,不管是明用、暗用還是化用,都要一一注解,找到原始出處。但是這種作法說易行難,作者亦提到有些重要的詩文,因為找不到某一句的出處,隻能忍痛舍棄,他舉出了靳雲鵬祝壽文中的一句“千三百戶,無忌齊國之封”,作者說:
我想齊國厲公名無忌,但他是個短命的國君,上台不久便被人殺死了。這個例子不适合用來祝壽。名字叫無忌的“好人” 有個魏信陵君,但他的故事在秦、趙、魏三國,與齊國沒有任何交集。兩個攔路虎都與齊國有關。于是我重新細讀了《史記》中的《齊太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國語》中的《齊語》和《戰國策》中的《齊策》,沒有找到,便又浏覽了《晏子春秋》。心裡想着不會是南北朝時的典故,可是也仍然浏覽了《齊書》和《北齊書》。
為了一句話,查了這麼多的原典,結果仍是一無所獲。但是,作者覺得這篇文章中提到的曆史人物十分重要,故未将其舍棄,而是在注釋中實話實說,自己沒有查到原典,隻能“質之高明”了。這種不知為不知的态度最令人贊賞。我在寫一些書時,也時常碰到這種情況,在取與舍之間不斷的糾結,而今讀到張先生的這段話,反而給我以啟示:有些讀不懂的典故,如果實在查不出出處來,而文中又不能繞過去,不如就作這樣的說明,這樣既保證了書稿的完整性,也不會有強作解人的尴尬。
翻閱本書的正文,幾乎找不到熟悉的詩句,但卻看到了王安石的《孤桐》。記得國中時,最喜歡此詩中的“淩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一句,而今馬齒徒長之負,更覺得“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有着老骥伏枥,志在千裡之味。
我對鄒城的了解,隻知道這裡是亞聖孟子的故鄉,本書中也收有多篇詠歎孟子之詩,比如顧炎武的《谒孟廟》。十餘年來我兩度前往鄒城,均是瞻仰孟府、孟廟與孟林,書中收有不少與之相關的文獻,這些詩文如若不是張延齡老先生的搜集與注釋,恐怕少有人知之。比如本書收的第一篇《息鄹操》,乃是選自《孔叢子》,據傳此為孔子所作,盡管作者認為“疑為僞托”,但仍選入了本書中。該詩的前幾句為:
周道衰微,禮樂淩遲。
文武既墜,吾将焉歸?
孔子的言論主要見于《論語》,我還真沒有讀過他寫的詩。但這首詩寫得太過直白,雖不似夫子所為,但因其名也足讓人聯想。不知道詹斌社長何以贈我該書,也許是想讓我重溫歌詠亞聖之作吧。
《常熟文庫》第61冊,《常熟文庫》編委會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為責編南江濤先生所贈。去年的某天,南先生在微信中告訴我,常熟當地要出版該文庫,所收錄者均是與常熟有關的稀見史料,他從别的文章中得知我藏有一部明刻本的《杭川集》,而此書為孤本,且封面有翁同龢墨筆題記,故希望将該書納入《常熟文庫》中。
十餘年前,市面上出現了一批翁同龢舊藏,此為其一。翁同龢在該書的封面上寫道:“族祖昇宇公著。來自海外,子孫保之。光緒壬辰十二月同龢敬記。”可見翁相國得此書同樣不易。由此也讓我了解到該書作者翁應祥乃是翁同龢的族祖,《杭川集》雖僅兩卷,然附有《遊武夷山記》一卷,亦不見着錄,故将此書欣而攜歸。常熟乃藏書之鄉,當地朋友衆多,曾有多人講到對此書感興趣,于是借《常熟文庫》彙編之機,将全書掃描,寄給責編南江濤,書出版後,南先生賜此冊以作樣書。
關于《常熟文庫》的價值以及編纂起因,戴逸先生在《總序》中,首先引用了邑人李傑為弘治版《常熟縣志》所作序言:
姑蘇為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為城,環江海以為池,實東吳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産殷盛,若粳秫、布枲、魚鹽、蔬果,水陸之珍奇,是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餘,而不資外助。
這段話講述的是常熟的東南形勝,故戴逸認為:“姑蘇為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為城,環江海以為池,實東吳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産殷盛,若粳秫、布枲、魚鹽、蔬果,水陸之珍奇,是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餘,而不資外助。”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常熟一帶的情形最能印證這句話。是以戴逸先生寫出了如下文字:
這一切催生了一種個性鮮明的文化,并推動這種文化不斷發展。毫無疑問,文化是常熟的一張閃亮的名片,常熟是鑲嵌于中國文化地圖上的一顆熠熠發光的明珠。
以錢底巷為代表的崧澤文化遺存,以羅墩為代表的良渚文化遺存,是五千年前常熟受到早期中華文明曙光照耀的實證。而商代末年仲雍的南下與春秋時期言偃的北上更是标志性的事件。它們表明,常熟很早就積極參與到與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中國文化的塑造中了。從此以後,崇文重教成為曆史上常熟人共同的價值取向。邑人孫原湘《客有問吾邑者書此答之》這樣向外人介紹家鄉:
軟紅塵裡小蓬萊,畫閣文疏對岸開。
七水流香穿郭過,半山飛緑進城來。
酒多按節傾家釀,花不論錢遍地栽。
莫笑耕夫多識字,梁時便有讀書台。
詩中滿滿的自豪,但凡讀過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在這個風雅之鄉,連農夫也“多識字”,這樣的整體文化素質必然推高精英人物的數量與品質。李傑的序言中說:“自泰伯、子遊禮讓風行,文學化洽,而人才彙出。是固江南名區,非特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多少巍科進士,多少狀元宰相,幾乎每個常熟人都會津津樂道。尤其令人驚歎的,是常熟著書立說者之多以及著述之豐富。别的不說,隻看《江蘇藝文志》。在江蘇各大市中,蘇州卷最多,有四個分冊,而常熟獨占其中一冊。這就無怪乎明人桑悅要說“吾邑仲雍過化之區,子遊所産之地,素為文獻之邦”了。如果說桑悅是常熟人,難免有自炫之嫌,那麼,山東人趙執信的“常熟為東南名區,文獻之盛,甲于海内,文人才士,指不勝屈”,應該說是代表了公論。
文化流派的出現是一個地區文化發達的重要表征。明末清初,常熟湧現出衆多文化藝術流派,顯示常熟文化進入了鼎盛時期。以嚴澄為代表的虞山琴派,以錢謙益為代表的虞山詩派,以缪希雍為代表的虞山醫派,以王翚為代表的虞山畫派,以林臯為代表的虞山印派,無不有着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甚至連本來難以成派的藏書,也被認為存在着一個虞山派。這些文化藝術流派的重要人物,人人都有在各自的領域産生巨大影響的著作。
書光有人寫出來還不夠,因為書難成而易毀,曆史上亡佚之書遠多于傳世之書。幸運的是,常熟恰好是藏書之鄉,是舉世公認的私家藏書中心之一。而且,常熟的藏書家們往往注重鄉邦文獻的收藏,在這方面,陳氏稽瑞樓、瞿氏鐵琴銅劍樓、徐氏虹隐樓、丁氏缃素樓堪稱代表。因而,常熟地方文獻傳世之多,世上罕有其匹。據不完全統計,到一九一一年為止,現存常熟地方文獻達兩千種以上。
戴先生在上文中舉出了常熟當地著名的藏書樓,而我在實際探訪中,當地留存至今的藏書樓,遠比這些例舉多數倍,從這個角度也可印證當地文風之盛。該編委會能夠将與常熟有關的文獻彙為一編,讓更多的人了解到當地乃是文獻之邦,我能為這部大書略效薄力,也是感到榮幸之事。
《跳上詩船到德清》,朱炜選注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2020年8月第2次印刷
本書内容乃是古代與德清有關的詩作,朱炜先生對這些詩作進行了系統的編排和解讀,還作了相應的串講,故不能僅以“選注”二字涵蓋之。然而他贈我此書時,在微信中說:“選注之書,就不留筆墨了。”顯現出朱先生的謙遜與謹嚴。
前幾年,我準備再到湖州地區尋訪,經朋友介紹,結識了湖州文史專家劉正武先生,劉先生開車帶我到莫幹山尋訪,在那裡認識了莫幹山民國圖書館館長朱炜先生。在朱先生的帶領下,我在武康山中找到欲訪之迹。一路上聽朱炜講述着他對詩的摯愛,同時也了解到他有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各自搜集當地有關的文獻和圖檔,隻要是發現對方所需,就會互相間義務支援,這樣的團體真讓人感覺溫暖。
當我讀到朱炜為本書所寫的自序時,方了解到他的童年就生活在莫幹山,國小畢業後,他轉到縣城武康求學。某天他無意間看到了張炜和書法家張功華的詩書合璧展,于是特意去拜訪張炜先生。張先生問他“炜”字作何解,朱炜背出了《詩經》上的“彤管有炜,說怿女美”,張先生覺得他孺子可教,于是收為關門弟子。從那時起,他跟着張炜先生學習平仄韻腳,多年過去,不改初衷,一直創作不離詩,當年他所的作品還曾獲得杭州進階中學第三屆櫻花文會徐志摩詩歌獎一等獎。
後來朱炜到杭州讀大學,仍然堅持寫詩,畢業的那一年,他志願到杭州蘇東坡紀念館做義務講解員,就是在這個階段,他給葉嘉瑩先生寫信,還收到了葉先生的秘書可延濤老師的回信,葉先生在信中鼓勵了他,後來他還得到了葉先生的一部簽名本。我見到朱炜時,他給我講述過與葉先生交往的一些細節,我覺得遠比他在序中所寫的要有趣得多。葉先生說過,中國一直有詩教的傳統,正是這個概念,讓朱炜完成了本書。
此書中講到了蘇轼來德清遊覽半月泉之事,以往我沒有留意到東坡與德清的關系,故那次也沒向朱炜提及探訪此遺迹。本書中還收有蘇轼與其他人遊覽半月泉的題名和拓片,但是朱炜在文中也談到,此乃嘉慶九年徐秉源等人根據蘇轼等人的手迹模刻的,有人質疑過此題款的真僞,但朱炜在文中并沒有論及他支援哪種意見,他更多的是疏理東坡與題款人毛滂、維琳等人的關系。
通過這些疏理可以看到他對武康文獻的熟悉,他還講到了白石道人姜夔之号的來由。原來,在武康的計籌山升元觀舊有白石道人祠,同時在湖州弁山有白石洞天,他的号就是從這裡得來的。讀到這段掌故,讓我又有了再遊武康之念。
《徐兆玮雜著七種》,(民國)徐兆玮撰,蘇醒整理
鳳凰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王勉老師所贈“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一輯中的一種,書前有北大中文系潘建國教授所撰《新舊說部兩搜尋》一文,作為代前言。我以往的了解,徐兆玮當是民國間常熟著名的藏書家,曾前往常熟探看過他的虹隐樓,而潘先生也是常熟人,我本以為他所寫此文會從鄉賢的角度來論述,讀罷方知徐兆玮對小說的摯愛程度超乎想像,而潘先生的研究領域恰好也是小說史方面,難怪他會寫出這麼一篇長文。
潘建國先生這篇代前言首先從明清以降常熟的藏書文化講起,他講到了汲古閣、绛雲樓、脈望館、鐵琴銅劍樓等,同時也談及常熟的刻書、藏書,對于一般藏家所輕視的稗官野史也多有留意。然在傳統觀念上,僅從“小說”一名,即可看出傳統士大夫對于這類作品的輕視,但世風也會随着時代而轉變:“迨清季,國門開放,西風勁吹,梁任公倡導‘小說界革命’,應者雲集,小說遂從不登大雅之‘小道’,迅速躍升為‘文學之最上乘’。”
關于徐兆玮,潘建國在代前言中講到了他原本是光緒十六年的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出身可謂正途,然他卻沒有傳統藏書家對小說的排斥,反而對新舊小說情有獨鐘,徐兆玮自稱:“喜閱本朝說部書,取其有資掌故也,”為此還輯纂了一部名為《黃車掌錄》的小說資料彙編。
光緒三十三年,徐兆玮從上海乘輪船到日本,前往東京法政大學進修法學,法政大學毗鄰日本著名的神保町古書街,這裡可是愛書人的聖地,凡是中國藏書家前往日本,必會到訪此街,大量購買傳統典籍,徐兆玮也不例外。然而奇怪的是,他在這裡大量購買的卻是日本小說,比如《絕島軍艦》《南洋王》《電力艦隊》等,僅從名字上就覺得,這不是傳統的和刻本,應該是一些西式平裝書。
徐兆玮買這些小說,并不是為了充實他的藏書樓,潘先生從他的日記中摘錄大量他閱讀小說的記載,比如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十五日:“閱《指環黨》一卷,《昙花夢》一卷,林纾譯《玉雪留痕》一卷。”而在這一個月内,他每天都在看小說,可惜那時《指環王》還沒有寫出來,否則必被他收入囊中,寫到日記裡。
他曾寫信給鄉友孫雄:“近日濕癬大發,不出門者兩月餘矣,日以新出小說雜志為惟一之生命,案頭累累皆是物也。足下當亦闵其志之荒矣。”得病兩個月,竟然以天天讀小說來消永晝,愛小說到這種程度,以我有限的所知,未聞第二位藏書家有如此之酷愛。馬廉的不登大雅之堂也藏有很多小說,但此堂小說本本珍稀,絕不像徐兆玮這樣大量收藏當代出版物。
徐兆玮不僅如此,他還租賃小說看。潘建國說,清末民國間,小說租憑業大盛于上海,朱文炳在《海上竹枝詞》中雲:“時新小說價誠昂,數頁無非幾角洋。幸有贳書新社出,看完照價一分償。”1955年至1956年間,上海市曾對私營書籍攤鋪進行整頓與改造,經調查登記,全市共有書刊租賃業2357戶,這其中的2253戶乃是出租連環畫,104戶出租小說。徐兆玮晚年定居上海,時常去租小說來閱讀。潘先生統計出徐兆玮租賃的小說多至百十餘部,為此徐兆玮還寫過一首名為《租書》的詩:
租書月費僅千錢,小說虞初日一編。
脂夜人妖空即色,靈山道侶俠疑仙。
文言退舍更通俗,泛覽終朝勝懶眠。
博弈用心宣聖許,蠹魚生活我猶賢。
他在該詩的小注中寫道:“租費三月一進制,每元三千,是月僅一千。”我未換算這筆錢究竟多不多,但是作為一位翰林,竟然如此嗜讀新小說,總是讓人有皯詫異,對于這一點,潘先生在代序中明确說,:“徐兆玮的小說購藏重心,乃在新小說,而非舊小說。”這難道說明了徐兆玮的思想是與時俱進的嗎?徐所撰《遊戲報館雜詠》中稱:
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
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
他也說,嗜讀說部書是何等之荒唐,而那個時代人們不是喜歡談論新學,就是喜歡聊《紅樓夢》,他在此詩後的小注讀來讓人發噱:“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戊戌報章述之,以為笑噱。鄙人著《黃車掌錄》十卷,于紅學頗多創獲,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證之。”
那時的京城人喜歡談《紅樓夢》,而彼時人們已将其稱之為“紅學”,當新政之後,談紅學的人又改談經濟,他所說的經濟相當于後世所說的政治,康梁失敗之後,談經濟的這幫人又改回來談紅學,顯然,徐兆玮的這段論述有嘲諷的口吻,他又接着說,自己所撰的《黃車掌錄》對于紅學頗有創獲,不知如何了解這個轉換。
根據虹隐樓日記所載,《黃車掌錄》始編于光緒二十五年,到光緒三十四年時,徐兆玮将該稿謄清一份,交給曹元忠閱正,後來他又繼續補充此稿,到民國二十六年時,還計劃重新寫定《黃車掌錄》,可惜三年後徐兆玮病逝于上海,《黃車掌錄》最終未能刊行。他花了這麼長的時間來撰寫此稿,最終卻未能出版,個中原因,潘建國認為一是徐兆玮追求完美,補輯不止,二也有客觀的因素。對于這兩個原因,潘先生在代序中作了詳細的分析。
比如說,徐兆玮在撰寫該書的過程中,不斷變換撰寫體例,當時譯本小說數量不斷增加,原本徐兆玮給每部小說題寫絕句,但因小說太多,他寫不過來,隻好更張,那時也有不少人開始研究翻譯小說,這讓徐兆玮更加努力的增添此書稿的新内容,使得該稿始終難以完結。但即使如此,《黃車掌錄》所記載的小說有一些也是他書未載者。
如何來解讀一位傳統藏書家這樣喜歡新小說呢,潘建國認為,小說對于徐兆玮來說,是人生惬意生活的一種。潘建國說:“他對于新舊說部的一往深情,對于小說閱讀的如饑似渴,對于稗史研考的堅持不懈,皆罕有出其右者。”徐在日記中自稱:“日惟以小說書報消遣永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否他在政局動蕩之時,以此來排解心中之郁悶呢?但潘建國認為:“徐兆玮的人生卻注定因為小說而改變,因為小說而精彩。”
徐兆玮的《黃車掌錄》一稿藏在常熟圖書館,潘先生曾到該館仔細翻閱,而今該館的蘇醒先生将該書稿本整理了出來,同時搜羅了一些徐氏的其他手稿,合印為此書,可謂嘉惠士林。
《會海鴻泥錄》韋力錄
中華書局,2020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因為疫情的影響,這本小書出得很晚,但這也就令李碧玉女史有了更多的校刊時間,使得書中的文字會少一些錯誤。
其實本書的内容很簡單,乃是我近幾年參加的一些與書有關的會議。自參加工作以來,我像大多數人一樣,參加過無數個會議,大多數會議都如過眼雲煙,會議一結束,用不了多久就忘記了。然我覺得與書有關的會議畢竟不同,一是出于個人的偏愛,二是因為這些會議大多言之有物,有些觀念乃是電光火石般的閃現,如果不将它記錄下來,也許一些好的想法就忘記了。
正是出于這樣的想法,我參加一些自認為有價值的會議時,就會帶上相機,以便拍照現場的一些情形,一者可以做配圖用,二來看到圖檔後也能回憶起更多的細節。同時,我也會在現場不停筆地記錄着每位發言者所講的要點,傳回之後,盡快地将記錄複原成一篇小文。
寫完之時,隻是覺得好玩,過後再翻看這些小文,雖然僅僅過了幾年,卻讓自己有一些閑話說玄宗之感。我感覺這些記錄應該有一些史料價值,于是把自己的想法講述給俞國林先生聽,他認為就此編一本書也是有意義的事。受其鼓勵,我将其編為此書。當時,我給本書起名為《書山會海》,因為這個詞在近幾十年來受到過無數次的痛批,起此名乃是以大俗為大雅。但俞先生認為此名不好聽,他給我起的名稱乃是《會海鴻泥錄》,于是我從善如流,故在此感念他的起名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