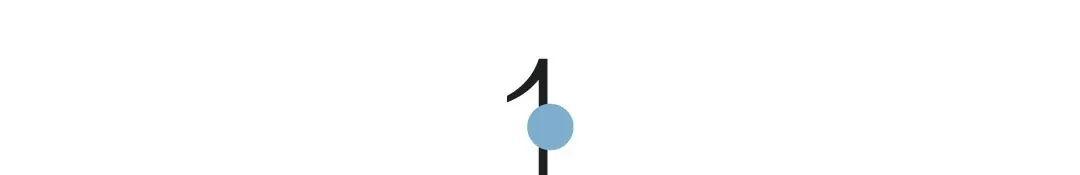
“這是真的。”
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别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哦,你也在這裡嗎?”
這段文藝腔的話語,出自張愛玲的散文《愛》。短短三百來字的文章,寫盡了一個人的漫漫一生——
一個被拐賣的女人,之後又被轉賣,走過山重水複,經過風波無數。待到韶華逝去,她還會回想起年輕時候的愛情。
一波三折的愛情,還沒開始,就已結束。一唱三歎的人生,讓人讀來覺得像小說,又像戲曲。然而這是現實中的故事。
是以,她要在文章開頭就強調:“這是真的。”
之是以是真的,那是因為,這個故事張愛玲從聽胡蘭成那裡聽來的。被拐賣的女人,就是胡蘭成的義母。
當時,兩人正處熱戀,一有空閑就膩歪在一起,聊中外文學、看西洋畫冊、日本版畫、北韓瓷器、古印度壁畫。
遇見張愛玲,胡蘭成覺得自己像一張走音的琴,獲得調弦正柱。
他倆也講述私房話,和彼此的過往。胡蘭成後來在書裡說,那段歲月,他倆在一起,說話說不完。
很多年後,張愛玲塵埃落定于美國,胡蘭成漂泊流亡在日本。他倆都老了,都在文字裡回望歲月。他在書裡詳寫了這則真實的故事。
如果将兩篇文章比作繪畫,張愛玲這篇獨幕喜劇文好似寫意,簡練含蓄;胡蘭成的回憶則是工筆,精雕細琢。
同一則故事,在不同的筆觸下産生别樣的質感,卻蘊含相同的況味:
錯過的叫愛情,經曆的是人生。
遇見後又錯過的愛情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在張愛玲筆下,故事這樣開篇。
在胡蘭成的記憶裡,故事女主角的身世簡直賽過一部寶卷。
這個女子,夫家姓俞,大家都叫她春姑娘。關于春姑娘的身世,是她自己講給義子胡蘭成聽的。
她原來的家,在杭州塘栖,父親在典當裡朝奉,相當于戲曲裡的員外。
也許從小被寵溺,也許天性使然,她非常嬌橫。小時候,典當夥計抱她玩耍,她非得騎在肩上。大人勸阻說女孩子家家不可以這樣,她不管,偏要騎。
上面有個哥哥,聰明伶俐,十幾歲就學會開當票。下面還有個弟弟,也長得粉團玉琢。
舊社會大多重男輕女,這戶人家的老夫人偏偏最疼愛女兒。夏夜乘涼,母親也要用簾子為她遮一遮,怕月亮曬黑了皮膚。
人情往來,她與姊妹同去赴宴,身着百繡裙,頭上金枝翡翠,打扮得花枝招展。元宵佳節,她邀朋引伴地去看花燈,笑語盈盈,衆人圍坐在一起賞燈、吃茶、嗑瓜子。
塘栖本是一塊優山美地,她每次節日裡出門,便成為風景中的一道風景。家境優,相貌好,來說媒的人踏斷門檻。
二十二歲那年,她遇到了這一生難以忘懷的愛情,也是改變她人生命運的轉折點。
有一天,她去後園樹上晾曬手巾。春光如許,心思搖漾,便信步到河邊看杏花。
“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個少年也在那裡,仿佛等着她似的。她知道他是鄰居家的親戚,也是來說媒的。
也許因為羞澀,也許出于矜持,她連對方的簡單招呼都沒回應。然而内心既驚又喜,還生出感激之情。因為遇見他,她才分明意識到自己是女兒身。
當下無言,轉身逃回。卻不知這一轉身,便是永遠的蹉跎。這是他倆第一次遇見,也是最後一次相見。
有些遇見,隻是一時,錯過卻是一世。
就像一句歌詞: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在。
被拐賣與轉賣的人生
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有些人為了金錢利益可以枉顧親情道義,純真無辜的人,是以會栽在自己人手裡。
那年四月,杏花飄落,杏子将熟。春姑娘的舅舅來了,說是接外甥女去自家住段時日,和表姊妹們作伴繡花。
不知是賭博輸錢欠下了債,還是其它原因,他并沒有把春姑娘帶到自家,而是賣給紹興城裡富貴人家作妾。
春姑娘平日裡很少出門,不知人情世故、人心叵測,大概做夢也沒想到自己遭人拐賣,而且賣她的人竟是自己舅舅。
新婚之夜,她在洞房裡大哭大鬧。那種情形,或許就如一句台詞——你喊吧,喊破喉嚨也沒人聽見。情急之下,她打了那富家少爺一巴掌。
這一巴掌結束了被迫的姻緣。
之後,春姑娘又被轉賣給浙江上虞一個姓章的男人。章先生家境殷實,人又斯文,擅長絲竹,很有文人的風雅,更主要愛惜她。
遺憾的是,不到三年,章先生就病逝了。在那之後,她又被轉賣到俞家。
俞家上代做鹽柴生意發家,在當地很有名聲。那姓俞的男人屬于農家子弟,有一股鄉土氣。春姑娘第一眼看到他,還以為他是做豬肉生意的屠夫,也歎息自己一朵鮮花飄落至泥土。
雖然缺乏一些生活的情趣和浪漫,但俞先生為人厚道,事事倚重春姑娘。雖然心有不甘,相比之下已算謀得好歸宿。
一個命運坎坷的女人在漂泊輾轉之後,最終在平實人家塵埃落定。這種際遇,落在胡蘭成的眼裡和筆端便是:
“從此縱有風浪浮華,她的一生隻是義父的了。”
這讓我想起《紅樓夢》中意味相仿的一句:“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不管小說亦或現實,短暫的是人生,冗長的是磨難。
在充滿磨難的人生中,失落的是愛情,蒼涼的是人生。
成為胡蘭成的義母
直到五十多歲,俞先生還沒一兒半女,便認胡蘭成做幹兒子。
十來歲的胡蘭成見到了義母春姑娘:“生得吊梢眼,水蛇腰,像京戲拾玉镯的旦角色。”
在他印象中,義母不但人長得美,做事又争強好勝,就像《紅樓夢》中王熙鳳似的人物。
胡蘭成第一次去,她正在堂前紡紗織布,身上穿輕孝。
他跪下,行禮,喊一聲母親,她笑着攙起,又連忙去房間取出銀項圈,往他脖子上一合,麻麻利利地戴上了。
這麼一個舉動,在小小年紀的胡蘭成心裡烙下一個詞:狠辣。
他後來能去杭州讀書,全靠俞家資助。放假回家,大多日子住俞家,跟在義母身邊。
她在檐下繡花、去谷場曬谷、到田畈上送飯,胡蘭成都願意跟随身後。她給他做紅桃綠葉的筆袋,給他講寒門子考中狀元不忘盡孝的故事,她總是想把他打扮成戲文裡讀書小官人的模樣。
其中心思與用意,胡蘭成自然明白。隻是他有自己的想法與追求,不願做他人繡羅上的金鹧鸪。
義父病逝時,義母一邊勞心費神料理喪事,一邊要與觊觎遺産的侄子鬥智鬥勇,忙着争訟打官司。進進出出,落在胡蘭成眼裡,義母更是個女強人。
辦完事胡蘭成準備回校,她給了一筆學費,做了番叮囑,句句都是真情真語。
再後來,春姑娘不但對胡蘭成與其妻子顯得面酸心硬,就連自己親生兒女也虐待,有點像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
上了年紀,她反而更加逞強,待人也狠辣。旁人也許無法明白其中緣由。
大半生已經過去,最終被她找到了娘家。沒有團圓帶來的歡喜,卻是落寞的蒼涼——父母都還健在,兄弟中有的已故,家道敗落,反而要她接濟。
娘家人去俞家走動,還得承奉她的笑臉。他們越承奉,她就越生氣,也就越沒好臉色。
胡蘭成說:“她這才覺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委屈,比以前她所想更委屈百倍。”
以前所想是怎樣呢?
讀完這個故事,我想起《徒然草》中一句話:“人心是不待風吹而自落的花。”
一個人的命運,猶如風吹花謝,零落到書卷文字,不管三言兩語還是連篇累牍,都是對現實人生的縮寫,甘苦自嘗,紙短情長。
即便過得很委屈,懷了很多怨恨,即便跋山涉水,再也回不去,若能有一段愛情,即便是短暫又單薄的愛情,也足以讓人有所懷念,像心裡藏着一塊糖。
現實生活中,我曾聽一位女性長輩在回憶裡設想——如果當初,沒有拒絕那個人,說不定就嫁給了他,日子哪裡會像現在這樣糟心……
我默默聽着,并不反駁,卻在心裡思忖——可能真的會比現在順心,同樣有可能比現在更加煩心。生活是一棵長滿可能的樹,誰說得準呢?
未曾得到的,總是最好的,人心向來如此。
如今,我漸漸能夠體諒往好的方面的遐想。生活中吃了太多苦,遭了不少罪,經曆的叫人生,錯過的叫愛情。既然隻是空想,為何不想得美好些?
遇見與錯過之間,能有空幻而朦胧的甜美往事令人回味,也算是一種苦中作樂吧。
故事裡,那個老了之後還常常說起春夜、桃樹和那個年輕人的春姑娘,便是如此。
作者 | 江徐,80後女子,煮字療饑,借筆畫心
圖檔| 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