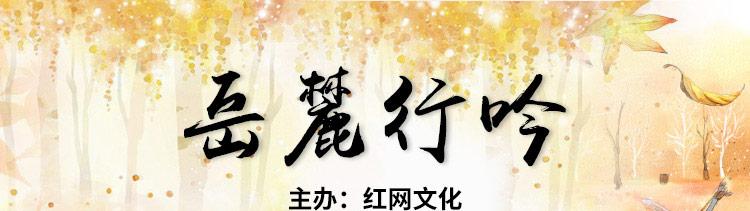
《甘建華地理詩選》圖書封面。
從衡嶽湘水到西部之西
——寫在《甘建華地理詩選》出版之際
文/尹朝晖
一
作為詩人的甘建華,早在20世紀80年代求學大西北時,就投身于轟轟烈烈的中國大學生詩歌運動。作為青海高原上第一個大學生詩歌社團湟水河的扛旗者,從那時起,現代新詩就嵌入了他的生命基因,帶着一個湘人的血液溫度,終于衍生出“西部之西”(The West of China's West)的文學版圖。
近幾年,我也徘徊在詩歌圈的外圍打醬油,見識了詩歌界的一些是非深淺。對建華兄的詩名,慢慢地有所了解。特别是經過他的極力舉薦與精心運作,台灣《創世紀》《台客詩刊》《華文現代詩》3家詩刊,相繼集體推出我們衡陽詩人和湖南詩人的作品,深化和拓展了他的“衡嶽湘水”,實在是功不可沒。而我有幸三番皆忝列其中,也是深感與有榮焉。
是以,那天他和我微信語音,談起他的地理詩選即将出版,約我寫幾句話,從資曆和自知之明的角度,我是十分惶恐的;從對他本人和詩歌的内心情感上,則是開心樂意的。
在目前湖南文化界和文學界,甘建華算得上是一個名聲響亮、值得尊敬的人物。而他的影響甚至遠及海内外,這有許多報刊發表其詩文為證,亦有不少海外華文詩人、評論家撰寫其詩評為證。
早年間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建華兄寫出了許多令人血脈贲張的深度報道,結集《天下好人》《鐵血之劍》兩本書,成為國内各大學新聞院系的研究對象,二三十名頂尖級專家學者發表評析文章,結集為《第三層表達》;作為衡陽為數不多的中國作協會員,他着眼于湖湘文化尤其是衡陽地方文化的研究和寫作,同時鐘情于第二故鄉青海柴達木盆地的散文創作與文史發掘,為兩地做了許多文化普及與推廣工作,先後獲得全國冰心散文獎、絲路散文獎、四川散文獎、吳伯箫散文獎、中華鐵人文學獎等各種獎項。
初次結識建華兄,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剛剛招聘到南嶽區委宣傳部。他那次來南嶽采訪,我陪他吃早餐,他站在鳳凰飯店下樓的台階上,透過鏡片光俯視着大堂内的我,把我壓抑得一路無話。後來因為工作和文學的關系,與他多有接觸和關注,慢慢地熟絡起來。特别是他作為一個黨報記者,始終保持着學生時代就萌生的良知,以新聞形式傳播正義,還天下人以公道和清白。
從這兩個層面而言,建華兄在衡陽、湖南乃至全國新聞界、文學界的影響,頗為後學如我所歆羨。
二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建華兄是一名地理學者,源于“西部之西”和“衡嶽湘水”兩個地理名詞。前者是他無中生有的虛構與獨創,後者是他進一步地深化與拓展,因而被中國地理學會招為會員,據說也是中國作協會員中目前唯一的中國地理學會會員。2018年11月1日,他的母校青海師範大學聘任他為地理學客座教授,據說在其母系成立60多年來,至今還是唯一的一個畢業生獲此榮耀。
“西部之西”是他一部同名小說的名字,卻有着地理學上的明确界限。在阿爾金山、祁連山和昆侖山之間,從盆地中部北緣的大柴旦出發,沿G315(西甯-喀什)茶卡-茫崖段,從魚卡、南八仙北上冷湖,再折而往西,直指老茫崖、油砂山、花土溝和阿拉爾草地,最終到達與新疆接壤的依吞布拉格。再傳回從尕斯庫勒湖、茫崖大坂,沿S303(格爾木-花土溝)東行,穿過甘森、那棱格勒河、烏圖美仁,到達戈壁新城格爾木,從G3011(原G215,甘肅柳園-格爾木)經盆地腹心達布遜湖,回到原點大柴旦鎮,整整一個大圈繞下來,約為1500公裡。它與“青海省柴達木盆地油氣田分布圖”大體一緻,建華兄與他的父親曾在此“我為祖國獻石油”。
“衡嶽湘水”其實就是南嶽衡山和湘江流域,具體說來,就是衡陽15310平方公裡的大地山河。“衡湘”最初見于東晉羅含《湘中記》(又稱《湘中山水記》),這是衡陽最早的文學作品。曆代名家包括唐人郎士元、韓愈,南宋楊萬裡,元代歐陽玄、張昱、鄭澤,明季李贽、徐霞客、高珩,晚清羅典、王萬澍、曾熙、彭維新,近現代齊白石、羅庸、吳宓、馮友蘭等,均有詩文稱道,山水因名詩而增輝,詩因名山水而流傳。建華兄曾請大詩人洛夫先生題寫“衡嶽湘水”四字,拟編輯、出品一套“衡嶽湘水叢書”。
對于建華兄來說,這兩個地方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義。因為,他的胞衣罐子埋在衡嶽湘水,他的青春熱血灑在西部之西。它們聯系着他成長臍帶的母性土地,撫育了他的少年莽撞、青春激情和中年建勳。
千百年來,老祖宗留下浩如煙海的詩歌,包含着豐富的生活中常見的地理知識和地理現象。譬如,“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李白);“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見牛羊”(《敕勒歌》),等等,這些流傳千古的名句,分别描寫了地理學科中的天氣物候、地形河流、自然景觀等相關知識。
建華兄的睿智與胸襟,是把一個地理學人的智性與詩人的血性結合,從“衡山之南”到“四海八荒”,從泉湖、界牌、福嚴寺、茅洞橋,到冷湖、茶卡、德令哈、烏圖美仁,行萬裡路,見萬個人,真正實作了詩與遠方的深度融合,拓展了一個文化學者的詩性主張。譬如《荞麥皁九章》其一:“村口那排葳蕤的樹木/就像大宅門的屏風/不易看透族人的心事/一步步走近/心裡悸動不甯/淚花迷離中/似乎觸及澎湃的血脈”。又如《花土溝的夢》:“繁華褪盡後的落寞/伴我一天天老去/相信依然有一雙大眼睛/眺望着通往西部之西/這條世界上最孤獨的公路”。明顯可見,建華兄在擴大自己文化版圖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放大自己,放大詩歌的格局。
看得出,他的内心是充盈的,亦是孤獨的。
三
著名湘籍作家韓少功在《文學的“根”》一文中說:“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該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裡,根不深,則葉難茂。”這句話後來成了尋根派文學一面迎風招展的大纛,它也深刻地影響了當時尚在湟水河畔寒窗苦讀的建華兄。
樹有根,人亦有根,建華兄的根,就是家鄉茅洞橋的根。“樹們一直甯靜地長在那兒/一棵是香樟/另兩棵也是香樟/幾蔸棕榈,一樹桃花/三五株女貞/橙子和柚子/春深處依然金黃欲墜/柞樹的刺去掉後/就是一杆筆直的秤/也是祖父傳奇的一生”(《村口》)。他一口氣為家鄉寫了20首詩,不僅老宅“門前橘花的馨香”,“彌漫了整個山沖”,圓柏、菖蒲、胡蔥、油桐、番椒等,都成了他的愛與鄉愁。在“衡嶽湘水”“衡山之南”“茅洞橋記”的大量篇幅中,他站在鄉村和城市的兩個次元,對現代文明程序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進行審視,對工業文明和農耕文明能否和諧共生展開深度思考。
對于遙遠而偏僻的柴達木盆地,那片傾注了三代石油人為之抛灑熱血和汗水的土地,建華兄用了大量的精力和篇幅,去摯愛、描摹、歌頌和緬懷。“二十二年後的夏日之晨/再度面對賽什騰山/一幅巨大的中國水墨寫意畫/淚水模糊的雙眼/在世界上日照時間最長的地方/曝光了一張情感的底片”(《回到冷湖》)。我覺得,不管是詩歌,還是其他的文學樣式,人類關心的是什麼,我們的文學怎樣去介入和幹預,就是人類命運的共同話題。
尤其是“奇人志異”“浙中之旅”“衡嶽湘水”輯中的一些詩,建華兄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發祥地和傳統文化集大成者,懷有高山仰止的敬意和“青藤門下走狗”式的謙卑。在徐霞客、龔自珍的雕塑和蘇東坡的墓前,他都曾紮紮實實地磕拜三記響頭。《青藤書屋》中的“何從乞漿食”“忍饑月下獨徘徊”,盡管非常節制地聲明先賢“徐渭不在”,卻把四百餘年後一個湖湘晚輩的虔誠與心酸寫得淋漓盡緻,進而更加确立起他們遺世獨立的文人形象。
建華兄用詩歌回答了三個終極性哲學命題:我是誰?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同時,準确生動地再現自然山水,并與世道人情共同作用于詩歌風格,回答了地理學的三個核心問題:它在哪裡?它是什麼樣的?它意味着什麼?
四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争朝夕。”(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每天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作為曾經身為新聞工作者的詩人建華兄,依然保持着敏銳的反應能力并表達幹預力。對于台海局勢、香港今昔、巴黎聖母院大火、叙利亞四十八小時停火、十三村征文等事件,在新聞發生的第一時間,建華兄便有熱氣騰騰的詩歌給予響應。讀《台灣清水斷崖》《香港尖沙咀一瞥》《巴黎聖母院》《中國男足》等詩,讓我很容易聯想其平時微信中的笑谑:“我不在江湖,但江湖仍有我的傳說。”
對于享譽世界華文詩壇洛夫先生的離去,父親含冤死于祁連山中的詩人痖弦,被北京副市長吳晗輕慢的文學家沈從文,拒吃山珍野味并痛斥當道的大畫家韓美林,為曆史作記而飽受争議的女作家方方,搖搖晃晃的腦癱女詩人餘秀華,建華兄均以極度推崇和悲憫之心,用詩歌表達他的良心尺度,用詩歌“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春天”,用詩歌摒棄和反諷着傳統的文人相輕。
作為詩人的建華兄,從來沒有沉溺于個人的小情緒中,就像著名詩人黃亞洲所說,他的“閱曆豐富、眼界開闊,這些都是詩人必要的修為”。他曾經用新聞傳播正義和良知,他現在用詩歌廣播博愛和溫暖。
行文至此,“瞬間淚目”。有些痛,是實體碰撞的外部生成;有些痛,是情動于衷的自然散發。之于建華兄的地理詩,亦如是。
萬法無差别,融解即同歸。每一個詩人,他的知識結構和生活經曆的不同,寫出來的詩歌一定千差萬别。一首好的詩歌,一定是帶着感性的詩歌,一定是帶着智性的詩歌,而一首出類拔萃的詩歌,應該是賦予神性光輝的詩歌。
在這裡,我要引用《孟子·盡心下》的一段話:“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我等凡夫俗子,倘若攀比樂正子,一生追随缪斯之神,窮盡一生可得善信美之一二,可謂足已。神性之光輝,永遠在高處照亮我們,沐浴我們,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從茅洞橋到花土溝,再從西部之西到衡嶽湘水,乃至于四海八荒,既是地理之旅,亦是詩歌之旅,更是精神之旅。
與建華兄共勉,頓首。
尹朝晖,筆名白丁,邵陽人,居南嶽。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衡陽詩歌學會副會長。曾在《創世紀》《詩選刊》《湖南文學》《安徽詩人》《台客詩刊》《華文現代詩》等刊發表詩歌。出版詩集《暮色四合》《五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