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孩子會說話以後,他便開始了背詩的漫長“旅程”。起先可能隻是父母為了教他更流利地說話,孩子很快就能背誦“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有時還能将之作為自己聰明的佐證在人前展示。漸漸地父母就會根據自己對傳統文化的了解(這種了解受到網絡上大量宣傳文章的影響),為孩子買來相關讀本,以及在網際網路上收藏各種音頻、視訊或付費課程等資源。上國小後,很多孩子都會購買“國小生必背古詩詞”的書,從此把背詩與學業正式對接。國小中高年級後,國文課本裡增加了文言文的部分,傳統文化的學習變成了可決定國文成績的關鍵名額之一。
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絕大部分著作都不是将兒童作為主要閱讀對象,沒有考慮到兒童的興趣、閱讀方式和接受能力,于是童書市場上也出現了大量試圖将傳統文化“低幼化”的讀本,用眼花缭亂都不足以形容其數量之多。僅僅四大名著就能變成立體書、漫畫書、繪本、拼音讀物、改編版、有聲版、原版、解讀版等多種形式,隻要家長願意買,孩子每長一歲都可以購買其中一到多個版本。在父母看向這個市場時,這個市場也在以海量的資源提醒他們傳統文化得從娃娃抓起。即便最佛系的父母,也有為選擇哪一個版本的成語故事而煩惱過。
如同任何一種被不斷強調的文化概念一樣,傳統文化在很多父母眼中開始帶有更深的人生寓意。有的父母認為學習它有助于形成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有的父母認為現代社會世風敗壞,傳統文化中的道德規訓卻是一種極好的育兒方法。還有的父母認為,學習它能提升孩子的文化修養,長大後能在祖國的大好河山中用詩詞歌賦抒發或排遣内心情感。
當傳統文化之于孩子變得更具功能性後,家長也易成為孩子學習的監工。在江南大學人文學院的黃曉丹看來,任何一種學習或閱讀,隻要它能作用于人的真知、德性、幸福或其中某一點,它就是值得學習的。傳統文化是衆多文化中的一種,并不需要被特殊獨立出來,應該讓孩子的傳統文化學習回歸到閱讀主流中,像其他閱讀一樣,以興趣來驅動。
黃曉丹不久前出版了《陶淵明也煩惱:給家長的傳統文化啟蒙課》,她因在大學教授古代文學課,平時經常給中國小老師做教育訓練,也會為一些在政府及事業機關的人做文學講座。很多聽衆為孩子的學習而煩惱,控訴孩子不愛讀書(《我的孩子不愛讀四大名著怎麼辦?》這篇書摘的标題取自家長的提問),她便萌生了要為家長寫一本傳統文化啟蒙書的念頭。她認為傳統文化讀本的選擇不應該是“四大名著這麼有名,孩子就一定得讀”。她在書中推薦的中國古典著作有三個共通性:經典的、有趣的和适合兒童的,目的是讓讀者看到傳統文化中有活力的部分,讓孩子可以自己從中讀到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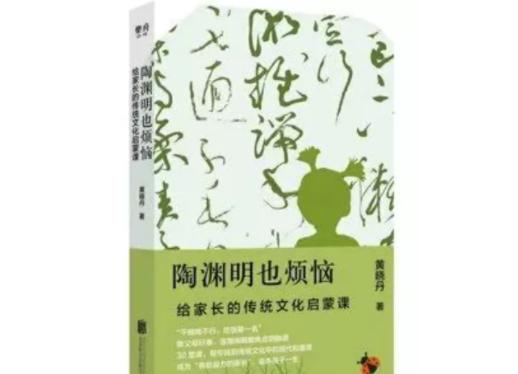
《陶淵明也煩惱:給家長的傳統文化啟蒙課》,黃曉丹 著,樂府文化 | 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6月版
我們也以這本書為契機采訪了黃曉丹。在采訪中,我們更關注的是家長在傳統文化讀本選擇上的困惑,以及家長之間讨論得最多的關于背誦的迷思。
傳統文化讀物的改編版這麼多,到底有沒有改編标準?
說起傳統文化,有人會想到二十四節氣,有人會想到儒家經典,還有人會想到四大名著。談論起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每個人也能說上幾句,但是非專業人士恐怕都難以清晰地給它下一個定義。在黃曉丹看來,傳統文化是一個中性概念,廣義地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的所有文化成果和文化活動都可以叫做傳統文化,甚至也包括現有中國領土上,在古代由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少數民族創造或由國際交通帶來的文化交流。“傳統文化”的範圍很大,但在我們現在的、總體是褒義用法中,“傳統文化”一般指“傳統文化經典”。
黃曉丹說,新文化運動之後,學界對于“傳統文化”的态度有“全盤否定”“儲存國故”與“折中改良”三種。以“全盤否定”派的觀點來看,不管經典不經典,中國的書最好是不讀;以“折中改良”派的觀點來看,最好能在保留傳統經典标準和适應現代價值觀之間尋求平衡;而“儲存國故”派則要求秉承傳統的“四部之學”。這三派的紛争是在學術層面上,而當今大衆所說的“傳統文化”,隻是傳統文化中最為粗淺的部分,對大多數人來說,不超過《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紅樓夢》十部書,及《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三部蒙學課本和《弟子規》一部僞蒙學課本。但這十來部書,在“傳統文化”甚至“傳統文化經典”的範圍内,都隻是滄海一粟。
但就算這十幾部書,現代人就已經很難完全讀懂了。這并不是因為現代人的文化水準下降了。現代人的平均文化水準遠遠超越古人,但語言文字、名物制度都在時間中變遷,是以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古代經典,都需要一代一代地重新注釋,以便讓當代人讀懂。
黃曉丹說,前人使用的解釋方法大抵有三種。一種是進行批注,起先是對原始版本進行注,接着進行注的注,這樣一層層注釋,形成“傳”“注”“箋”“疏”的次第,比如著名的《毛詩正義》,是由西漢的毛亨第一輪注釋,叫做“傳”,東漢的鄭玄在毛傳的基礎上再做注釋,叫做“箋”,唐代的孔穎達再在鄭箋的基礎上注釋,叫做“正義”。第二種是翻譯,就像我們上課的時候老師把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一樣。第三種是重述,它是一種創造性的改寫,比如魯迅寫的《故事新編》。通過這三種方法,人們讀不懂的古代文本得以解讀和傳播,後代在解釋的時候也會不斷地加入自己的觀點。
黃曉丹,現任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在大學既教中文系的中國古代文學課,也教國小教育系的兒童文學課。已出版有《詩人十四個》。
這種為了傳播而進行的解釋無可厚非,但是它跟現在我們看到許多改編作品存在很大的差異。以前不論是做注、翻譯還是重述,都有界定标準。一種界定由官方指定,科舉考試也按照它來考,比如明代科舉,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标準教科書。還有一種就是知識分子群體同行評議,比如要看仇兆鳌注釋的《杜工部集》,要看王琦注釋的《李太白集》。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的标準變成了流量評議。在這種評議中,改寫是否尊重原著,在改寫過程中是不是在知識上、價值觀上和語言美感上有比較高水準的介入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營銷做得怎麼樣,有沒有讓更多人看到了它,聽到了它。
黃曉丹認為,現在很多出版商做書時一味迎合傳統文化這個概念,很多看起來像傳統文化的書,其實傳統文化的内容非常少,被稀釋了很多倍後,就像我們喝的牛奶飲料一樣,牛奶沒有多少,味道卻很好,其實孩子沒有從中汲取到營養。
可是現在我們也很難為傳統文化讀本找到一個普适的标準,同樣主題的兩本書隻有拿到專家面前,他才知道哪一本是在胡說,哪一本講得基本是對的。而對于家長來說,看待傳統文化讀本就跟藝術鑒賞一樣,更多依靠的是鑒賞者自己的素養。
黃曉丹建議,如果家長已經形成了一套自己購買童書的準則,相信自己的挑選眼光,那麼無須因為手上拿的這本書是關于傳統文化的就覺得自己的準則不适用了。有時候像傳統文化這種十分流行的概念會左右讀者的判斷,若家長覺得一本“傳統文化必讀書”裡的價值觀不能接受,語言形式不夠精美,配圖醜陋,判斷它是消遣讀物,那麼他就應該相信自己的判斷。公認的經典應該高于我們對于普通書籍的評價标準,而不是說因為它是經典,就可以低于這個标準。家長不必懷疑自己的眼光,也不要太把自己當外行。
為什麼有的孩子就是對傳統文化提不起興趣?
孩子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常常與家長的引導有很大的關系。但是黃曉丹也看過不少例子,就是家長饒有興趣,孩子依然提不起興趣。她認為,這跟孩子的先天氣質有關。
黃曉丹說,現代學科體系包含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被分為實體、化學、數學、曆史、地理等不同學科。20世紀初曾有學者嘗試将中國古代文化成果分梳整理後歸并到現代學術體系中,但問題在于,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發展邏輯是不同的。自然科學以疊代的規律發展,新成果一般超越并淘汰舊成果。人文學科以累積的方式發展,新成果并不能摒斥舊成果。這樣就形成了一種不平衡:我們現在還能學習、欣賞先秦直至清代的文學、藝術、哲學、史學作品,卻不大可能學習、欣賞古代的數學、天文學、地理學作品。是以,“傳統文化”并不是萬能的,自然科學中很多學科門類在“傳統文化”中都沒有對應物。它們産生于現代,也隻能用現代的方式進行學習。
黃曉丹認為,人有先天上的氣質差異,古希臘就有對人格的分類,後來發展出的“大五人格測試”及“MTBI”更是提供了對于先天氣質差異的更深認識。是以,有些孩子的禀賦在文學、藝術、哲學方面,這些學科在傳統中有對應書籍,有些孩子的禀賦在程式設計、生化、實體方面,這些學科在傳統中不太有對應書籍。當後一種孩子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無興趣,其實是對某些學科的無興趣。
黃曉丹提到,那些興趣和天賦都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孩子,他們可以讀莎士比亞,也可以讀曹雪芹,對于傳統文化中文學藝術部分的接受基本沒有障礙,還能獲得很多好處。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他們覺得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學的世界都是荒誕不經的,對人文學科毫無興趣,當然也就不太願意配合學習傳統文化。因為能夠傳承下來的傳統文化基本是在人文學科。家長沒有必要刻意追求孩子在學習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應該破除“學習了傳統文化就能變成一個高雅的人”的迷信。
但黃曉丹在做教育訓練時發現,有一些具有理工學科背景的成年人,他們想尋求文學藝術鑒賞方面的指導,他們的理由是,覺得自己的感覺力不行。為什麼有的人在獲得了一定的地位或成就之後開始思考感受力呢?因為幸福是和感受相關的,和分析能力沒有太大關系。是以當他們開始思考我與世界、與他人、與孩子的聯系時,就把目光轉向了傳統文化。如果是帶着這樣的需求去學習傳統文化,他們就能注意到傳統文化中真正令自己産生感受力的東西,而不是先考慮這個文化在經典中的排名是第1名還是第200名。
是以不論對人文學科是否具有天賦,隻要是從自己的需求出發,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都不晚,與其費盡心思地去背誦别人定義的經典,不如先激活自己的感覺,建立經典與自己生活的關聯。
大量背誦,孩子在未來真的能在某種情到深處時自然吟誦嗎?
許多父母相信童年時的背誦能在一生中留下記憶,要求孩子無論喜不喜歡都要将某些詩詞或文章背下來,黃曉丹認為,這就像為了将來能從資料庫裡提取資訊,而把整個資料庫都背下來一樣。但實際上傳統文化浩如煙海,就拿詩詞來說,存世唐詩有五萬餘首,存世宋詞有二萬餘首,存世宋詩有二十七萬首。即使把《唐詩三百首》裡的詩都背會了,那麼這300首就足夠應付孩子未來所有的感受嗎?
黃曉丹說,正常的邏輯應該是,當你産生了某種感受時,有人把最适合表達這種感覺的詩貼出來讓你看到了,然後你覺得這首詩真好,被它安慰到了。對于這樣的詩,去有意加以記憶是有益的,而且這種記憶也會更自然、更深刻、更持久。孩子未來需要的是用資料庫來對應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通過現在的強制背誦,等着将來在記憶的資料庫裡湊到可以表達自己感受的詩詞。
黃曉丹說,隻要一個人翻過《萬首唐人絕句》,他就會消除對《唐詩三百首》的執著。一個有感覺力且有一定知識水準的人去看《萬首唐人絕句》,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100首,而且會毫不費力地把它們背出來,這才是一種去跟自我的感覺建立聯系的方式。
黃曉丹認為,家長應該具備兩種思維,雖然這兩種思維可能是沖突的。其一是要破除對于傳統文化這個概念的崇拜,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我們還不知道這個叫傳統,所有發生的一切都是傳統文化。其二就是家長要知道傳統文化的内容到底有多麼豐富,其豐富程度已經超過我們所有現代文化的總和。是以傳統文化不是靠補課就能補完的東西,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窮盡對傳統文學的學習。
很多家長希望詩詞可以提高孩子的感受力,讓詩詞成為自己和孩子之間傳遞感受的媒介,家長也通過為孩子誦讀,把自己感受到的世界美好的一面傳遞給孩子,黃曉丹建議,如果是出于這種目的,就不要用僵化的背誦方式,可以嘗試購買目的性沒有那麼強的傳統文化讀本。當成年人熱愛傳統文化,孩子才有可能被他們的熱情感染,進而主動去了解。
黃曉丹深有感觸,很多孩子抵觸的不是傳統文化,而是抵觸傳統文化的狹隘化。這種狹隘局限了他們自己的感受力,要他們按照别人的标準來占領自己的記憶空間。盡管中國的傳統經典中有趣和富有想象力的内容一點也不輸于西方經典,但是孩子們感受到的一直是枯燥的和道德感太強的部分。
采寫 | 申婵
編輯 | 王一
校對 |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