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關于北京大學的早期求學回憶,顯得分量太不足了。就是在這不多的回憶文字中,讓讀者很難以感覺當年馮友蘭在北大讀書的情景,以及師友之間的學術交往。作為早期北大哲學門學生,馮友蘭當時的同學基本上是人中之龍,他們以後在學術道路上彼此援引,學問上互相切磋,成為現代學術發展的獨特風景。馮友蘭與陳鐘凡之間是不同年級的同學,在馮友蘭從美國留學歸國初期的大學講授中,陳鐘凡是扮演了自己的引薦角色的。在無法獨斷河南中州大學校務後,馮友蘭準備着到廣東大學發展。這個到廣州教書的邀請,就是陳鐘凡發出的。但我在《三松堂自序》中卻沒有發現陳鐘凡的名字,馮友蘭說“我有一個北大的同學,在廣州廣東大學作文科主任,約我去。”這個做文科主任的北大同學就是陳鐘凡。按照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揭示的、馮友蘭寫在1966年的《我的反動曆史和反動關系(補充材料之一)》,馮友蘭很清楚寫明是時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教授、兼任廣東大學文科主任陳鐘凡發出的邀請,目的是陳将自己兼任的文科主任讓給馮友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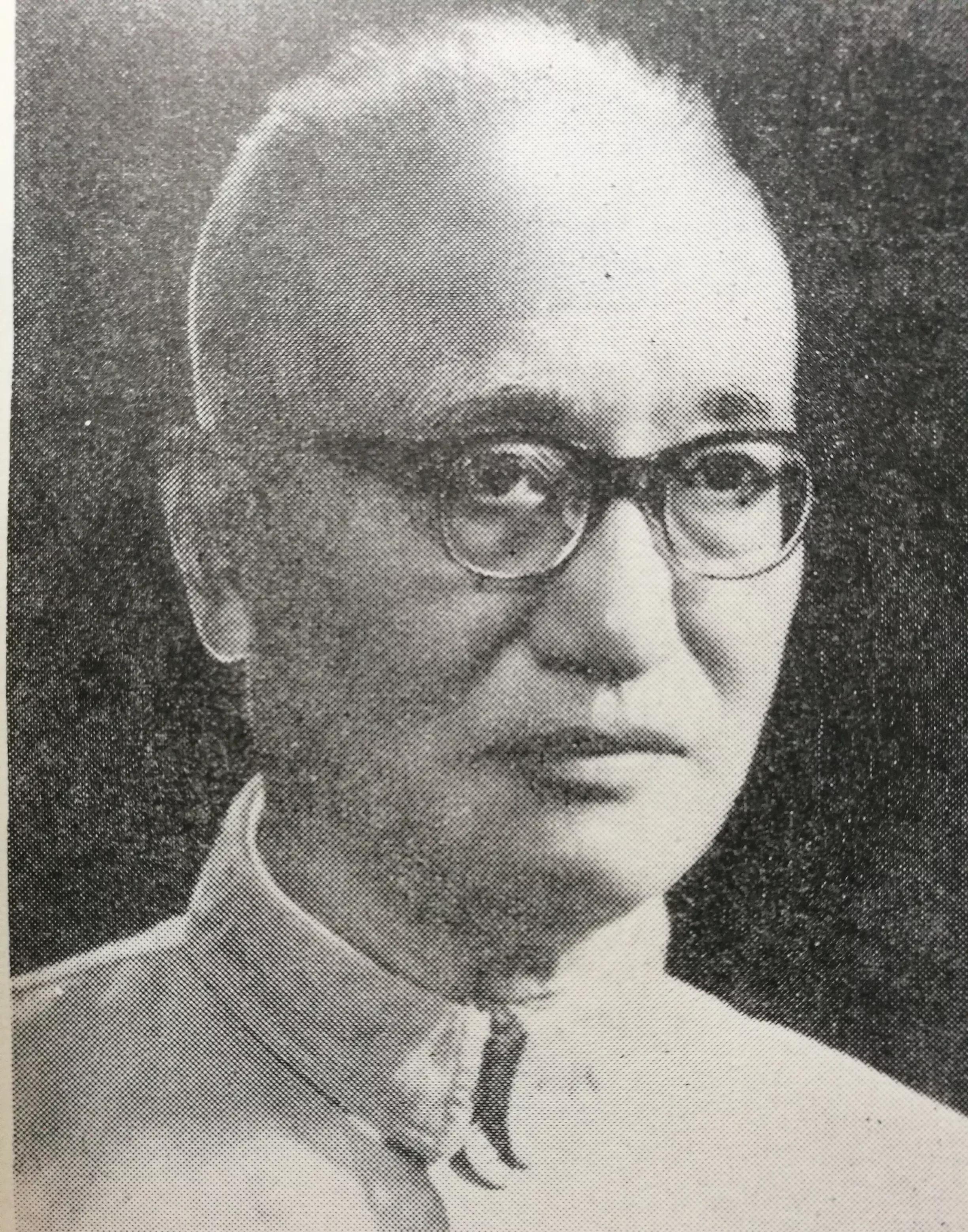
著名文學史家陳鐘凡
馮友蘭與陳鐘凡是北京大學早期哲學門的同學,但并不是同一年級的。陳鐘凡生于1888年,比馮友蘭年長7歲。17歲在江蘇淮安中學讀書時加入光複會,23歲參加辛亥革命,25歲在家鄉鹽城縣立國小做國文教員,這是陳鐘凡考入北京大學哲學門前的經曆。1914年,陳鐘凡26歲考進北大哲學門;1915年,20歲的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中國哲學門。陳鐘凡比馮友蘭高一屆。當陳鐘凡這一屆哲學門畢業生離校時,三年級生的同學馮友蘭、孫本文等同學還主持召開了歡送會。陳鐘凡在北大讀書時,遠比馮友蘭活躍,這似乎與他年齡比較大、社會閱曆相對豐富有關系。
陳鐘凡讀書期間,對研究所研究員劉少珊的《老莊哲學演講錄》主張的以遠西哲學解釋周秦玄理,提出了批評。這個批評文字發表在民國7年4月12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劉少珊對陳鐘凡的批評,作了很客氣的答複。劉謂自己的《古字通》、《老子學系論》對老子學說的見解有自己的資料依據,對陳鐘凡提出劉有不少史籍資料沒有援引,以及《孔子家語》不能信據,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陳鐘凡在北大哲學門研究所的學術活動中比較突出,且對諸子學有比較深厚的積蘊,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家學的薰陶。陳鐘凡的叔父陳玉樹(1853~1906)是江陰南菁書院山長王先謙的及門弟子,精通《毛詩》、《爾雅》、諸子學。陳鐘凡随叔父學,見聞益富。北大《國故》月刊社成立時,陳鐘凡作為北大文科預科教員擔任這個月刊社的編輯。在《國故》月刊的創刊号上,陳鐘凡發表了《諸子通誼》的論文。《國故》月刊後來曾刊登了陳鐘凡叔父陳玉樹的遺著,這是在陳鐘凡畢業留校北大以後的事了。馮友蘭在留學美國時,因為北大同學楊振聲的介紹成為《新潮》社成員。這就比較明顯地表明了陳、馮兩人的學術取向的不同。
按照地域學風、師承授受與學派傳衍劃分江蘇地域的學術派别,學術史家往往就有以蘇州為中心的“吳派”之說,有以常州為中心的“常州今文學派”之别,有以揚州為中心的“揚州學派”之分。吳派以經學箋注為主,說經依傍古文經學,尤其是對禮、易研究很深透,本本主義的色彩很濃厚,好古、信古,缺乏懷疑精神。常州學派專守今文經學,不十分注重疏解、箋注,而着重的是今文經學的義理、義疏;不迷信古學,有懷疑經典的學問精神。揚州學派講究字字有考證,句句有來曆,語語征實,言而可據,據而可信。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經文考證,金壇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疏,甘泉焦循的《孟子正義》,儀征劉氏的左氏學,寶應劉台拱的《論語骈枝》,将這個學派的學術特性與學問方式傳衍得很分明。陳鐘凡所師承的學問出處,就是比較典型的揚州學派;也就是說,陳鐘凡可以視為揚州學派的餘脈後勁。
揚州學派之儀征劉氏四代家傳左氏學。陳鐘凡1917年北大哲學門畢業留校教書,同時為文科哲學門、文學門研究所研究所學生。1919年《國故》月刊社創立,陳鐘凡為編輯之一。《國故》月刊的總編輯是儀征劉師培、蕲春黃侃。劉師培(字申叔)是晚期揚州學派的學術中堅,劉師培的曾祖父劉文淇(字孟瞻)“文學為江淮甲觀,士林無異詞”。(梅鶴孫《青谿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第14頁)《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是道光時代左氏學的力作,也為劉氏家族研究左傳奠定了學術基礎。劉文淇之子劉毓松繼承家學,有父風,繼續攻治左傳:“自孟瞻先生為左氏學,缵承先志,旁通經史諸子百家,凡所寓目,悉留于心;或廣坐道其原委,聞者私校原書,不訛一字。”(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第111頁)其著《春秋左氏傳大義》足以傳家。劉毓松長子劉壽曾繼續祖、父左氏學,成《左氏疏義》,成就三世之學。清人汪士铎稱贊劉壽曾“治經該博,摛詞古雅,大師碩彥,禮先缟帶。”(梅鶴孫《青谿舊屋儀征劉氏五世小記》第85頁)劉師培為劉壽曾猶子,傳承先業,守古文家法,《春秋左氏傳例略》、《禮經舊說考》、《周書補正》等大見家學功力。章太炎亦向劉師培攻習左氏學。
劉師培在北京大學國文門教授時,化育了一大批弟子,陳鐘凡即是其中者之一。劉師培1919年病逝後,南社創始人陳去病在寫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信中謂“申叔幼承家學,瓣香前哲,詞章經術,相容并包,實為當世所罕覩。”(《北京大學日刊》第504号)劉辭世三年後,陳鐘凡撰寫了《儀征劉先生行述》,以表彰先師之學。陳鐘凡從清代學術流變中評判劉師培的學術地位,他說“清代經師治古文者,自高郵王氏父子以降,迄于定海黃氏、德清俞氏、瑞安孫氏,各揭厥識,匡微補缺,闡發宏多。若夫廣征古說,足诤馬鄭之違,且鉗今師之口,則諸家未之或逮。”(《北京大學日刊》第1095号)章太炎弟子錢玄同在30年代整理《劉申叔先生遺書》時,不遺餘力,表達對劉氏學問的高度尊敬。一手促成南桂馨印行《劉申叔先生遺書》的學者張江裁,對劉師培的詞章、經術也是推崇備至:“先生考古既獨具卓識,觀人所不能觀,察人所不能察。惟其一覽千載,故恒一語破的。”(張江裁《劉申叔先生遺書刊行始末記》;《國學論衡》第8期;民國25年版)
陳鐘凡北大的老師劉師培
陳鐘凡經學、諸子學之家學隻是造其端,而得學術真傳、儒術之菁華,及劉師培之門而能成其大。在陳鐘凡學術生涯中,揚州學派之文選學,對其詞章、文體、文學流變史的影響是深刻的。李詳是揚州興化人,曾授徒鹽城許家,與陳鐘凡叔父陳玉樹交好;李詳是晚清《國粹學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與劉師培也有學術之誼。李詳專攻文選之學,對揚州學派的變遷極為熟悉。陳鐘凡執教東南大學,與吳梅、陳去病成立國學研究會,創辦《國學叢刊》時,與江蘇老輩學人如李詳、胡玉缙、孫德謙等都有比較多的學術聯系。陳鐘凡《古書校讀法》、《諸子通誼》、《經學通論》等,是他北大畢業後的學術論著,大多是研究經學、子學、目錄學;以後,陳鐘凡将自己的學術重心轉移到了中國文學史領域。
1926年,馮友蘭離開廣州廣東大學哲學系,前往北平的燕京大學做哲學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這期間與陳鐘凡保持了通信聯系。馮在給陳的信中報告了自己在燕京大學的教課現狀:“弟上學期在燕京授《中國哲學史》一學期,自洪範講至清末,隻說粗枝大葉,并無講義。本年弟在燕京隻講人生哲學,未講哲學史。”信中馮友蘭還代問了“小石、作賓、中敏”。小石,即胡小石,是陳鐘凡的學術朋友,作賓即董作賓,為北大的旁聽生,後考入北大國學門研究所研究所學生,是著名的甲骨學家,為馮友蘭的河南同鄉。中敏即任中敏,北大國文系畢業生,專門研究詞曲史,為吳梅的高足。胡、董、任三位與馮友蘭的學術研究不很相關。陳鐘凡的諸子學、中國思想史研究比較知名于時,但陳後來的學術發展多層面、多領域。這似乎限定了陳在某一個領域的特出貢獻。
早期北京大學同學中,馮友蘭沒有如顧颉剛、傅斯年以胡适之為學術門戶,也沒有如羅家倫、段錫朋等人吃政治飯,他始終如一的在哲學、中國哲學史上自立門戶、自成家派,成就了馮氏的學術席位。當諸多早期北大同學消散在學術的新風舊雨而名聲淹晦時,馮友蘭的以學術為切務不作他觀的超然态度,成就了他心志的專一。陳鐘凡的學術成就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諸子學、古典文獻與中國戲曲史的研究,最後流于中國文學史,這就與他早期在北大哲學門所攻讀的專業疏離的太遠了。這算不算是一種學術史的遺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