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這個字在中國文化裡内涵很深,它有時代表一種身份,有時代表一種職業,有時代表一種風度,有時代表一種精神形态。
士之謂始于西周,是貴族階層的最後一級,也就是“王、諸侯、卿、大夫、士”裡面的士。春秋時,士大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祿為生,有的有食田。但士這個貴族身份比較勉強,《禮記·玉藻》:“士佩瓀玟而缊組绶”。瓀玟乃石次玉者,也就是今天考古學所說的“假玉”們,就是松石、水晶、玉髓之類。士比之真正的貴族要差一級,是以隻能佩戴用黃色絲帶系起的“假玉 ”。
在其所在階層中,士的地位、身份确乎略顯尴尬。《白虎通疏證·卷一·爵》明确稱:“士非爵”而“以大夫知卿亦爵也”。士身處統治階層中但卻被排除于貴族爵位體系外,則至少其就不可能有“封建”身份和“裂土”資格,是以他就絕不可能稱為“某君”,隻能是“某君”之下的部屬。《白虎通疏證·卷一·爵》:
士這種部屬就是最早的一批專業的行政或技術官僚。但我們知道,一個穩定政治體的運作,特别是中國這種很早就形成的以自上而下集權治理體系為主的社會形制下,這些技術官僚才是日常社會管理的主力,是政權穩固的基礎。是以身份雖尴尬,重要性卻毫不含糊,如何培養并選拔他們就進而成為國家制度體系中很關鍵的部分。也是以,士即是中國古代大一統集權體系的基礎,選士制度亦是選官制度發展的源頭。以其為源頭而最終不斷發展了三千多年的這一體系,直接構造了曆史興替的部分邏輯。
因其重要性,是以選士制度在三禮的《周禮》與《禮記》中都有明确記載,并在《禮記》中直接記入《王制》篇,其記載為:
這一《王制》所載的選士制度,從秀士而俊士、造士,最終經考核而成為進士可授官。進士者,進而為士,更證明了“士”是官僚的資格本源。這一記載被認為是西周制度,現南京科舉博物館科舉源流說明文字開篇即此。但現行《禮記》來源可疑,早有論述應為西漢僞書。而從其選士制度描述看,比如由“鄉”而初選曰“論”;由鄉向上兩途:分由司徒與學者升者名目有别;之後入中樞考核,合格者授官。此一流程極符合西漢後期及東漢察舉制特征,唯其中的名詞有别耳。是以,此一選士制度極可能是漢儒托古而作的僞“周制”,其反應的更大機率是漢本朝的察舉制。是以,更多以漢代察舉制作為中國選官制度可考察的源頭更為合理。
到了戰國後期,貴族壟斷政治的局面被打破,一大批著名的草根達人登上核心政治舞台,他們多被稱為卿士,“士”開始成為有政治地位的知識階層的稱呼,其中最為博學的被稱為“博士”。同時,“士”這個稱呼也開始有了泛指餘地,一些專注于某種技能和事務的人被稱為士,如“遊士”、“辯士”、“俠士”等。《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成書于東漢早期,這裡對于“士”的解釋還比較接近于戰國之“士”的本相。也于此時起,士這一名詞開始有了除身份以外的其他文化意涵萌芽。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此時士的身份進入一種半開放性的狀态:一方面,它确實還是統治階層,甚至依然被視為貴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開始向非貴族階層開放了部分入口。可以說,在這一階段,士背後的政治内涵開始向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轉化。這一點,此時的“士”與歐洲封建社會早期所謂“騎士”群體有一定的類似性。歐洲此時的“騎士”亦是一個新的概念,指大批無正式爵位、貴族資格模糊,以成為正式貴族武裝附庸來換取土地和職位的人。所不同的是,在漢武帝徹底結束“封建”時代之後,中國之“士”直接演進成了龐大而穩固的官僚集團,而非歐洲“騎士”向貴族集團堅持不懈地融入。
從西漢早期起,選官(士)制度真正有據可查地登上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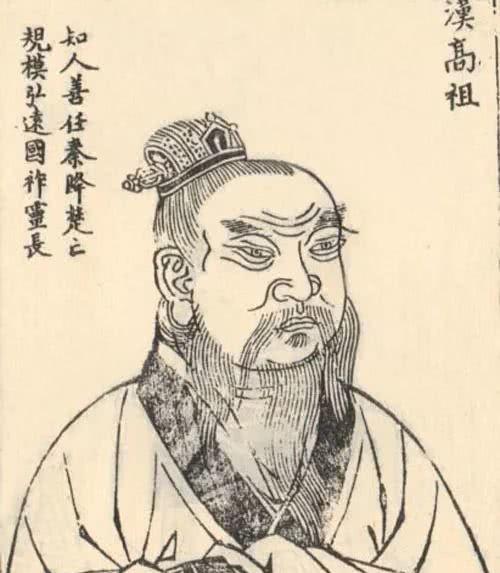
西漢的建立,是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規律性更替的第一次。這個第一次就具有太多的試驗性,之後我們在曆史裡看到的曆次興替中那些耳熟能詳的操作,于西漢初是不會必然存在的,比如改正朔、大赦、均田等等。甚至包括行政體系如何建立,于劉邦集團而言,都需要摸着石頭過河。
《通典·選舉一》:
以此诏觀之,三要點:
1、我太缺人了,天下的精英們,你們既然接受了我做皇帝,就得出來幫我治天下啊,出來吧,别再藏着了。
2、耽于秦之橫暴失政,漢王朝強調用人的标準核心是“德”,有明德者可用。
3、給現任官員下達選人的KPI,完不成的領責甚至免官。
此诏從行政和實操角度說,可稱隻具大略而缺乏實際操作指導性,因為标準、流程皆無。但即使這樣一個大而無當的诏書,依然在政權建立的第十一年才頒布,可知漢的前十年在行政上如何艱難和一團亂麻。但無論如何,這樣一道诏書開啟了漢王朝乃至整個中國的選官制度史。
在高帝開始進行用人選官的制度探索後,至惠帝和高後有了一些進展,可統一視為高帝時代的成果,《通典·選舉一》:
雖未給高帝之诏添加什麼實質性進展,但請注意,為“明德”的具體标準提出了第一個具象名額:孝。随其後的是文、景時代,這個時代與高帝時代共同構成漢代選官制度的序幕,《通典·選舉一》:
文帝始行黃老之術,文、景之治的實質以掙錢、攢錢為務,既無尊儒之後的諸多道德羁絆,亦有盡量充實國庫的強烈沖動。是以,後世須被诟病的“有錢就當官”,于時堂皇國策毫無挂礙,甚至有理論依據,即:“時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赀十萬乃得為吏。”
但其中還是為武帝時代創立察舉制做了一個貢獻,即認為廉者一寡欲二無錢,是以降低身價要求的标準以使廉者可入仕。則文、景時代為高帝定的用人“明德”原則又添加一個可具象的标準: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