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寫|楊世琪
五一勞動節假期即将結束。這些天你出去了嗎?因為新的冠狀病毒,你可能會呆在家裡很長一段時間,即使你出去度假,你也不能走得太遠。夏天來了,你懷念外面的世界,那裡的人群,那裡的大自然嗎?今天就和你談談大自然吧。
面對大自然中可愛的生物,我們忍不住拍了幾張照片,或者停下來欣賞它們很長一段時間,但很多時候,我們與它們的聯系隻在那裡。在現代社會中,速度主宰着一切,我們很少關心自然界中昆蟲和鳥類的鳥類和鳥類。對于逐漸與自然隔絕的孩子來說,這尤其是一個巨大的缺失點。為此,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ve)寫了《森林裡最後的孩子》(The Last Child in the Forest),在書中他将逐漸脫離自然的孩子描述為"自然缺陷"。如何彌補這一缺陷?僅僅閱讀知識科學書籍可能還不夠,我們需要一種通過曲折捕捉的知識,我們需要一種從日常生活中探索世界背面的方法。
自然音符是一種嘗試。2008年,《注意自然》一書被引入中國,自然筆記慢慢被接受為接近自然的一種方式。後來,我們進行了各種自然筆記課程,自然筆記比賽,但如何做到取得更好的成績,但沒有明确的例子。最近出版的兒童科學系列"我的自然筆記"的第一個系列以"家"為半徑,通過文字和圖檔将孩子們帶到廚房和陽台,觀察和探索周圍的自然世界。
由于新的冠狀病毒,我們必須呆在有限的空間裡,但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有限的空間,通過一小扇自然音符的窗戶來探索神奇的大自然。好的天然音符是無年齡的,它們所包含的自然和審美精神,從長遠來看也會在各個方面影響人們的思想和思想。
目前的疫情向我們表明,在自然面前,人類畢竟是脆弱的。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成為我們需要從這次疫情中反思的問題。那麼自然音符能起到什麼作用呢?我們的自然教育應該如何進行?如何避免現代城市的孩子成為"森林中的最後一個孩子"?對此,圍繞《我的自然筆記》系列叢書前後的故事,我們采訪了該系列主編餘東麗和陸永林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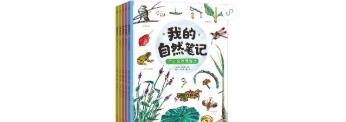
《我的自然筆記》(《奇特房客》、《家有寵物》、《廚房發現》和《自然遊戲》、《發現一隻鳥》等)第一輯,作者:于東麗、盧永林、于東林、于東林、秦秀平、李航,小博基湖南科技出版社,2020年4月
人與自然:惡魔島的鳥人
1962年,電影史上獨具特色的"監獄電影"《惡魔島的鳥人》誕生。
(惡魔島的鳥人)
。在這部改編自現實生活中的電影中,年輕的羅伯特·斯特勞德因過失殺人罪被判處終身監禁,他的生活逐漸消失。一個暴風雨的夜晚,在監獄裡呆了多年的斯特勞德正在離開牢房,這時一隻濕漉漉的、病了的鳥落在他的腳邊,經過幾次猶豫,他把這隻鳥帶回了他的牢房。在他的悉心呵護下,小鳥漸漸痊愈,斯特勞德心底的頑強冰塊慢慢融化了。後來,監獄裡爆發了一場奇怪的鳥瘟,他努力拯救死鳥,使他成為一名著名的鳥類學家,隻上了幾年國小。
"惡魔島的鳥人1962。
盡管受到好評,斯特勞德仍然是一個囚犯,不可避免地會變老。隻是,在他的精神中,有些東西正在悄悄地改變。他用自己對自然界生命真正意義的了解,安慰了監獄裡絕望的年輕人。他試圖盡可能多地生活,甚至測量雲的大小。在斯特勞德,我們感受到大自然給人們帶來的變化,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從這個角度來看,《惡魔島的鳥人》也可以說是一部"自然片"。
同樣在1962年,一本關于自然的書《寂靜的春天》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這本書的聲名鵲起引發了"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以來最激烈的辯論",并直接導緻了現代環保主義運動。其實,在《寂靜的春天》之前,不乏《沙村年鑒》這樣深入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作品,但當時人們依然沉溺于對戰後工業發展的熱情之中。
1949年出版的《沙國年鑒》是奧爾多·利奧波德近一生的觀察日記。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個廢棄農場裡,利奧波德與這片土地一起工作,并撰寫了許多自然散文和哲學論文。在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土地倫理"的概念,并呼籲培養"生态良知"。但就像許多真正重要的書一樣,利奧波德的作品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60年代,當"寂靜的春天"出現時,利奧波德獲得了遲到的贊譽。
從一個普通的生活過人成長為自然觀察者和研究者,是惡魔島囚犯斯特勞德經曆的第一次蛻變。從曆史上看,許多自然科學家和自然作家都經曆過這一過程,普通人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沙國年鑒》也是如此。20世紀60年代以後,直到今天,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加入了認識和保護自然的行列。餘東麗就是其中之一。2009年,《沙湘年鑒》出版60年後,她以一本名為《筆記自然》的書開啟了自己的"蛻變"。
于東麗,文學博士,是中國最早倡導"自然音符"的人之一。2008年加入上海綠洲生态交流與保護中心,成為一名環保志願者。2013年,他出版了《自然筆記》,并與丈夫盧永林一起創辦了"家庭寫作工作坊"。2014年,"自然公益學校"成立,微信公衆号開通,近幾年來,學校開展了數十項社會家庭公益自然教育活動。(右圖是餘東麗,他正在和孩子們一起做自然的筆記)
這種"蛻變"也是個人的遭遇。燕東麗的家鄉是四川省攀枝花市,20世紀70年代,攀枝花煤礦開采已經不像後來那樣不一樣,自然環境還是比較原始的風格。小時候,于東麗看到,是各種山草、鳥和獸,推開窗戶,打開門,仿佛"世上萬物都朝向自己"。她後來意識到,這就是利奧波德所說的"荒野":"荒野是讓人們享受獨處的樂趣,"利奧波德說。其實,孩子也需要一些時間和内心的孤獨,當心安靜下來,與萬物交流時,那種"孤獨"就很美妙了。我現在明白了,在我的童年時代,我享受着利奧波德所說的極大的幸福感,而現在荒野是一種稀缺的資源。"
這種"幸福"在于東麗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後來,随着黑煤窯在山上蔓延,許多自然生物在她真正認識它們之前就已經消失了,甚至連房屋最終都一起消失在瓦礫和灰塵中。她也不得不跟随父母,在全國各地搬家,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因為沒有記錄過這些自然生物,她一直記不清它們長什麼樣子,留下的隻有深深的遺憾和遺憾。
利奧波德在《沙國年鑒》中寫道:"對于我們幾個人來說,有機會看到蜻蜓比看電視更重要,有機會看到一朵白頭花是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就像言論自由一樣。"利奧波德向赫恩登和更多親近自然并最終失去自然的人表達了他的想法。
自然筆記:蹲下來,找到決定性的蜻蜓和蜻蜓
"那是一個沉悶的夜晚,一家不平凡的折扣書店,"她回憶起自己與Note Nature的相遇。但在這樣一個沒有安全感的時間和空間裡,我接受了它。當時,那本《注自然》和很多書一起躺在地上,卻在翻開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心裡等它很久了。"
《注意自然》(美國)克萊爾·沃克·萊斯利,查爾斯·E·E·羅斯,由麥子翻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
很長一段時間,餘東麗都想分享各種關于自然的故事,但她找不到合适的方式。直到Note Nature的出現,她才意識到她仍然可以以"自然筆記"的方式傳達自己的聲音。她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好奇地看着周圍的自然世界,孜孜不倦地寫作和繪畫,并創造了中國大陸的第一個自然音符。在她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然做筆記,包括她的婆婆秦秀英。在她的指導下,修英的祖母,隻讀國小一年半,在七十多歲時學會了寫作和繪畫,并出版了《呼瑪的天空》一書。
對于國内很多讀者來說,"自然筆記"看似一種新穎的表達方式,但實際上,它并不是一件新鮮事,而是一種古老的觀察和記錄自然的方式。作為記錄手寫和手繪相結合的一種方式,它可以是科學探索性的,記錄從發現到回答的探索過程,或者散文,記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與大自然的對話。
在做自然筆記的過程中,你可能會遇到涉及科學、藝術等不同學科的問題,但不懂繪畫技巧,沒有生物學知識,也不會阻礙自然筆記的創作。Leslie、Yu Dongli和秀瑩的祖母在第一次寫下自然筆記時,看着紙上的空白。真正重要的是一顆充滿激情的心。在制作自然記錄或長或短時間時,我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世界中,同時,它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安靜的背景,我們不僅可以仔細研究其他生物的生命軌迹,還可以仔細檢查它們的日常生活。
《呼瑪的天空》,修英奶奶畫,鐵葫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
此外,萊斯利和同力一緻認為,沒有必要長途跋涉數千英裡進行驚心動魄的冒險,即使我們呆在家裡并保持最近的視窗,我們也可以記錄自然界中發生的事情。
《我的自然筆記》的第一個系列是關于"家"作為觀察半徑的。在《奇異房客》中,餘東麗和陸永林發現浴室地闆上長出了一棵幼苗,就像一雙小眼睛。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中的許多人可能隻會對這樣一個問題做出反應:浴室裡怎麼會有草?然後,拔下插頭或停止。但于東麗帶着強烈的好奇心,在讓幼苗繼續生長的同時,在仔細觀察、精心養護的同時,也在其中做了實驗,進而發現了一系列有趣的事情。我們後來才知道,這些"小眼睛"被稱為決定性的。
在仔細觀察時,利奧波德在《沙國年鑒》中提到了另一種小型的、被忽視的植物——飛蛾。他寫道:"那個渴望春天,但眼睛朝上的人,從未見過像蜻蜓這樣小的東西,那些對春天感到沮喪,低垂眼睛的人,已經踩到了春天,仍然對它一無所知。那個把膝蓋放在泥濘中尋找春天的人找到了它 - 它是如此之多。"
在《我的自然筆記》中,它充滿了這樣的細節和時刻。在《家有萌芽的最愛》中,顔東麗喜歡對待家庭,記錄了八哥"小睡"、棕頭牡丹鹦鹉"綠群"、紫光漣漪"坦坦"的故事。在最後一個故事中,"Tantan"因為沒有羽毛成功而死亡,這讀起來很悲傷。在"奇怪的房客"中,她饒有興趣地觀察、實驗和記錄了花盆中的老鼠、蛞蝓和跳躍的昆蟲,頁面标本中的蚜蟲,香料食品中的煙草甲蟲,甚至是在睡覺時不幸被壓碎的隐藏的鳍蟲。在《廚房發現》中,她通過吃紫薯來探索植物色素的秘密,以發現舌頭顔色的變化;通過吃蘆葦根,她追蹤植物根和莖的奧秘,并使用宇宙星系繪制各種植物芽星系來比較其根上的芽。
芥藍芽星系圖。
像這樣的許多想法都令人印象深刻。她發現紫光幼蟲是精緻的六角形柱子,是以她用蠕蟲做了一幅印刷藝術畫。後來,她發現植物汁液在不同的環境和媒體中會變色,于是她用植物汁作為顔料,創作了各種獨特的畫作。
通過實驗,她發現,如果将植物的莖比作動力傳動系統,那麼蕃薯和胡蘿蔔就是一種營養巴士。
閱讀這些自然的音符會帶來極大的樂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餘東麗和陸永林對生活細節的敏銳感受和熱愛。在她家裡,無論是在客廳、餐廳還是書房、卧室裡,都是一片收藏和實驗的"重土",甚至廚房裡還裝滿了各種瓶子和罐頭來做實驗。"如果你認為廚房隻是一個做飯的地方,那麼隻有食物才能從中産生,如果你能把廚房變成一個小實驗室,那麼不僅僅是食物從中出來,而是科學探究的精神,藝術創作的靈感,以及觸摸自然奧秘的樂趣, "她說。
探索性自然筆記,讓孩子和大自然快樂"約會"
在《我的自然筆記》這套書中,有很多如《發現者》,如《與自然玩遊戲》的作者之一,陸永林的五位阿姨秦秀平,《尋鳥》的作者李航,以及第二輯的作者正在創作中。每個作者的風格都不一樣,每本書都有許多無窮無盡的故事。
就像于東麗和秦秀平的《玩弄自然》一樣,沒有質樸的野味。借用城鄉觸手可及的各種自然事物,兩人進行了三輪比賽——樹葉制成的"平底船"和樹葉上的露珠制成的"彩色珠寶",柳樹枝制成的樹皮面具和懸挂鈴木制成的樹皮面具,以及牛草遊戲和"來訪蟾蜍", 每個遊戲都有一個有趣的過程,探索每個遊戲背後的科學原理。
2017年春天,編輯李偉看到餘東麗的自然筆記部落格,驚訝于這些俏皮可愛嚴肅的文字和圖檔,認為它們是做書的好素材,并與餘東麗取得了聯系。在逐漸接觸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高度認同感:在中國,雖然很多以自然筆記為名的書籍已經出版,但真正适合孩子直接閱讀和學習的原創本土作品卻寥寥無幾。是以,他們想出了一個想法,即創作一系列有趣的自然音符,激發孩子們的科學探索"書籍。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何建立這樣一套書?當時,無論是國内還是國外,都沒有類似的例子可供參考,他們隻能在摸索前進,而在摸索的過程中,有人不斷退縮。經過幾年的反複讨論和讨論,第一個系列終于問世了。
秀英奶奶和八哥"小睡"。
該系列涉及知識的方方面面,但由于作者都是普通人,沒有專業背景,缺乏專業的裝置和實驗室,是以每一個小小的探索過程都充滿了曲折。"但我認為這是最有趣的事情,這是探索過程中最真實的狀态。"如果沒有問題,這很容易,這與從普通網頁中學習沒有什麼不同,"她說。我們普通人探索的時候,會發現科學探索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枯燥乏味,我們會發現一些我們平時認為理所當然的真理是不正确的。有挫折要找新發現,最重要的是在個人觀察和實驗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獨立思考。"
房屋的自然窗戶,順時針方向,是植物區,海洋區,昆蟲區,燕窩區。
中國"自然筆記",自然教育的得失
自2009年拿自然筆記以來,已經十多年了,李安東的人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曾幾何時,她是一個忙碌的編輯,下班後經常空虛,現在她不僅覺得自己的内心世界越來越豐富,而且感到一種責任,"那是對自然的責任,同時将自然教育傳播給更多的人",她也開始認真反思"教育"這個詞。
随着自然音符的引入和推廣,中國已經舉辦了許多針對年輕人的自然音符比賽,許多學校都在積極倡導。在上海,一些學校将其引入自然課和科技課,既作為教學内容,也作為學習的手段,自然筆記越來越受歡迎。
顔東麗認為,當自然音符作為"新事物"被引入時,舉辦比賽有助于它的普及和推廣,但随着自然音符的概念廣為人知,然後遊戲作為唯一或最重要的發展形式,它偏離了它的起點。"自然筆記的初衷是倡導大家平等地親近自然,一旦進入遊戲,就會有太多的等級制度和競争感。許多學校和機構現在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取消了比賽,而是展示,分享和交流自然音符。
自然展示櫃。"與大自然玩耍"中的樹皮面具。
在業餘時間,她也會帶孩子親近大自然,其中一次讓她感覺很深。有一次在上海閘北公園"雨課",她讓孩子們舔雨,品嘗雨的味道,但沒有孩子主動去做,全都盯着家長。她吃了一驚,沒想到孩子和自然之間的差距會這麼大。後來,在她的鼓勵和父母的允許下,孩子們終于嘗到了雨的味道,發現它是甜蜜的。看着興奮的孩子們,餘東麗感到既高興又有些難過。
這種隔閡是現代生活的産物,在目前的疫情形勢下,餘東麗還有另一層擔憂:人們都在倡導遠離野生動物,一方面,這對保護野生動物有好處,但另一方面,孩子和自然會變得更加遙遠?
公園是孩子們親近大自然最友善的地方,但現在它們變得越來越統一。閘北公園是嚴東麗一家搬家前最常去的地方。在那些日子裡,公園保留了它原來的外觀,雖然面積很小,但堆疊的灌木叢非常有曆史意義,許多動物栖息在其中。當他們搬家時,公園正在進行重大翻新。說起蛻變,她覺得有點苦澀。她說,為了滿足城市的監管要求,人們看起來就像一片亂糟糟的灌木叢被砍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草,園内有很多樹枝和縫隙的樹林,小路穿過安靜,現在是一片平坦的,原來的風格已經消失了。
曾幾何時,閘北公園内有一片懸挂的鈴木森林,樹上有幾個巨大的喜鵲巢,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稀有群落。這是一件好事,也是自然教育的好材料。但有一年,一隻喜鵲因為在公園裡撿不到巢料,隻好去現場撿拾,半山腰,剛撞到一個遊客,公園裡就被抱怨了,一夜之間清理了所有的喜鵲巢穴。這讓餘東麗感到憤怒和悲傷。"在許多人眼中,城市公園是人們放松的地方,但對于野生動物來說,這是他們的家。如果人們不改變自己的審美觀念,不給野外環境足夠的寬容,我們失去的就是自然延伸到我們最近的觸角。沒有這些觸手,我們将無法再近距離看到真實的自然。"
在她看來,大自然應該是豐富而有棱角的,而不是均勻的溫柔。"自然的語言是什麼樣的?"人們經常使用"安靜,安靜"這個詞。事實并非如此。大自然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生物,所有的生物都在說話,說話,每一種生命形式都在表達自己,這才是大自然真正的語言。"
用植物汁塗漆。
多年前,生物學寵兒餘東麗誤撞上了語言學和寫作的博士。然後她意識到,人的語言與自然的語言是如此相似。語言的進化就像生物物種的進化,從下往上,從少到多,最後長成一棵綠樹成蔭的樹。
"語言譜系認為,人類語言最初有一個或幾個共同的祖先,在人類發展的漫長過程中,語言分支出來,最終演變成豐富多樣的民族語言和方言。正如每種語言都包含人類發展和進化的密碼一樣,每個生物物種也是如此,它們的解釋将有助于解開人類發展和生命進化的奧秘。是以,保護民族語言和方言,保護每一個生物物種,都非常重要。沒有他們,我們将失去的将是我們的過去和曆史,我們将永遠不知道我們從哪裡來,未來将迷失。"
在自然教育中,一個重要的教訓是自然的精神儲備。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為了讓人們到鄉下,親近大自然,美國政府修建了很多道路,卻破壞了當地美麗的自然環境,利奧波德是以提出:"發展休閑娛樂,不是要把道路建成美麗的鄉村,而是要讓人類的心靈有能力感覺鄉村的美麗。"
此刻,他覺得利奧波德的話還不是不合時宜的,"利奧波德很久以前就說過這麼深刻的話,但我們仍然在重複同樣的毀滅行為。隻有有了這樣的心靈儲備,才有可能知道如何以一種既不破壞它也不感覺它的美麗的方式進入曠野。是以現在我更喜歡從家裡和學校開始,引導孩子們磨練這樣一個"美麗的心靈"。"
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年1月11日-1948年4月21日),被譽為美國新保護活動的"先知"和"美國新環境理論的創始人"。《沙國年鑒》是他的自然散文和哲學散文集。
在疫情下,我們改造創造自己
疫情期間,餘東麗、陸永林在《自然公益學校》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疫情期間普通人的自白或兩個'消息'》的文章,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延伸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要成為自然的倒置者,想超越自然的局限到人, 并靠自己的雙腳站立。然而,人也是他自己的本性。人必須反對自己,成為自己的叛逆者,才能第二次出生。"
這段話,寫于一種特殊的心态,凝聚了兩人多年來對自然教育和環境保護的思考。盧永林是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他說:"要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畢竟要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擺放。我們要保護環境,但我們也知道,人們是在自己的生活條件下,在各種利益的鍊條上。一方面,一個人會為自然做一些好事,另一方面,一旦他回到日常生活中,回到各種利益鍊條上,很可能他在自然界中就有那種放棄的善意。如果人與人之間的競争是永無止境的,不能有更好的解脫,人們對事物的欲望,對自然的直接或間接掠奪也将是無止境的。"
那麼如何放慢腳步呢?盧永林說:"人是從自然中生來的,他們也背負着或者因為自然對人的束縛,是以人要超越。這不是問題,因為這是人與獸區分的界柱,是人類的根源。但這還不夠,它能保證人成為人,卻不能保證人成為有美德的人。是以,人們需要做自己的否定和超越——做自己的反轉。"這個"自我"不僅包括生命的每一個個體,也包括生命中的每一個個體的人類物種、文明和社會。所謂"反制自己"和"做自己的反轉",其實是一種對人自身的全面反思和更新。
這些畫作是基于紫色洋芋汁的藍色特征,變成綠色。
于東麗平時和陸永林讨論類似的問題,經常談論我們内心環保的事實。這也是一種反思,人要時刻反思自己的内心,不能懈怠。如果我們隻是去大自然的第一秒去感受美麗和舒适,第二秒接受朋友的邀請去吃山難得遊戲,這就是心靈的污染;
梭羅每天早上去湖邊洗澡,"但洗澡其實隻是一種外在的儀式,真正的目的是每天淨化心靈,"她說。梭羅說:"如果你醒來時面對的生活不如你入睡時更崇高,那麼這一天就沒有多少希望了。"是以他日複一日地更新他的思想。我們不是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但心靈的環境保護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和可以做到的事情。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美國作家和哲學家,也是廢奴主義者和博物學家。圖為2017年《新京報書評》特輯《多面梭羅:尋找男人的烏托邦》的封面。
通過勤奮的反思,我們對自己的"對立",最終會成為我們對更自由、更廣闊、更深刻的生活的擁抱。但要真正使這成為可能,最終需要将其落實到每個普通人自己的轉化和創造中。就像這次疫情一樣,有那麼多事情在召喚着普通人之前、之後和之後。"普通人必須創造世界,普通人必須創造自己,"盧寫道。"
所謂"創造",也是内在力量的産生。外面的世界有瘟疫,人心中有瘟疫,人類生活中的許多危機實際上源于許多普通人的日常腐敗,這種日常的腐敗會形成一種共同的習俗,進而産生普世權力。是以,"創造世界"的必要性在于,如果一個人沒有比自己更廣闊的世界作為支撐,就很容易在中間退卻,跌倒,成為後續。所謂"自己創造"是指,雖然普通人在掌權中處于弱勢,但不是在智慧、勇氣、美德上流放,而是應該回顧自己的意識和無意識,主動擺脫世人的主導觀念、生活方式,開辟自己的人生道路。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事實并非如此,人們應該從疫情中吸取真正的教訓。從小個角度來看,做自然筆記的個人行為也是對自己的一種"轉化",是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一種小"革命"。正如文章所寫的:"隻有當一個人處理好自己的關系時,他才能處理好與世界上所有事物的關系。我們都應該向卡夫卡學習,并繼續對自己發動戰争。我們不僅要抵制所有他人的腐敗,而且要抵制我們自己所有人的腐敗。"這正是阿爾卡特的鳥類飼養員從大自然中學到的。
撰稿:楊世琪
編輯:席旭偉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