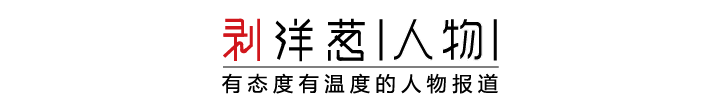
“孩子沉迷遊戲的‘鍋’不應該隻甩在家長身上。家長和孩子一樣,都不了解遊戲的多元性、複雜性,他們通常覺得所有的遊戲都是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怎麼判斷什麼遊戲是好的、是應該讓孩子玩呢?”學者劉夢霏說。
中國上海,一家網吧内,年輕人上網玩電子網絡遊戲。圖/IC photo
文丨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賈甯
►本文6094字 閱讀11分鐘
時隔半年,文潔還是常常想起,因女兒擅自給遊戲充了三千多塊,她的家庭一下子變成了戰場:丈夫打了女兒,女兒鬧起了絕食。那一刻,她感覺好像“失去了女兒”。女兒也從此變得“好冷漠、好陌生”。
她将這些厄運歸結為女兒沉迷于“遊戲”。
在當下的中文語境裡,“遊戲”常常指向電子遊戲。在中國資訊化飛速發展的二十餘年裡,“遊戲”屢遭“網瘾”“電子鴉片”等争議。
2021年8月30日,國家新聞出版署在官方網站釋出《關于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要求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節假日每日20時至21時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服務。這在網際網路上被稱為“史上最嚴防沉迷政策”。
新規落地至今,關于“遊戲”的争議仍在繼續。
被改變的孩子
文潔不會忘記,從去年11月的一天起,她的生活遭遇突變。那天她随手檢視微信的消費流水,發現自六月以來,共計有遊戲支出3000餘元。對她的家庭來說,這不是一筆小錢:她在湖北黃岡市的一農家樂做服務員,每天掙50元;丈夫則在工地做小工,收入也不穩定。
晚上回家,文潔問15歲、上初三的女兒小慧,最近是不是在打遊戲?小慧說,偶爾打。她又問,充錢了嗎?小慧說,是充了一點,但不知道充了多少。
文潔将手機上的賬單甩在小慧面前,指責她不懂事。小慧一梗脖子,與她吵起來,“她說就是她充的,那又怎麼樣呢?”
相似的事情也發生在福建北部某鄉村的張海甯家。2020年夏天,張海甯偶然查出,自己的一張銀行卡在半年間有兩千餘元的遊戲支出。他叫來10歲的兒子洋洋嚴問了一番,洋洋吞吞吐吐地承認,“一次充五十、一百的,充了許多次,還把扣費短信都删除掉了。”
從此,張海甯明令禁止兒子玩手機遊戲,兒子口上答應,“實際上在想盡辦法偷玩。”家裡是以鬧得雞飛狗跳。
張海甯有兩台退役的舊手機,雖不插卡,連着無線網絡也能使用。為免兒子偷玩,他将舊手機藏在櫃子裡、罐子裡、衣服裡。但都被兒子翻出。兒子還會以讀學校通知、查學科作業等理由要來手機。張海甯有事走開,半小時、一小時後回來,兒子稱作業仍未查完。有幾次,張海甯突擊傳回,逮到孩子正是在玩遊戲。
“能怎麼辦呢?最多就是批評兩句。”張海甯說,“小孩說有作業不會做,要用手機上網查,我總不能不給他查。”他唯一欣慰的是洋洋還算“乖巧”,被批評時,“就看看天,看看地,從不回嘴。”
文潔則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絕望”。與女兒因遊戲消費吵架的第二天,收工回家的丈夫聽說事由,氣得發抖,動手打了女兒。
家庭沖突就此爆發。女兒絕食近一周,被送入醫院打營養吊針。出院後,女兒“像徹底變了個人”,不愛說話,總把自己關在房間内玩手機,“飯也不吃,澡也不洗。”喊她吃飯,若她正在打遊戲,便會“發狂一樣地喊叫”。半年來,她在全縣的成績排名從一千多名掉到近三千名。
今年四月,文潔為女兒洗衣服時,無意中洗壞了其留在牛仔褲口袋裡的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她同學給她的遊戲賬号。”女兒抄起一個凳子,摔裂了,又對着文潔大罵一些“非常髒的話”,便摔門而去了。
文潔很心碎。在她的印象裡,小慧剛讀國小就會掃地、擦桌、給自己煮面條吃,還會和她一起編鞋子賣,以補貼家用。文潔在農家樂做服務員,一個月隻歇兩天,每天端菜、清潔十幾個小時,回到家往往精疲力竭,小慧會給她打水泡腳,“甚至把我腳捂在懷裡取暖。”
而今,女兒變了,文潔認為,是電子遊戲改變了女兒。
年輕人在網吧上網。圖/IC photo
“瘾”從何來
五年前,張海甯居住的村落連入無線網絡,村裡的孩子逐漸“一堆一堆地”窩在各家的牆腳,“抱着手機蹭wifi。”他的兒子洋洋是什麼時候加入其中的,他也不十厘清楚,隻知道兒子玩的是一種“打來打去,非常刺激”的遊戲。
自兩年前禁止兒子玩遊戲起,他便察覺到兒子的學習專注力在逐漸下降,“以前小孩回家第一件事是做作業,現在回家磨磨蹭蹭,找到機會就要問我借手機查作業。”有幾回,張海甯小睡過去,醒來已是淩晨,發現孩子依然在客廳“捧着手機寫作業”。
上周,兒子提出自己考了一門一百分,想玩手機,“我老婆同意了,把手機給了他——我說你考一科一百分,就要玩手機,那麼如果考兩科三科呢?好好學習怎麼能附帶條件呢?”張海甯将手機收回,孩子“跳來跳去,大哭起來”。
張海甯總結,兒子對遊戲“入迷”了。
文潔記得,大約兩年前,女兒的學校因疫情的緣故開始上網課,她便把一台舊手機給女兒使用。至于女兒是否從此開始玩遊戲,她未曾留意。唯一的迹象出現在去年6月,有朋友告訴她,她的微信号顯示在打一款推塔類遊戲,應該是她的女兒在操作。但她想着,“學校裡學習累,休息的時候,玩玩就玩玩了。”便沒作幹涉。
直到“充錢”事發,她才發覺,從前連電視都看得不多的女兒,對遊戲的“瘾”已非常大,“整天整天地想着要更新、要闖關。”
她試圖詢問女兒沉迷遊戲的原因,女兒回答,所有的孩子都喜歡玩。
“遊戲裡面的級别、目标都非常清楚,打掉這個怪就能升一級,設定一個小小的目标,實作之後不斷地獎賞,能刺激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尚俊傑曾分析,人們之是以熱愛玩電子遊戲,是享受随之而來的生理性的刺激。
香港大學人類學博士饒一晨曾做過與“網瘾少年”相關的田野調查。他回憶,彼時他所接觸的“網瘾少年”多沉迷于“高度競争的遊戲”,如槍擊類遊戲、推塔類遊戲等等。
他說,當下許多熱門遊戲的設計,“利用了人類神經的弱點”,每一場遊戲都給人“短、平、快”的刺激,而孩子更難抵擋這種刺激。相應地,孩子就容易陷入電子遊戲無法自拔。
2021年7月28日,上海,暑假期間小朋友們在一電子賣場内玩網絡遊戲。圖/ IC photo
“其實那些十幾歲的孩子,普遍是具備中上的認知水準的。”饒一晨說,他與“網瘾少年”們交流,發現他們多數能客觀認識到自己在電子遊戲上花費了過量的時間或金錢,“就是忍不住。”
他觀察到,來自家庭與社會的壓力,也常是導緻青少年沉迷遊戲的原因之一。“許多孩子受到的教育,是必須獲得好的成績、念好的學校,才能獲得家長和社會的認可。他們被迫在這樣一條競争賽道裡,所得的成績與家長與社會的期待是有差距的。是以,他們會在快速獲得正向回報的遊戲世界裡尋求安慰。”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豔曾帶領團隊對一萬餘名未成年人進行調研,她發現,家庭環境對于孩子的遊戲态度亦有影響:在民主型的家庭環境下,孩子沉迷遊戲的比例為1.7%,在專制型家庭,孩子沉迷遊戲的比例為9.7%,而在放任不管型的家庭,這一資料比例則高達11.7%。
極偶爾,張海甯會與兒子交流手機遊戲,“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喜歡玩遊戲?他說在遊戲裡可以打槍、打仗,會有‘成功的喜悅’。”
但他仍自稱堅決不允許兒子玩電子遊戲:“即使你在遊戲裡有再大的成就感,你學到的東西也都是沒用的。”
文潔則分析:“大概就是遊戲故意設計得會讓人有瘾?”這讓她憤恨。采訪過程中,她總是忍不住發問:為什麼不禁止遊戲?
“防沉迷”的二十年
實際上,中國早在二十年前便開始對青少年人群的電子遊戲活動進行監督管理。
從2002年起,國務院、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部門陸續出台有關政策,例如“網際網路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機關不得接納未成年人進入營業場所”“将未成年玩家的‘健康遊戲時間’設定為3小時以内”“各網遊營運商投入使用防沉迷系統”等等。
然而,最初這些嘗試效果甚微。有媒體發文分析,早年,因各個遊戲公司沒有向公安部調取、核驗身份證号與姓名的權限,政策要求建立的防沉迷系統無法做到百分百的實名制,“(未成年人)網上随便找個身份證生成器,或者找父母、親戚、門衛大爺随便借個身份證輸入一下,甚至網上還有販賣成年人資訊幫助新增賬號,即可輕松跨入成人世界。”
近年來,多家網際網路公司與公安部就身份認證系統達成合作,情況有所改觀。
2019年10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關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提出“每日22時至次日8時,網絡遊戲企業不得以任何形式為未成年人提供遊戲服務”“8~16周歲使用者,單次充值金額不得超過50元,每月充值金額累計不得超過200元”等要求。
2021年8月30日,國家新聞出版署再發《關于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下稱《通知》),提出“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節假日每日20時至21時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服務”“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實名注冊和登入的使用者提供遊戲服務。”
這被業内稱為“史上最嚴防沉迷政策”。
據中國音數協遊戲工委的最新報告,2021年的防沉迷新政出台後,超八成受訪家長表示孩子玩電子遊戲的時間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其中43%的家長稱“明顯減少”。另外,根據南方都市報調查問卷,去年8月的《通知》釋出後,“每周玩遊戲1-3個小時”的學生占比下降了4.36%,“不在網絡遊戲上有所花費”的學生比例,從87.06%上升到90.17%。
為配合政策,國内大型遊戲公司如騰訊、網易紛紛推出家長監督平台。例如,家長們可以通過騰訊“成長守護平台”綁定孩子的遊戲賬号、實時監督孩子的遊戲行為。有騰訊内部人士介紹,系統發現實名為成年人的賬号有疑似未成年人的行為特征,會在遊戲登入或消費時,要求人臉識别認證;針對55歲以上實名使用者的夜間登入行為,系統也會啟用人臉識别,以防止未成年人冒用家長賬号或裝置等。
文潔在家長監督平台上将女兒小慧的遊戲賬号設定成了青少年模式,凡用此賬号玩遊戲,時長不能超過兩小時。然而,今年初,她發現女兒借用了别人的賬号打過一次推塔類遊戲。
張海甯近來聽人說了,“小孩子給遊戲充錢需要人臉認證。”他的兒子洋洋再未有過電子遊戲消費,也不再玩從前那款“打打殺殺”的遊戲,轉而玩一款“砍樹、蓋房子”的遊戲。
他說,兒子在手機上密密麻麻裝了兩頁應用程式,“是以我想,就算有些遊戲有時間限制,但他總能找到能玩的東西。”
2021年7月28日,小朋友在商場内玩槍擊類遊戲。圖/IC photo
正确應對和引導
時代變了,文潔感慨。
她小的時候,與夥伴的娛樂局限于跳繩、踢毽子等活動,要不就是上鎮裡、縣裡去逛街,“連電視都很難看到。”張海甯也有同感,他童年時做的遊戲,無非是下河摸魚、玩水,或是自制兩把木頭手槍,扮解放軍打仗。而今,他們的孩子從出生起,就沉浸在電子科技與網際網路的汪洋之中。
家長們對未來充滿擔憂。
張海甯想,等兒子念到中學,總要給他配一台手機,“現在這是必需的工具,沒手機,人就和瞎子一樣。”至于後續的遊戲時間管理,“隻能靠孩子自覺。”
文潔則說,自己從未想過沒收女兒的手機,“沒收是不現實的,現在哪個孩子不玩手機?而且總要讓孩子和同學在QQ上聊聊天。”她所希求的,不過是孩子能從電子世界裡留出時間,“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該念的書念好。”但她心裡沒有主意,盼着孩子“能變得懂事”。
“孩子沉迷遊戲的‘鍋’不應該隻甩在家長身上。家長和孩子一樣,都不了解遊戲的多元性、複雜性,他們通常覺得所有的遊戲都是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怎麼判斷什麼遊戲是好的、是應該讓孩子玩呢?”學者劉夢霏說,“他們隻能寄希望于,孩子徹底遠離電子遊戲,什麼遊戲也不玩。這在現代社會是不可能的,是以,留給家長的都是無力感。”
2015年,劉夢霏在北京師範大學開設了國内第一門遊戲研究課程“遊戲研究與遊戲化”,緻力于電子遊戲研究及去污名化。
“現在我們講到電子遊戲,就說是電子鴉片、電子海洛因,實際上,遊戲産業是很複雜、很多元的。”劉夢霏認為,市面上的遊戲可分為賭博遊戲、消費遊戲、作品遊戲,不同類型的遊戲應有不同的管理辦法。
“我覺得,賭博遊戲,也就是市場上常見的抽卡遊戲,國家應該禁止青少年觸碰,因為這種遊戲的核心機制就是賭博。”劉夢霏解釋,“而那些免費下載下傳、道具收費的遊戲,我歸為消費遊戲。它的核心是一套消費與社交系統,比如孩子在遊戲裡買皮膚,隻是在朋友面前顯得好看,但遊戲能力并沒有變得無敵,沒有因為消費而在遊戲體驗上碾壓其他玩家,這是消費遊戲的平衡之處。是以,就像吃零食一樣,孩子可以适當地玩消費遊戲——但孩子也不該隻玩消費遊戲。”
劉夢霏認為,對孩子真正有益的是作品遊戲,“一種能帶來精神觸動的,有知識、文化與審美表達的遊戲。”她舉例道,她玩過一款武俠類遊戲,玩家需要學習“宮商角徵羽”的音律知識,若要在遊戲裡掌握醫術,還需背誦一張古代的人形穴道圖。又比如,她小時候常玩的一款航海系列遊戲,玩家可以坐船前往地球上未知的海域,遊戲中,既有“大航海時代的人物的主觀能動性的表達”,也有“對曆史和曆史人物的學習”。每次考試前,她都會玩此遊戲來整合記憶地理知識。
但資訊化飛速發展的二十餘年以來,市面上消費遊戲、賭博遊戲大行其道,真正的作品遊戲已十分罕見了。是以,劉夢霏表示,在監督設定防沉迷系統之外,有關部門也應适當給予作品遊戲一定的支援,“比如給更多版号、扶持建立資料館、在更多學校開設更多遊戲教育學科等等,讓遊戲教育和遊戲研究擁有一個更正規的體系。”
“電子遊戲的出現是時代潮流,我們不應該逆潮流而行。如今,要杜絕青少年接觸遊戲已經不可能了。我們能做的,就是讓學校給予孩子正确的遊戲教育,培養他們的遊戲審美、遊戲時間觀、遊戲消費觀,讓他們認識到,什麼遊戲是好的,什麼遊戲是不好的。這樣,社會上所謂的網瘾問題,或許會大有改觀。”劉夢霏說,這也能改變家長群體的無力局面。
另一方面,短期内,家長們用自己的方式試着改變孩子。
張海甯在家裡支了張乒乓球桌,空下來就和兒子打球。他實際上是個忙人,照料着家裡幾畝地之外,還常常要做砍毛竹、挖竹筍、腌魚幹等活計。“孩子放假一個人在家呆半天,可能就看半天的電視,或是玩半天的手機。”他決意要多陪陪兒子。
與女兒起沖突之初,文潔整夜裡睡不着覺,“想死的心都有了。”後來她查閱到網上的教程,在平台上申請退得女兒充值的三千餘元。五月份,她又在平台心理咨詢師的建議下,為女兒寫了兩封信,折起來放在女兒的枕頭上。
她在信裡折中地寫道,“媽媽不要求你多的,就要求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好之後,你想休閑玩手機,你就玩吧……”
女兒回家後,讀了信,與她談了一番。第二天,她領着女兒到縣裡逛街,在奶茶店又深談一番。她覺得女兒“好像是聽進去一點了”。
女兒開始有些“原來的樣子”,“至少願意和我說話,願意吃飯、洗澡,能把自己拾掇幹淨了。”母親節當天,女兒送了她一張賀卡和一個發夾。發夾是金色質地的,嵌了十多顆大紅珠子。文潔感到久違的寬心。
母親節當天,女兒送了文潔一張賀卡和一個發夾。受訪者供圖
不過遊戲是仍然在玩的。文潔說,女兒最近換了胃口,玩起一款卡通風格、跑來跑去的遊戲。她對此毫不了解,女兒對她說,那是一款“冒險小遊戲”。文潔遵守約定,預設了女兒的遊戲權利。
5月27日,文潔接受采訪的夜裡9點多鐘,女兒就在隔壁房間展開着她的“冒險”。
(文潔、張海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