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周,那部旁白會不停嘲諷辱罵玩家的遊戲《史丹利的寓言》——的超級豪華版發售,并在短短24小時内突破十萬銷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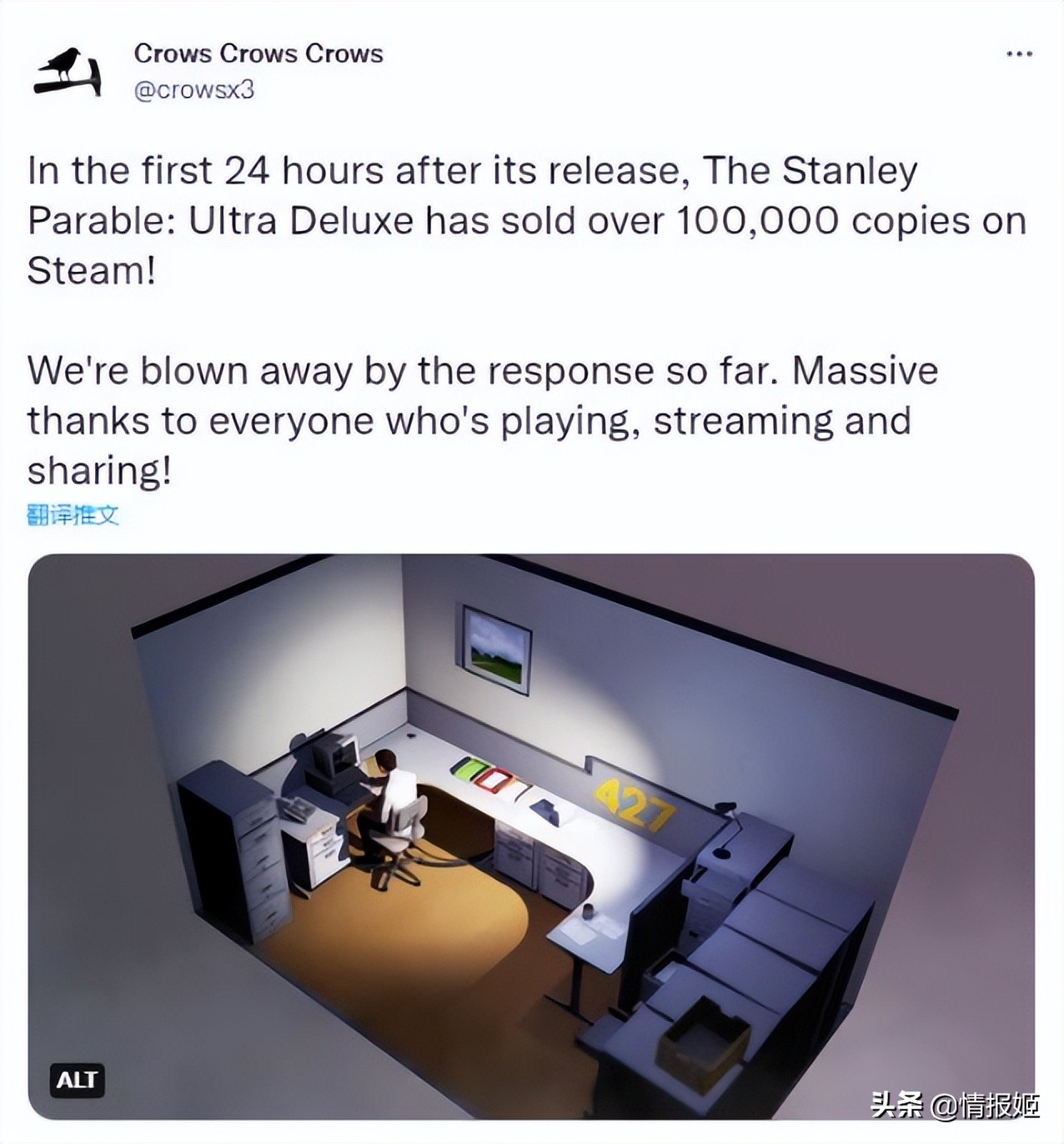
(“在遊戲發售的24小時内,《史丹利的寓言超級豪華版》銷量已經超過10W!我們被迄今為止的反響深深震撼。非常感謝遊玩、觀看直播和分享的每一個人!”)
為此,開發商Crows Crows Crows還拍了張整活照慶祝。
《史丹利的寓言》本是一部9年前就發售的、畫質像古早CS的“FPS”遊戲。而上星期發售的“超級豪華版”,畫面并沒有經過重制,玩法也沒有經過翻新——它隻是在原版遊戲上新增了一些演出和劇情(和跳躍功能),就拿下了24小時内破10W銷量的恐怖成績。
(給滿分的理由:能跳了!)
一個低成本小遊戲能受到全球玩家如此狂熱追捧,不是因為别的,正是因為它将“Meta GAME”這個門類玩出了花。
毫不誇張地說,《史丹利的寓言》從根本上改變了電子遊戲這一藝術載體的固有範式,粉碎了遊戲設計與叙事方法論的條條框框。隻因為,它試圖透過螢幕,讓坐在發光機器前沉迷敲打按鈕的你,成為這場充滿譏諷、不羁與叛逆味的虛無賽博戲劇的主角。
這就是Meta Game的魅力所在。
所謂Meta Game,簡單來說,就是包含了“将虛拟世界與現實世界連接配接起來的橋段”的遊戲,一般譯作“元遊戲”。普通的遊戲試圖把你往螢幕裡拽,元遊戲則總是試圖從螢幕裡爬出來。
在Meta Game中,有的遊戲會出現一些颠覆系統底層的演出,有的角色會意識到自己是遊戲中的人物,有時候連電腦前的玩家也會被視作故事的一部分。總之,Meta Game中的Meta要素,都是些會打破玩家對電子遊戲的“固有觀念”的玩意。
(《失控玩家》的GUY,就意識到了自己隻是一團代碼)
如果你常年關注獨立遊戲行業,那麼在2022年的今天,你可能已經對Meta或者“打破第四牆”之類的玩意感到膩味了。畢竟近十年那些優秀到破圈的小遊戲,總是都沾點Meta元素。
Meta題材看似自由,但實際上已經被許多優秀的“前輩”立下了範式。其中許多遊戲對Meta要素的應用方式,更類似于把它當做一部長篇推理小說的謎底,是“一次性”的驚喜。畢竟Meta Game并不像其他類型的遊戲那般有更多循規蹈矩的創作方式,它最要求的就是“創意”。
久而久之,逐漸趨同的Meta設計,總會讓玩家對突如其來的“神展開”失去敏感度。
(不會再因為唐突死人而一驚一乍,全都多虧了這位獻上的神展開)
為了仔細探讨Meta要素在遊戲中的運用效果,我們可以來回顧分析一下近幾年那些優秀的帶Meta要素的遊戲都是如何巧妙運用破牆武器,來給玩家留下深刻印象的。
首先,Meta要素,大多從三種角度影響一部遊戲。
第一種,是利用類似叙述詭計般“欺騙”玩家的關卡設計,來實作“純遊戲性”上的Meta。
例如幾年前被譽為神作的《信使(The Messenger)》,遊戲開始時是經典的紅白機8bit畫風,玩法也是線性的類忍者龍劍傳橫版過關模式。但在到遊戲中期,經過某個特定劇情節點後,整個遊戲會大變樣。遊戲畫面會從8bit直接變成16bit(音樂也會從8變成16),而線性闖關玩法也會直接颠覆,變成類銀河城玩法。
(8bit畫面在遊戲中期特定節點後會升維打擊變成16bit)
再來看看2013年大受好評的《進化之地(Evoland)》。
乍看之下,這是一個普通古早RPG的模闆的遊戲,但遊戲中玩家獲得的道具并非一般的裝備消耗品,而是一項一項遊戲系統機制。最開始,玩家需要獲得“左鍵”才能向左移動,獲得“遊戲音效”後遊戲才有了SE,獲得“滾動地圖”後畫面才可以時刻跟蹤角色。随後一步一步獲得“16位色彩”讓黑白畫面變成彩色,獲得“第三次元”讓2D遊戲變成3D遊戲……
(進化之地,從黑白像素遊戲一路進化成3D遊戲)
這類遊戲創意毋庸置疑相當優秀,但也通常給人一種“為了展現這個Meta創意,而特地做了一款遊戲”的感覺。
這些遊戲的所有玩法,都是圍繞一個核心Meta要素設計的,隻有Meta出現時能夠帶給人足夠的震撼,但用于支撐這份震撼的遊戲玩法,絕大部分時候隻能說“勉強達到了基本要求”。
《信使》盡管在遊戲中期轉變成了類銀河城玩法,但演出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銀河城遊戲所注重的地圖探索與一些精巧的鎖鑰設計,在《信使》中是幾乎沒有展現的。《信使》角色單調的成長設計限制了收集品的豐富度,也無法避免像法環大後期一樣讓人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它的銀河城僅僅是粗暴地标記一個目的地,玩家前往過程中順路清理掉橫版時期沒走過的路,屬于“形式主義銀河城”。《進化之地》也是一樣的。
(《Fez》)
更早時候,有一部被譽為獨立遊戲巅峰之一的遊戲《Fez》。這部遊戲将“次元”當做了遊戲内的設定,一開始玩家是一個隻能感覺平面的生物,但随着劇情發展到大後期,玩家會獲得對三維的感覺能力,從此,原本橫版的世界,能夠通過第一人稱視角切換,被玩家觀察到其3D姿态。可以說,《Fez》就是這類“升維Meta”的老前輩之一了。
(從橫版2D切換為第一人稱3D視角)
但《Fez》雖同為遊戲性Meta,卻不僅僅隻着墨于Meta演出。《Fez》創造了一套極度詳細、完整且晦澀的世界觀,和大量為三維演出設計的新謎題新玩法,為遊戲中的二三維玩法鋪墊了足夠的厚重感。通過三維視角,以前走過的每一個角落都是全新的世界,都可能藏着新的秘密。這樣的Meta才是融會貫通的Meta,才是能最大限度擺脫“一次性驚喜”拘束的Meta。
(不少UP去研究Fez中出現的自創文字,還做了文字對照表)
第二種類型,是一開始就将Meta要素本身當做遊戲核心玩法與體驗的一部分,并貫穿始終的遊戲。一切因Meta而生,也因Meta而死。比起注重在系統上颠覆前面流程來給人震撼的第一種Meta類型,第二種類型會更注重人“機”互動的體驗。
它們通常會塑造一些人格化角色充當玩家與遊戲溝通的橋梁,用直接明了的方式給玩家一種“在遊戲中玩遊戲”以及“與遊戲制作者博弈”的體驗。
例如剛才提到的《史丹利的寓言》,在基本遵守步行模拟器的架構下,玩家最主要的體驗全部來自選擇遵守(或違反)風趣幽默的旁白事先做好的“訓示”。由此玩家與遊戲産生互動,得以獲得持續探索辦公樓的驅動力。而史丹利也是這類風格的鼻祖,我們可以暫時把這個類别下的遊戲都稱為“史丹利like”。
(史丹利的寓言超級豪華版的新獎杯:“十年内别再打開這個遊戲”,已經有3.3%的玩家去2032年完成了)
又例如2020年獲得了Aggie(Adventure Gamers)獎的5個評委選擇獎的《這裡沒有遊戲:錯誤次元(There Is No Game: Wrong Dimension)》,玩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把遊戲不讓你做的事全部做一遍,然後享受旁白破防破口大罵的樣子,繼續期待接下來還能怎麼“頂撞”遊戲。
(我偏要)
再例如上個月一經發售便大受好評的《勇者鬥幺蛾(tERRORbane)》,玩家的一項主要任務,也是跟“開發者”對着幹,尋找被刻意嵌在遊戲裡的無數BUG,然後嗆死“開發者”。
(同時也融入了無數遊戲著名梗)
在這些Meta Game中,玩家和遊戲的絕大部分互動,都建立在玩家與“旁白”那些直白的互相回報之上。玩家做的“荒唐事”會直接且迅速地反應到遊戲中,也能立刻得知這麼做的後果。而驅動玩家持續玩下去的引力,其實更多來自于“看看你們還能給我整點什麼狠活”的逆反心與好奇心。
不過,“狠活”是不長久的。盡管吸引玩家持續玩下去的絕大部分動力都來自于看狠活的“獵奇心”,但這些遊戲之是以脫穎而出,不是因為狠活多,而是因為它們還在“整活”的基礎上完整地講了一個有深度、有起伏的故事。
這些故事,有的充滿了對虛拟與真實世界裡自我認同的哲學探讨,有的試圖和你分享一個被壓榨的獨立遊戲制作者落魄且迷茫的人生,也有的隻是想拉着你來一場迪士尼風格的合家歡大冒險。但無一例外——它們都展現了一些遠高于遊戲視角的人文關懷,展現了一些通過Meta才能探讨的文學性核心,展現了一些符合Meta氣質的、觸及形而上與假唯物界限的光芒。
(《艾希ICEY》)
盡管如此,史丹利like領域目前依然是個誰先上誰吃香的藍海,對Meta以外的領域也有許多價值。“和旁白對着幹”的藝術與腦洞仍然還有着許多發散方向,比如俄羅斯人做的《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就是個處處展現史丹利核的遊戲。
(THE BIG RED BUTTON)
再來說第三種類型。在以“劇情”為核心的遊戲中,它們通常将一些瞬間超脫玩家了解的突兀的Meta要素,當做推動劇情進展的關鍵線索。很多時候,遊戲不會直白地提示玩家破局的關鍵。如果玩家沒有從慣性思維中脫離出來,就永遠“悟”不到,解開線索的鑰匙很可能不在遊戲裡,而在現實中。
例如鼎鼎大名的《傳說之下(UNDERTALE)》,為了達成完美結局,需要玩家“不殺死任何一個生物”,這是一周目玩家不太可能想到的。而如果走了殺盡一切的屠殺線,遊戲裡的某位角色甚至能夠檢測玩家的存檔資料,并永遠會記得你雙手曾沾滿鮮血。玩家也無法再進入真正的完美結局(除了卸幹淨重裝)。
再例如另一部小衆但與《Undertale》齊名的《OneShot》。
這部被譯作《一次機會》的遊戲簡直就是Meta的遊樂場,從頭到尾充斥着極度華麗且契合劇情的強悍Meta演出。
玩家不僅要根據劇情進入自己電腦的“我的檔案”裡尋找隐藏的密碼,還要将遊戲視窗移出螢幕邊界來制造“暗室”以“沖洗照片”,甚至還要像小時候讀《冒險小虎隊》系列一樣用解密卡一樣的另外一個程式疊加在遊戲視窗上,才能知道正确的道路。
(将兩個程式疊在一起,才能訓示正确的路)
(不停驅趕玩家進入遊戲的對話框)
而這一切,全都是和劇情進展緊緊相連的,因為在《OneShot》中,玩家是确實作為一個角色參與到故事中的。玩家的幹預,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再例如各位都非常熟悉的《DD文學俱樂部》,和它的祖宗《君與彼女與彼女之戀》。
在這兩部看似正常普通的“戀愛GALGAME”中,其實每個角色都能透過螢幕得知玩家的存在。她們明白自己隻不過是遊戲中的角色,也知道自己不過是由一串串代碼控制的資料團。她們會肆無忌憚地殺人或自刎,會銘記你前世的選擇(讀檔記錄)。她們甚至能像病毒一樣肆意改變玩家的桌面,能藏起自己的開始程式。這些神展開相當猝不及防,但細想又能發現前面全都是伏筆,非常巧妙。
玩家必須遊戲内外結合,通過遊戲的線索在電腦中尋找解開困局的密碼,通過不限于尋找文檔、更改名字、改變檔案位置、删除角色資料(殺死角色)等方式來推進劇情。
無疑,不按正常出牌的Nitroplus發售了這部《彼女與彼女》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這種帶有如此硬核Meta要素的R18遊戲震撼了整個GAL業界。而且N+不僅是為了吓唬玩家整的活,還真的為此寫了一個殘缺且傷感的浪漫愛情故事。後來不少廠商模仿這種模式推出了自己的遊戲,但沒有再能超越經典的了。
還要刻意強調一下橫尾太郎這位老逼登,他如今最為大衆所知的傑作,就是《尼爾:自動人形》E結局中玩家化身黑客飛機爆射所有STAFF,并在動聽的《Weight of the World》中獲得來自平行世界玩家的生命(存檔),在衆多不知名的守護中抵達結局。最後,玩家也能選擇獻出自己的存檔,幫助其他受困玩家拯救幾位主角的生命。
這樣的Meta設計實際上是對玩家的一種“道德綁架”,悄悄讓玩家産生了對尼爾玩家群體的集體榮譽感。所有玩過這個遊戲的人就算不在乎劇情邏輯,也能在同伴一一為你赴死之時體會到已經超脫遊戲的大我合一。
可惜就可惜在,如果事後仔細認真回想,不去查閱其他文獻設定的話,你是真的搞不懂自己到底怎麼救了2B9S的,也搞不懂為啥有那麼多存檔源源不斷替你去死的。也隻有橫尾太郎能塑造出這種“過程很感動,賢者時間才懵逼”的神秘演出了。冷靜下來後,隻能怪罪自己太年輕被騙了眼淚。
最後還要特别聊一聊打越鋼太郎在NDS上發售的《極限脫出999》,2009年的Spike為了契合NDS的上下屏機能,在這部遊戲中設計了一個到現在都被行業所驚歎的絕妙Meta演出。
熟悉打越的人可能知道他的名作《Ever17》。他最擅長玩的就是“儲存記憶跳躍世界線”的那一套,并講究一個叫做“形态形成場理論”的“僞科學”。意思就是說,就算跨越時空,兩個有超能力的人也能通過一種叫做“形态形成場”的力場進行心靈感應。
而《極限脫出999》的結局中,男主角為了拯救“九年前死去”的女主角,需要通過跨越時空的心靈感應,在時間限制内把解謎得到的資訊發送給九年前的女主角輸入。此時,上下螢幕分别是男女主跨時空的對話。
(下屏為女主角,上螢幕為男主角)
接下來,為了突出男主角“傳送資訊”的過程,NDS的上下屏此時此刻甚至被颠倒過來,代表着第一人稱的切換。數獨遊戲得到的數字就是九年前的密碼,密碼必須及時傳送給九年前的女主輸入。兩個時空通過這種方式被連通。這就是本作将NDS上下屏演出發揮到極緻的、最終的解謎。
(得益于NDS上下屏特性才有的颠倒數獨,這裡需要玩家親自翻轉NDS)
以上這些以劇情體驗為核心的遊戲,其加入Meta要素的方式與關聯的玩法,都是死死貼緊劇情、甚至直接讓meta充當解開劇情困境的最大推動力的。這麼做有時候能塑造一個令人驚喜的神展開,也有時候會讓劇情變得兒戲且都合主義,充滿機械降神嫌疑。但無論如何,它們都大幅增強了作品關鍵情節的演出效果,至少在某個瞬間,讓玩家起了雞皮疙瘩。
隻要有這麼一個場景,玩家就會永遠記住這部作品。
上述三種Meta Game的套路,基本涵蓋了市面上大部分元遊戲的模式。它們最為重要的一點共性,也許是它們并非僅将亮點都留給了Meta,而是借助Meta,表達了更多個人的、深層次的精神核心。Meta對于優秀的Meta Game而言,更多是一種增添色彩的叙事工具,一種用來展現精神核心的“修辭手法”,而非單純隻是個唬爛噱頭。
當然,最近還有像《邪惡銘刻》這樣論外的徹底放飛自我的驚奇之作,甚至結合了許多ARG要素。不過這部遊戲實在太過特殊,更像是一場探讨電子遊戲邊界的行為藝術。
這個時代,越來越多的遊戲制作者通過破牆來表達自己對虛拟與現實交界的思考。這些燃燒的靈魂透過螢幕對玩家發起挑釁、質問與批判。但在散盡火光與餘晖之後,他們仍舊恪守本職,陪玩家玩完這場賽博家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