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耿朔、仇鹿鳴編《問彼嵩洛:中原訪古行記》(中華書局,2019年),本為随筆,行文随心,交稿逾年,對文中的個别問題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所涉及的文物亦獲得朋友們襄助不少照片,故修訂增補成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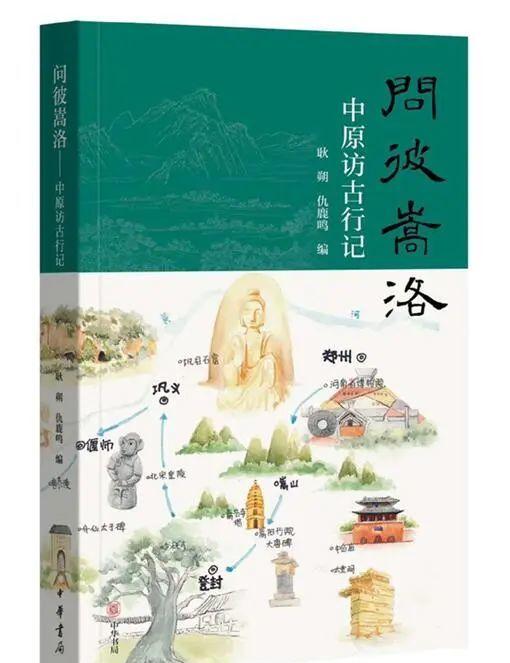
《問彼嵩洛》書影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們在中原腹心的河洛之地進行了一次為時不長不短的考察活動,具體情況,本書的前言和朋友們的文章中已有記述,這裡就不再饒舌了。我願以兩位主編的信譽起誓,這決不是為了偷懶的緣故。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直到别人告知我:要寫文章!烈日下一切鮮明的回憶立即變成了永垂不朽的顔色,看來文字确實标志着主體的死亡,正如我們此次看到的衆多墓碑和墓志,它唯一的好處就是讓死亡可以被長久地欣賞。為着讓風花雪月多活幾天的善良願望,我成為了拖稿勢力中最頑固的一員(後來得知還不是最最頑固的)。然而,我這顆善心實在經不住那些已經完工了死亡大業的魔鬼們的百般引誘和揶揄,現在讓我放下輕松的鵝毛筆,拿起沉重的鐵鑿,雕刻我此次考察的墓碑。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堕,心亦不能為之哀。”中國古代的建築,其主體一直是土木,秦漢以來一些特殊的建築(喪葬、紀念)多用石材。我們此次考察的對象主要是漢唐時期的古迹,一兩千年的地火水風,石材尚且剝落生苔,木材更極少能夠儲存。土中的雪泥鴻爪則需要仔細辨認,往往要親手清理才能有較為清楚的認識,也就是考古工作者經常标榜的“土中找土”的技藝。我們的匆匆一瞥,焦點自然主要在大型的夯土工程(如城牆、宮殿基址、封土等),更主要在号稱永垂不朽的石刻上了。關于碑志,有更專業的朋友們關注,這裡談一點我較熟悉的漢代石雕方面的問題。由于考察活動已經過去一段時間,總體過程和具體細節的記憶已不能連貫,這裡也不是寫論文,不必集中在一點上,征引辯論。姑且讓文字作思想最忠實的記錄,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吧,美其名曰“漫憶”。其中必然有許多不能嚴謹之處,所涉及的問題也不能回顧和伸展,隻是由回憶促發的當下思想的流水賬,想到問題時“莊”,談到感受時“諧”,望讀者一哂而已。
一、中嶽漢三阙
漢阙結構示意(以四川大邑出土天門畫像磚為例,其上門吏為阙前守衛,不屬于阙身)
《說文解字》中說:“阙,門觀也。”《釋名》中的說法更符合漢代經師的套路:“阙,阙(缺)也。在門兩旁,中央阙(缺)然為道也。”不論怎樣辯論名實,阙事實上就是一對門樓,用以壯觀其門,是以往往有一定的等級制度。比如天子用三出阙(每個阙體有從内而外依次降低的相接的三個部分),其下有子母阙(兩個部分)、單體阙,屋檐也有重檐和單檐。已經發掘的漢景帝陽陵陵園的南門阙就是一對三出阙,說明天子之制确實存在。有學者讨論過(由于文稿性質,允許我不去查證征引了吧,後同),按照文獻記載,二千石以上高官的府第方可置阙,然而實際發現的墓阙的使用情況卻比較複雜,平民(一般來說應是沒有官職的地方豪強)也見使用,而且也有用重檐子母阙的。實際的立阙除了身份的限制外,财力的局限恐怕更為重要。山東嘉祥武氏墓阙題記中說:“造此阙,直錢十五萬。”東漢蜀郡屬國都尉(《水經注》中誤作蜀郡太守)王子雅石樓(即石阙)題記中說:“父殁當葬,三女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這對石阙的造價更高達一千萬。漢墓題記多标榜,其上的造價或有水分,不能全信,但毫無疑問的是,一對雕刻精美的石阙必然非一戶普通人家所能置辦。然而墓葬圖像(主要是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中的阙一方面不必擔心禮制上的過分招搖,另一方面造價相對低廉(尤其是畫像磚和壁畫),是以受到東漢墓葬的普遍歡迎,更加沒有制度可言了。四川地區東漢晚期一磚一畫而大量模印的畫像磚可能已經可以作為成品供喪家選用(自由選擇并不是就沒有套路,現在全國的室内裝修也沒太大差别,而我們自認為是絕對自由的),等級制度恐怕更無從談起了。可是,我們在墓葬圖像中卻沒有見到過三出阙,看來在客觀的制度和主觀的心理上還是存在着一些人們不去觸摸的紅線。甚至連墓葬中表現的天門(也用雙阙表示,不少有題記)也是子母阙和單體阙,天界之門應該不會存在僭越人間的罪過,似乎是等級限制了人們的想象力了。
甘肅成縣出土天門銅棺飾(采自《漢風—中國漢代文物展》)
墓葬制度的問題很複雜,尤其在漢代,特别是地下的部分,因墓葬的逾制僭越而受到懲處的事例很多,但基本都是作為政治鬥争中失敗者的罪名出現。有規定未必一定遵守,沒有規定也并非無拘無束,并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若有若無,像是西方極樂世界中的餐盤,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例如,《漢書?王莽傳》中記載王莽在清算董賢家族時,其中的一個重要罪名就是董賢的棺上畫了四象,左青龍,右白虎,至尊無以加,僭越了天子之制。按說起來四象的确是天之象征,董賢你一個男寵,棺材上憑什麼畫四象,死有餘辜,開棺裸屍,滿門抄沒。然而從西漢中晚期的蔔千秋墓開始(西漢中期的梁王墓還算是諸侯王,稍可寬宥),在墓葬中乃至葬具上繪制四象便是常見之事。還有不少繪了完整的日、月、四象、二十八宿的天象圖,相對于董賢的裸屍,就該鞭屍了。怎麼解釋?我們是采取此一時彼一時、此一地彼一地的科學式了解,繪制禮制起伏的時空曲線,還是這個罪名和制度本身就比較玄學?
南陽麒麟崗畫像石墓前室墓頂上日月及四象等(采自《南陽麒麟崗漢畫像石墓》)
還是回過來說中嶽漢三阙,即嵩山中至今尚存的三對東漢石阙。太室阙建于安帝元初五年(118),啟母阙建于安帝延光二年(123),少室阙大概與啟母阙同時。這些皆可從阙上的題記直接讀出來或推算出來。現在能見到的東漢石阙數量不多,但也不算很少,而且基本是墓阙(墓地的大門),中嶽漢三阙卻是廟阙(祭祀場所的大門)。太室(泰室)廟、少室廟是祭山嶽的,屬于自然神祇的神廟;啟母廟祭祀的是夏禹的夫人、夏啟的母親,傳說中在此處化為巨石,屬于神話人物的祠廟(漢代人恐怕并沒有這樣的區分)。不過作為石阙而言,它們與從東漢初期就開始出現的石質墓阙在造型上、圖像上并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圖像的問題容後再談),不必分開來談。
少室阙東阙(作者攝)
少室阙西阙(作者攝)
漢三阙從形制上講,有一定的地位。文獻記載中在四川梓潼有光武帝時期修建的李業阙,然而其本體或已不存,現存的一石及題刻或許是出于後人僞托,尤其是頂蓋,十分怪異,不可輕信。按:我們前幾天去川北考察的途中,正好尋訪了李業阙,問了許多當地人都不知道,好不容易才找到。細讀上面清代人的題記,可知頂蓋确實是後配,阙體的埋藏和出土過程卻比較清楚,而且屬于清代人的“主動性發掘”,可信程度較大。阙體更像石碑,但上下四角有類似建築結構的裝飾,介乎碑、阙之間。若是原石,便是我們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石阙了。正面下部為清代人關于其來龍去脈的詳細記述,上部題名恐怕也是後代人題刻的。
梓潼“李業阙”(頂為後配,作者攝)
早期的石阙多存于山東臨沂:如莒南孫氏阙,建于章帝元和二年(85);平邑皇聖卿阙,建于元和三年(86)左右;平邑功曹阙,建于章和元年(87)左右。此三阙時代、地域極為相近,後二阙形制極為相同,皆較低矮,不足兩米,單體單檐,阙體方正,造型簡單,矮小的鬥拱直接承托屋檐,缺少後來往往稱之為阙樓的部分,圖像皆在阙身,内容基本一緻。孫氏阙僅存阙身,也是單體阙,向上收分,與前二者略有不同,仍然較為簡單低矮。
平邑皇聖卿阙(耿朔攝)
平邑功曹阙(耿朔攝)
而建造于安帝時期的漢三阙就顯得有所發展了,皆為單檐子母阙,阙身更加寬大,高為三四米,鬥拱部分雖然仍不突出,但裝飾已經複雜化了,圖像仍然主要在阙身,也出現在相當于後來所謂的阙樓部分,不過此部分的圖像多為仿建築的連璧、椽頭等較為簡單的裝飾和結構。
太室阙東阙上部(作者攝)
更晚一些的嘉祥武氏阙(桓帝建和元年,147),結構更顯複雜,也有三四米高,重檐子母阙,阙樓的部分已較為突出,圖像滿布于阙身和阙樓,沒有主次之分(隻是阙身畫面更大)。
嘉祥武氏阙西阙(王磊攝)
之後的石阙主要分布于四川(包括後來分出的重慶)。川西(雅安周邊)和川北(綿陽周邊)的形制較為相近,阙體高大(五六米高),有複雜突出的鬥拱部分,體量可與其下的阙身相侔,多稱之為阙樓,多為重檐子母阙,但上重屋檐較小,直接疊壓在下重屋檐上,看上去更像單檐,圖像多在阙樓的鬥拱之間和阙身上部與阙樓相接處,典型者如雅安高頤阙(獻帝建安十四年左右,209)、樊敏阙(建安十年左右,205)和綿陽平陽府君阙。
雅安高頤阙(龐政攝)
蘆山樊敏阙(龐政攝)
綿陽平陽府君阙一(作者攝)
綿陽平陽府君阙二(作者攝)
川東石阙形制多瘦高,阙體向上收分,多為單體阙,其他與川西略同,見渠縣諸阙。
渠縣馮煥阙(耿朔攝)
渠縣蒲家灣漢阙(耿朔攝)
三峽地區的石阙形制更為瘦高俏麗,單體阙和子母阙都有,突出的特色是上下兩重檐的體量相當,距離較寬,分割成兩重阙樓。如果川西的典型石阙隻能稱為單檐,那麼這裡就是标準的重檐;如果川西已稱重檐,也可以稱之為重樓,如忠縣丁房阙、無名阙。當然也有例外,如忠縣烏楊阙就沒有重樓,但仍然十分瘦高,一眼就能看出是三峽地區的漢阙。
忠縣丁房阙(秦臻攝)
移置三峽博物館大廳的烏楊阙(王磊攝)
以上是漢代現存石阙形制的概括印象,因為材料本身就不多,概括也是極不準确的,稍微出現幾例新材料恐怕就要進行重大調整,如果把圖像材料放進去(雖然這樣眉毛胡子一起亂抓也未必好),問題會變得十分複雜。還有不少介乎碑、阙之間的材料,也特别有趣。有讀者會嫌棄我上面講形制太多,然而這是了解文物最為重要的基礎和主要的知識,隻是為着什麼目的講到什麼程度而已。
由上面看來,漢三阙所處的安帝時期,不論從石阙數量和形制來看,都有較大的發展。不僅石阙是這樣,太室阙前站立的東漢石人也是如此(石人的問題容後再談),碑刻亦是如此(安帝之前寥寥無幾,自安帝開始增多,其後極盛于桓靈),曾經有先生講漢代墓葬制度的變化時,也特别點出安帝這個時間點。這些墓葬設施,安帝之前即已出現,緩慢發展,安帝以後勢不可擋,而史書中有一個判語:“自安帝政治衰缺。”具體從喪葬政策來看,衆所周知,自漢初即大行厚葬之風,前期多在帝王和諸侯王,中期以來被及全民,勞民傷财,破家敗業,世風逾下。是以自西漢晚期朝廷就啟動了長期調控政策,成帝永始四年(前13年)下诏禁止厚葬,其後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都曾下诏節葬,似乎成為每朝皇帝一以貫之的國策。而且從正史記載來看,自成帝開始的每朝皇帝(西漢末的特殊情況自然顧及不上)都專門下過一次诏令,而安帝分别于永初元年(107)和元初五年(118)兩次下诏節葬,後一诏書中還說“有司惰任,訖不奉行”(把鍋甩給了下級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後終東漢一代近百年時間中再無節葬诏令頒行了(獻帝時又下過一次,自然應了解為曹魏的政策了)。而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是,漢代的厚葬之風伴随着禁止厚葬的诏書的頒布逐漸高漲,東漢中期以後(大概就是安帝以後)臻于全盛,大型的多室墓、精美的裝飾、地面上的各種設施蓬勃發展。其間三昧,值得品味。
墓阙上還題刻了一些阙的造價(未必真實),東漢早中期的孫氏阙是一萬五,中晚期的武氏阙是十五萬,晚期的王子雅阙高達一千萬。不過我們在這個造價上暫且不要過多追究,一方面從其他材料來看,東漢晚期标榜吹噓之風越來越盛,騙鬼唬人,不必當真;另一方面東漢晚期的通貨膨脹應該是比較瘋狂的,後來劉備發行直百錢(百倍面值),孫權發行當千錢(千倍面值),據說竟然沒有嚴重擾亂市場經濟,也可見一斑。
漢三阙的圖像與時代稍早一些的平邑功曹阙和皇聖卿阙最為接近,隻是由于阙體更大,畫面更多,内容要稍多一些,并在類似于阙樓的部分增加了建築裝飾(連璧、椽頭)而已。總體上也不過是墓葬和墓阙中常見的日月、神獸、出行、狩獵、百戲、拜谒、宴飲這些内容。啟母阙上有一幅一人坐樹下,旁一人持鋤狀物的形象,可能是孝子故事,然而過于簡單,不好确認。圖像的位置群組合上除三阙自身形成的一個傳統外,看不出太多的資訊(記憶中,一阙的部分圖像組合與其他二阙及自身相對部分比照有所錯亂,由于構成阙體的石塊大小相似,可能是後人複原時未能多方比較研究而緻位置錯誤,不太可能是修建時的錯誤,因為石塊不多、分層也少、圖像簡單,當時人出錯的可能性較小)。
有意見認為啟母阙上已經漫漶嚴重的兩幅人物圖像(好像是中間一人呈坐姿,兩旁有二侍者)分别是夏禹化熊和啟母化石的故事,與啟母阙應景。由于一則圖像漫漶又十分簡單,二則整個漢代圖像中還從來沒有這兩種題材可以類比,也無榜題依憑,三則這兩個圖像從整體來看處于宴飲、百戲的場景之中,我覺得就是一般的人物,沒有明顯的特殊之處。這樣說并不是我們就不能識讀出新的題材,而是識讀一個新的題材得有可靠的榜題或者能排他的較為特殊而具有一定複雜程度的圖像因素(這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較能使人信服)。而且總體來看,三阙的圖像嚴格遵守着流行的套路,與同時期的墓阙和墓葬一般無二,并沒有要配合其祭祀對象的意圖。
啟母阙和少室阙的百戲、宴飲圖像中皆有一人舞蹈跳躍于一圓形物旁邊的題材,通常認為是中國最早的蹴踘圖,意義特别重大。啟母阙上該人物長袖舒展,長裙搖曳,其足旁有一較大的圓形物,圓形物似有邊輪。少室阙上的圖像頗有不同,一人長袖仰身似跳躍狀,下身着褲而不着裙,圓形物在其足下,有一圈邊輪,旁有一人坐于幾案旁,一手持竿指向圓形物。這兩個圖像與常見的百戲題材比較起來有一定特殊之處,圓形物在其足前或足下,且漢代已有一些關于蹴鞠的記載,這種看法具有一定道理。不過也還存在一定疑問,原因還是圖像因素太簡單,不具排他性,且無真正确認的圖像來對照。是以,這兩個圖像到底是否為相同題材,具體為何種題材?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可以确定屬于樂舞百戲,蹴鞠可備一說,但真正要确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發現。
啟母阙上的“蹴鞠”圖像
少室阙上的“蹴鞠”圖像
還有三阙上的大象圖像,同訪的朋友都問起我這個問題,看來大家特别感興趣。少室阙和啟母阙上都有一頭巨體長鼻之獸,一般都将它們認作大象,形象都有些怪異。太室阙上也有一頭長鼻之獸,形态更為怪異,是以有人又将它認作“獏”,我認為還是大象這個常見的、也見于其他二阙的題材。形象失真而怪異,一方面是刻畫粗糙抽象(三阙上的圖像皆較粗糙抽象),更主要的一方面應該是當時的一般工匠對于大象還沒有準确的知識所緻。關于漢代的大象圖像,學界已有不少讨論,我以前也做過細緻的分析,涉及文化交流中傳播、接受、了解、附會及運用等許多方面,說來話長,這裡就不贅言了。
少室阙上的大象
啟母阙上的大象
太室阙上的大象
二、石人、石獸
唐代人說:“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是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唐代陵墓前的這些石像生确實是儀仗之屬,但是推之于秦漢就得格外小心了。因為從目前漢墓前的石雕來看,似乎尚無等級制度,二千石高官墓前有,四百石的小縣縣長墓前也能見到,有些甚至懷疑是平民(無官職的地方豪強)墓葬,而且種類和數量也看不出制度化的差别。漢代人自己也說:“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圹,毆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側以禁禦之,而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看來漢代墓前放置石獸,一開始恐怕是出于喪葬信仰,而非墓葬制度。
從文獻記載來看,中國的大型像生石雕出現于秦漢,特别是秦始皇和漢武帝時。記載中的秦始皇和漢武帝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求仙方面确實高度相似,他們都聽說了大人,又造金人,都去東海求仙,又都封禅了泰山(據說與求仙有關),都在苑囿中造了蓬萊仙島,又刻了巨大的石鲸。不知是秦始皇影響了漢武帝,畢竟人家是始皇帝,祖龍雖死魂猶在;還是漢武帝影響了“秦始皇”,畢竟為始皇帝寫本紀的人生活在漢武帝的時代,而且我們相信他在寫秦始皇時餘光正瞄着漢武帝。實際上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早期大型石雕是漢武帝時代的,主要有昆明池的石雕和霍去病墓的石雕(有學者認為是否是霍去病墓可能存在一些誤會)。
霍去病墓石卧馬(作者攝)
霍去病墓石卧豬(作者攝)
正如學者所說,霍去病墓的石雕隻是随石賦形,作為一種山野景觀(據說他的墳墓是仿造祁連山)散置于封土的草叢之中(我剛去看過,感受尤為切實),與東漢以來興起的立于墓前神道的石雕還不是一回事,而東漢墓前的石雕與南北朝以來形成制度的墓前神道石雕恐怕也還有些不同。說到東漢興起的墓前石雕,就不得不注意洛陽地區,因為一則這裡的東漢石雕出土不少,二則這裡是東漢陵墓所在,看看這一制作最初是否與皇家有關。
最有可能是帝陵石雕的當屬孟津的大石象,雖然此次我們足迹未及,但不得不提。石象形體巨大,造型寫實,高有三四米,重二十多噸,位置在邙山陵區南約一公裡處,正好《水經注》中說到光武帝陵前有石象,是以一般把它作為東漢時期的石雕,并可能與東漢陵墓有關。由于沒有其他時代資訊,這個說法到底對不對,目前不能确定。
孟津石象(莫陽攝)
我個人的想法是,如此體量的石雕,如果是墓前之物,基本隻能考慮東漢。西漢陵墓前尚未發現同類石雕,霍去病墓前倒有一個石象,但是随石賦形,十分粗犷,體形也小,又為孤例。魏晉禁斷石獸,雖然仍有一些孑遺,但形制多為小而呆闆的坐獸。北朝陵墓開始恢複石雕,以石人為多,偶有石獸,洛陽地區也是延續魏晉的坐獸,仍然形小而呆闆,如靜陵石獅;關中西魏永陵有站立的石獸,風格簡單粗犷,開初唐之風。唐陵石獸體型高大而精美,但是并無石象,地域也不合适。宋陵那種低矮呆萌的石象又絕不與此相類。明陵前也有高大的石象,不過風格和地域也絕不相幹。東漢大型石雕倒是特别興盛,形體大而精美,不過這些石雕都是地方官吏和豪強墓前的,也沒有見到如此巨大者。如果它是東漢的,恐怕隻能是帝陵之物了。然而,東漢帝陵至今未發現其他明确的石雕材料,是以問題并沒有解決。
霍去病墓石象(作者攝)
宋仁宗永昭陵石象(作者攝)
以上是從墓前石雕發展的大勢來說。從具體風格而言,雖然東漢墓葬中的大象圖像往往失真而怪異,但那多是根本見不到真象的民間藝術,财力也一般。漢代高等級墓葬中也有比較形象的大象,若是帝陵,當然是有能力做出如此高大精美的石象來的。
不過,大型石象除了可能與陵墓關聯外,還可以與佛教藝術關聯。象是佛教的重要瑞獸,許多佛本生和佛傳故事中皆有它的身影,也是佛教藝術中的常見題材。江蘇連雲港孔望山石刻中就有一件體形高大的石象(大概有兩三米高吧),造型有些醜陋,但還算比較具象,一般認為可能早到東漢,總體上與早期佛教有關。
孔望山石象(采自《連雲港孔望山》)
是以,孟津石象的時代判斷與其性質判斷密切相關。如果确實是陵墓前的石雕,時代應該為東漢。但如果是佛教石雕,其時代就未易量了。不過,一方面,自北魏以來,對于洛陽佛寺的勝迹就多有記載,如此巨大的石象恐怕很難不引起注意,當然時過境遷,文獻佚失,誰也不能保證;另一方面,石象所處的地點确實臨近東漢陵墓,而且北魏的郦道元也确實記述東漢陵前有石象。由此來看,我個人還是偏向東漢陵墓說,然而,畢竟是孤例,如果堅持孤證不立的原則,也不妨暫時采取擱置的态度。
說完大象,再說說獅子,東漢墓葬也是獅子雕刻開始出現的地方。現在能見到最形象的一對獅子石雕就與洛陽有關,雖然發現于山東,其後頸上題記為“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師子一雙”。類似的例子還見于山東嘉祥武氏阙前的一對,阙上有題記雲 “建和元年……孫宗作師子,直四萬”。在鹹陽沈家橋、四川蘆山石馬壩、河南淮陽北關一号墓都出土過典型的東漢石獅。這些石獅特征都十分明顯,大多身體較虎粗短,頭部較大,兩頰和後頸上都有獅子獨有的鬃毛,而且都沒有神怪的因素,頭上無角,身上無翼,寫實形象。
劉漢石獅(王磊攝)
武氏阙前石獅(王磊攝)
蘆山石獅(龐政攝)
不過漢代的石獸大多不是這樣,往往頭上長角,肩上生翼,一般稱為天祿、辟邪,洛陽地區就出土不少,我們此次在偃師博物館中見到的正是這樣(也有少數無翼無角的石虎,正如有少數典型的石獅一樣)。有學者将之與古代波斯的頭上長角,肩上生翼的獅形神獸比較,認為應該是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從外形來看,确實特别像,是以我個人一定程度上也傾向于同意。不過二者的地域、時代隔得還有點遠(波斯大約在前5世紀,早了五六百年),其間蹤迹難尋,還有疑問。
洛陽孫旗屯石翼獸(王磊攝)
雅安高頤阙前石翼獸(作者攝)
其實,漢代圖像中還有一類本土化了的走了樣的獅子,正如走了樣的大象一樣。有學者已經注意到,我剛剛仔細讨論過。這類圖像在南陽地區很多,格套十厘清楚,一般畫面中心為兩頭虎形猛獸對峙,其中一隻獸昂首挺胸、張口按爪,不可一世,頭頂有像馬一樣的鬃毛直挺向上、怒發沖冠,另一獸(頭頂無鬃毛)俯首夾尾,臣服于前。我認為那個怒發沖冠的猛獸就是當時人根據傳說改造出來的獅子。正如大象一樣,獅子主要由西域進貢,皇室苑囿中應該有,但是一般人根本看不到。隻是大家傳聞有一種外國猛獸,像虎一樣,頭上有鬃毛,比虎豹還厲害,虎豹見了都要夾起尾巴老實做獸(實際上獅子未必打得過老虎,外來的猛獸好吓人嘛)。大家又不知道獅子的鬃毛到底長啥樣,當然就要從熟悉的馬的鬃毛上來提取素材了。
南陽漢畫像石中的獅子伏虎豹(采自《中國南陽漢畫像石大全》)
這也不是我瞎想,東漢人就說“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鬥”,就是個有髯的老虎。獅子在當時又叫狻猊(狻麑),“狻麑如虦貓,食虎豹”,就是隻大虦貓(虦貓,本來是淺毛虎的意思,大概是說其毛色比老虎淺),而且還能吃老虎。與上述圖像最配合的是一則北魏時期的文獻,說:
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為逆賊萬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诏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并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于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
上述圖像不正是“虎見獅子必伏”、“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的同義詞嗎?不過是用畫不是用字而已。雖然很多時候用後世文獻有很大風險,但我們前面已經有漢代自身的文獻,隻是比較簡略,具體邏輯也能接上,而且這種神化獅子的觀念應該越晚越弱,慢慢見多識廣了嘛,或許還說得過去吧。不過,我們還是要特别小心。研究圖像的如果把文獻丢開不看,錯過了這些風景,屬于過失犯罪;如果濫用文獻,生拉硬拽,就是故意犯罪了。
本來還想說說石人,這也是東漢開始出現并影響後世的一種制作,主要也與墓葬有關,也有其他性質的,中嶽廟前就有一對。可參考的研究已有不少,去年我也正好指導一位同學系統梳理了這個問題,有一些心得。不過寫到這裡主編交給我的字數已經完成,再寫就是目無主編了,我願意這樣認為。
中嶽廟石人(作者攝)
其實,此次考察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東西還很多,從此以後我也立志要多走走看看,有些東西是紙上得來終覺淺,有些甚至紙上就得不來。比如我此次在偃師博物館中仔細看了所謂洛陽地區早期的空心畫像磚墓,畫像磚一詞給我們傳達的預設是與四川地區的那種典型畫像磚歸為同類。可是當我看到這些早期的空心畫像磚時,眼睛的歸類卻與語言的歸類不同,更願意把它們看作畫像石。就是用更為廉價的磚來替代石材,用更有效率的戳印來代替鑿刻,實際是要做出石的效果,是以用以作門楣和門柱。而門扉的形制由于不便燒磚,還得用石材來雕刻,粗看起來,不易分别。且二者本來就是一體,分為畫像石和畫像磚反而多餘(這隻是說洛陽地區早期空心磚墓的情況,并不是說其他時間、其他地域二者也不分别)。而這裡的空心磚墓,實際上就是利用磚來仿建一個石椁,這個“石椁”與山東地區早期的畫像石椁墓既有聯系,又有差別,需要單獨梳理,又需要放到一個更大的系統來了解。
這使我想到,上一次在人民大學參加第二屆曆史考古青年論壇時,一位研究漢代考古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向我“征稿”,他很反感現在有些圖像研究解釋太過,奇談怪論太多,希望我寫一篇東西從方法上、材料上批評一下。這個我覺得很重要,但掂量一下自己恐難勝任。我想,這位先生之是以能看到這些問題,就在于他對材料有總體把握,不受欺妄迷惑(他在評議青年學者報告的時候對材料就可謂如數家珍,知根知底)。我倒願意發心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主要的漢代圖像材料從載體、時空、組合、題材、格套、裝飾、題刻的發展等方面好好作一番梳理,為越來越多人參與的圖像使用和解釋提供必要的基礎,這也是我們考古學研究的一項基本責任。我現在就放下這裡輕松的筆觸,去做這件沉重的工作。
附記:文中所論所及石刻,我基本都走訪過,但以往更沉醉于觀摩,往往忽略拍照,偶用手機拍點,去年以前的那個手機照片效果比較寫意,幸有各地朋友廣泛贊助。原文中有些涉及洛陽石雕的材料我自己拿不準,特向錢國祥先生請教出土和收藏情況,删除了資訊不明确者,以期更為嚴謹。亦特向上述師友緻謝。
附:考察途中作詩詞二首
太極殿阊阖門遺址懷古
阊阖門高薄日斜, 黃塵風急纛旗遮。
漢家舊業複無望, 魏室新臣老更奢。
傳鼓驚雷連甲騎, 流星飛羽亂兵車。
宮牆龍戰玄黃血, 豈是當時斬白蛇?
石州慢 中原訪古,用去年金陵、河北韻
野黍離離,搖曳此間,多少過客。燎原烈日無聲,躁動幾絲風色。難尋痕迹,隐約丘壟連綿,一齊抛向恩仇側。黃土細摩挲,認千年時刻。
中國,聆茲伊洛,問彼嵩高,總成沉默。縱使年年,踏遍人間阡陌。古今同夢,夢斷夢續何方,精神都付斑斑墨。暗處再燃犀,讀當時魂魄。
文 | 王煜